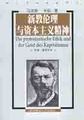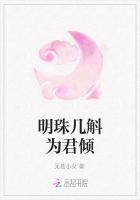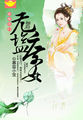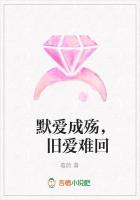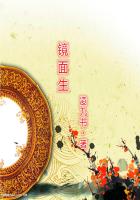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
曾国藩对“情态”十分重视。
“情态”与平常所说的“神态”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
前面讲到的“神”与“情态”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它们是里与表的关系。神”蓄含于内,“情态”则显于外,“神”以静态为主,“情态”以动为主,“神”是情态”之源,“情态”是“神”之流。
“情态”是“神”的流露和外现,二者一为表一为里,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说“情态者,神之余”。如上所述,如果其“神’或嫌不足,而情态优雅洒脱,情态就可以补救其“神”之缺陷,所以说“常佐神之不足”。
“神”与“情”常被合称为“神情”,似乎二者是一个东西或一回事儿,其实二者相去颇远,大有区别。“神”
含于内,“情”现于外;“神”往往呈静态,“情”常常呈动态;“神”一般能久长,“情”通常贵自然。总之,精神是本质,情态是现象。所以作者认为,“久注视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
情态与容貌之间,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容貌为形体的静态之相,是表现仪表风姿的,情态为形体的动态之相,是表现风度气质的,二者质不同,“形”亦有别。然而二者却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过唯有两美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常见容貌清秀美丽,而情态俗不可耐者,也有容貌丑陋不堪,而情态端谨风雅者,二者均令人遗憾。
再谈“恒态”和“时态”问题。“恒态”与“时态”是相互对照的一组概念。恒态,直解为恒定时的形态,具体地说,就是人的形体相貌、精神气质、言谈举止等各种形貌在恒定状态时的表现,在这儿主要是指言谈举止的表现形态。观察一个人的恒态,对帮助评判他的心性品质有重要作用。时态,与恒态相对,直解为运动时的形态,时态与人的社会属性、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人的活动,无不打上环境和时代的烙印。脱离时代与环境而独立生活的人是不存在的。连烽火岛上的鲁滨逊也用着其他人造的枪和火药。通过这一点,能充分体察出人的内心活动。
古人由于各种局限,未能明确地提出“恒态”与“时态”相结合的方法,较多地注意了“恒态”而忽略了“时态”,因而缺陷不小。曾国藩在这方面则脱出了前人的框子而有所创建,明确提出“恒态”,“时态”概念,由自发上升到自觉高度,在这方面比其他人大进了一步。
这也是曾国藩作为晚清重臣的过人之处。
古人并没能提出“恒态”、“时态”的动静结合方法,而《冰鉴》却弥补了它们的不足。实际上,恒态与时态相结合的方法,有辩证法的成分,能有效地避免机械主义的错误。
曾国藩在本章中指出了四种形态:弱态,狂态,疏懒态,周旋态,并给它们下了定义,作了对比和定性分析。文字不多,但微言大义,言近与远,值得借鉴。
“弱态”之人,性情温柔和善,平易近人,往往又爱多愁善感,“细数窗前雨滴”,缺乏刚阳果敢之气,有优柔寡断之嫌。即所谓的“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优,不重不轻正候,甘心消受,谁叫你会风流”之人。但这类人的优点和长处在于内心活动敏锐,感受深刻,若从事文学艺术事业或宗教慈善事业,往往有可能做出一定成就。这种人心事细密,做事周全,易叫人放心。;但不太适合做开创性的工作。“狂态”之人,大多不满现实,爱愤世嫉俗,对社会弊病总喜欢痛斥其不足,个人品性往往是耿介高朴,自成一格,正因如此,难与其他人打成一片,团结合作精神不是很好。但这类人有钻劲,又聪明,肯发奋,持之以恒,终能有过人的成就。历史上如郑板桥等人,就属这一类。但过于狂傲,失却分寸,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少的麻烦。如三国时的杨修,恃才傲物,又不肯遵军纪,随便乱说,掉了脑袋;弥衡,年纪轻轻的,不仅不服人,还公然擂鼓大骂曹操,丢了性命。他们的死,不能说曹操不负责任,与他们自己的狂傲不羁不无关系。
具“疏懒态”者,大多有才可恃,对世俗公认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不以为然,满不在乎,由此引发而为怠慢懒散,倨做不恭。这种人,倘若心性坦诚而纯真,则不仅可以呼朋引类,广交天下名士,而且在学术研究或诗歌创作上会有所成就。疏懒往往只是他们人格的一个侧面,如果某种事业或某项工作确实吸引了他们,他们会全身心地投人其中,而孜孜不倦勤勉无比。虽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疏懒不堪。但有一点则是无疑的,即断不能做官。上官一般不会选择他们作为下官,而他们既不善与同僚相处,也不善于接人待物,更不会奉承巴结上官。
他们这么做多半是因为不愿在这些人际关系方面去浪费精力和时间,因此他们宁愿挂冠弃印而去。如陶渊明,做了40多天小官,毅然辞职而去,宁去种田,‘‘带月荷锄归”,种种地,写写诗,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神仙日子。尽管生活很艰苦,他也自得其乐,绝不为五斗米向上官折腰。
具“周旋态”者,智慧极高而心机机警,待人则能应付自如,接物则能游刃有余,是交际应酬的高手和行家。这种人是天生的外交家,做国家的外交官或大家豪门的外掌柜,任大公司或大企业的公关先生或公关小姐,都能愉快胜任的。其办事能力也很强,往往能独挡一面。假若在周旋中别有一种强杆豪雄之气,那么在外交场合,必能折冲樽俎,建功立业。古人所谓“会盟之际,一言兴邦;使于四方,不辱廷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历史上盛传的蔺相如完壁归赵、唐睢不辱使命等故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然而,这中间仍须细细分辨,事物往往不会简单到四种类型就能概括一切,人之性态也如此:
“弱态”若带“媚”,则变为奉迎谄媚之流,摇尾乞怜之辈,这是一种贱相。
“狂态”若带“哗”,则为喧嚷跳叫,无理取闹之流,暴戾粗野,卑俗下流之辈,这是一种妄相。
“疏懒态”若无“真诚”,则会一味狂妄自大,此实为招祸致灾之阶,殊不足取。这是一种傲相。
“周旋态”若无“健举”,会由城府极深,迹近狡诈、阴险和歹毒,这是一种险相。对这种人,倒是应该时时警惕,处处提防的,不能因一人之险过而乱了自己的阵脚,甚至败坏了自己的事业。
在这一个是非之间,刘邵在《人物志》中明确提出一个“七似之流”的概念,就是说社会上有一类人,表面看来博学多识,能力很强,但究竟属不属实呢,就需要仔细分辨了。刘邵把这类人分为七种,称为“七似”,也就是模棱两可的人。
一似:有人口齿伶俐,滔滔不绝,很能制造气氛,哗众取宠,表面看来似乎能言善辩,但实际观察其脑子的知识,乃一肚子草包,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目前社会有很多这一类的演说家,我们要小心上他们的当。
二似:肚里有些才华,但明明缺少高等教育,却对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等各种问题都讲得头头是道。表面上看来似乎博学多能,其实样样通就意味着样样都不精。这类人以御用学者居多,这是似若博意者。
三似:有人水平低,根本听不懂对方的言论,却故意用点头等动作迎合对方,装出听懂的样子。在有权有势的人身旁常有这一类拍马屁的人,这是似若赞解者。
四似:有人学问太差,遇到问题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等别人全都发表完之后,再跟随赞同附和,应用他人的某些言语胡讲一通。许多不学无术的学者即属此类,这是似能只断者。
五似:有人无能力回答问题,遇到别人质问之时,故意假装得精妙高深的样子,避而不答,其实是一窍不通。有些官员遇到民众质问时,常认为不屑一答,加以回避,其实是不懂,故意顾左右而言他即属此类。这是似若有余实不知者。
六似:有人一听别人的言论就感到非常佩服,其实似懂非懂,就是不懂。是似悦而不译者。
七似有一种江郎人物,道理上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可仍然牵强附会,不肯服输,一味地强词夺理。此种理不直气不壮的人,在讨论场上处处可见。这是似理不可屈者。
前面所讲的各态,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作为用人者,应迎其长,避其短;在察看之时,则应从细小处人手,方可明断其是非真假,正大者可成器材,偏狭者会成败类,应注意区分。
本节承接前面,论述与“恒态”相对的“时态”。“时态”和“恒态”的概念,前面已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方有对谈,神忽他往”,正在与人交谈时,他却随便把目光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或者一个话题正在交谈中,他却突然把话题转到与此全不相干的另一件事上去,可见这种人既不尊重对方,又缺乏诚意,心中定有别情。
“众方称言,此独冷笑”,大家正谈得笑语嫣然,兴致勃勃之时,唯独他一个人在旁边作冷然观,无动于衷,可见这人自外于众人,而且为人冷漠寡情,居心叵测。
以上两种情况均与正常情态相悖,不合常理。如果不是当时心中有什么其他急事,导致他失常的表情,那么这种人多半是属于胸怀城府,居心险恶之人。这种人与他人建立良好友谊不容易,别人对他也敬而远之。因此,曾国藩评论为“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
前面谈到要从细处分辨,以上二种情形不细心,是不易察觉到的。粗者粗处看,细者细处看。曾国藩的价值取向和审慎之处就在于此。
“言不必当,极口称是”,别人发表的观点和见解未必完全正确,未必十分精当,他却在一旁连连附和,高声称唱,一味地点头“是,是,是”。这种人如不是故意的,定是一个小人,胸无定见,意志软弱,只知道巴结奉迎,投机取巧讨好别人。这类人自然当不得重任。
“未交此人,故意诋毁”,不曾与人交往,对人家全然不了解,全是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主观想像,就在人背后飞短流长,说人坏话,故意恶意诽镑他人,诬人清白。这种人多半是无德行的小人,无学无识,又缺乏修养,既俗不可耐,又不能自知。
以上两种人,由于品格卑下,又无识无能,庸俗无聊,鄙贱无耻,既不能与之共事,更不可与之共友。立身端正的人,应与这类人划清界线。当然,如果他们知而能改,又当别论。
“漫无可否,临事迟回”。生活中有一类人,他们优柔寡断、畏畏缩缩,做事只知因循守旧,而不知人有创新,陈规当除。因此,他们既缺少雄心壮志,又没有什么实际才干,动手动脑能力都差。遇事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喜欢推卸过错,不敢承担责任,不敢挑工作重担。
因而,他们什么见解也没有,什么事也做不成,徘徊迟疑,犹豫不决,空老终身。
“不甚关情,亦为堕泪”。指生活中那类多愁善感的人,他们内心世界很丰富,也非常敏感,见花动情,闻风伤心,如病中的小女人,软弱、憔悴。凡遇事情,不论与自己相不相关,都一副泪眼汪汪的样子,一种病中女儿态。
曾国藩对以上两种情况一言评之为妇人之仁。这个评断正确与否,贴切与否,精当与否,可以讨论。但文中所指的两种类型之人,确是存在于生活中的,要与这种人交谈共事,的确很让他人为难。须眉丈夫,整天如小女儿一样扭捏垂泪,谁能长久持之?这种人要去办什么事情?没有意志、没有头脑,全凭“夫君”作主,能有成就么?因而作者说不足与之论心。
以上几种情况,作者评为“时态”。我们知道,人的气质性格个性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终生不变的,一变俱变,因而曾国藩最后一句“三者不必定人终身”,足见他的客观公正,不以一语伤事之情状。
中国古代对人的性格气质等都有所研究,但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多散见于各种着述之中。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一成不变呢?不是。曾国藩体情察意,明确认识到性情气质不是固定永恒的,都是会有所变化的。更深一步说,作者已经明确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性情、人格情操、言谈举止,跟他的命运好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会决定人的终身命运。验之社会现实生活,可以发现,一个奸邪的小人却能身居高官显位,而一个正人君子却功名难求;贤相良将常常过早身首异处,巨奸大猾往往能够得享永年。“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屡见不鲜,不算什么怪事,因为社会生活太复杂了,没有固定不变的公式。
“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古人讲求学以致用。三种“时态”分析已毕,又该如何呢?知道这个道理,那么在生活中可以去发现那些与人真诚,不饰虚伪,勇敢果决,敢做敢为,主见沉浮,立场坚定之士,与他们交朋友、共谋大事,可以成功。反之,则不可与小人交往,以趋吉避凶。这实际上是衡量、检验选择人的标准,以此来评判所遇之人,自然可以确定哪些能成为亲密战友,哪些能同甘共苦,哪些人只能敬而远之,以此结交天下之土,可保无误。
但是不是就确保无误了呢?不是,我们知道,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固然是识人,然而最困难的也是识人。人人不同,就像各人的面目都不相同。外形相似的人内心世界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古人常有“贤不可知,人不易识”的感叹识人最常犯的两项错误:
以己度人,主观太深认识一个人,以自己作为衡量别人的标准,主观意识太强,经常会造成识人的错误与偏差。
先说《列子·说符篇》的一则故事。从前有一个人遗失了一把斧头,他怀疑被隔壁的小孩偷走了。于是,他就暗中观察小孩的行动,不论是言语与动作,或是神态与举止,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偷斧头的人。因为没有证据,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揭发。隔了几天,他在后山找到遗失的斧头,原来是自己弄丢的。从此之后,他再去观察隔壁的小孩,再怎么看也不像是会偷斧头的人。
这个人就是以自己来度量别人,主观意识太强,才会把老实的小孩看成是贼。他心中认定小孩是贼,因此小孩越看越像贼;他心中认为小孩不是贼以后,再怎么看都不是赋。其实小孩本就不像贼。完全受主观意识所左右,这也是由于主观意识作祟因而造成识人的错误。我们要小心提防。
三国时代精于识人的诸葛亮,就曾因主观太深而看错马谡。马谡历任竹县、成都县令以及越隽太守,能力过人,并好谈军国大事,诸葛亮很器重他。刘备在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希望你能察觉此事。”由于诸葛亮对马谡印象很好,因此非但听不进刘备的话,而且还任命马谡为参军。两人谈论军国大事,每每从清晨到深夜。公元228年,诸葛亮出师祁山,当时众大臣建议派魏延或吴壹为先锋,可是诸葛亮独排众议,任命马谡为先锋,统率大军与魏国的张交战于街亭,结果被张所击败。因为先锋大军败走,诸葛亮只好退守汉中。
以自己的主观意识认识人,这是人性上的弱点,也是识人的大忌,精明的诸葛亮都难免陷人其中,何况一般凡夫俗子。
深受个人好恶所影响当我们喜欢一个人时,就会忽略他的缺点而肯定他的一切;当我们讨厌一个人时就会忘掉(或忽略)他的优点,单挑他们的弱点而否定他的一切。
举一个实例来说明。
战国时期有一个叫弥子瑕的人。因为他长得俊美,所以很受卫王的宠爱,被任命为侍臣。根据卫国法律的规定,私下使用大王马车者,将处以割断双腿的刑事。弥子瑕因为母亲生病,就私驾大王的马车回家探病。卫王知道此事之后,不但没有处罚弥子瑕,反而称赞他说子瑕真孝顺呀!为了母亲的病竟然忘了刑事。”有一天,弥子瑕陪同卫王游览果园,弥子瑕摘下一个桃子,吃了一半,另一半献给卫王。卫王高兴地说:“弥子瑕真爱我啊!把好吃的桃子献给我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