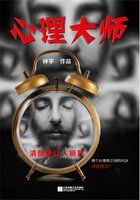正说着,有人喊“出发喽——出发喽——”,就见附近有人开始向马背上搭鞍驾,有的收拾帆布吊槽,有的从树干上解开拴马绳,牵马而行。段九儿正要收拾,被汤云拦住,说:“咱们可能先不过河。”段九儿迟疑间,翟团长和蔺副团长已匆匆赶过来,二人都披着雨衣,雨水落在二人肩头,在雨布上激起水花。
我吃力地从地下站起来,迎向他们。
“看你瘦多了,苦夏……”蔺有亮关切地看着我,“这强行军可走苦了你吧?”
“大伙儿还不都一样。”我带搭不理扔给蔺有亮一句。自打结婚酒席上,我就没给他一个好脸看。虽然他把我送到部队参军,是我的引路人,可是却又帮着把我弄到翟团长的婚宴上,这到底有违我的意愿。
“这样吧,你先跟蔺副团长走,过河,到宿营地好好休息。”翟团长对我说。
“不!”我拒绝道,“小汤说你病了,我跟王队长请了假来看你,现在你的病好了,我得回文工队去。”
“翟团长真的病了,上午头疼得厉害,我跟钱政委商量,想请你来照顾照顾……”蔺有亮解释道,“再说,翟团长也惦记你,担心你掉队,你跟我们团部行军会好一些……”
“要是图轻省,那我就不来抗美援朝了!”我依然嘴硬。其实我心里对这艰苦备尝的冒雨行军真的是发憷了。不过,让我以照顾翟团长有病的名义来到团部,其实是“照顾”我,对此,我还是有一种被轻视的感觉。就像与翟团长结婚的事情一样,总是不由分说,以种种理由强加到你的头上,使你失去自主。
“都是行军,跟我们团走也好,跟师部走也好,都得到前线不是?”蔺有亮劝慰我。
“让她回去!”翟玉祥突然发火了,或许是刚才会议的争吵余怒未消,他挥手冲我瞪眼,“你走吧!没人送你!走吧!”
这可令我尴尬万分:天色将晚,大雨不停,一路踩烂的泥浆,我到哪里找师文工队?况且,单人掉队被敌特工杀死的事时有发生,而我是一个没有武器的女文工队员……
“把我弄这儿来,让我自己回去,我怎么去?”我气得耍开小性子,一屁股坐在雨布上,别过头去淌眼泪。
“你走吧!”翟团长吩咐蔺有亮,“抓紧渡河,到对岸林地间选好营地,看看西边起雾了,估摸明天能有个好天气,部队可以白天好好歇一天……”
“那苦夏?可别让她一人……”
“不管她,你们先走!”
蔺有亮牵马离去。风雨中响起河水的浪涛声与人喊马嘶的嘈杂。
这时,翟团长从兜里摸出两块压缩干粮,走近拴在树上的黄骠马,爱抚地摸摸它的鬃毛,将两块压缩干粮摊在大手里,让马从他手中嚼食着。翟团长说:
“人累,马更累……它把你驮到这里,你再让它把你驮回去,它不觉得冤枉?再说,也不知你文工队今夜宿营地,怎么办?要不然,你就跟我们走到休整地,再送你回文工队……你要一定今晚归队,那只有自己走……再说,就是马能走,汤云也不能再离开了……哎,小汤,你怎么弄挺轻机枪,谁的?”
翟团长发现了汤云提在手里的机枪,转移了话题。我明白,事已至此,再不能人为地给别人添麻烦了,顺其自然吧。我不再吭气。
“这是三连掉队的,实在走不动了……”汤云解释着,瞅了我一眼。
“胡闹!乱弹琴!”翟玉祥斥责道,“你不懂得枪不离身吗?遇到情况,机枪手没机枪,打个鸟仗?”
“是我让小汤替别人扛的,”我替小汤解释,“那两个战士拉肚子,实在不行了……
“你,小汤,去到河边路口等着,掉队的上来把枪还他。告诉警卫连一排长,让他组织人收拢掉队的人,准备渡河,最后等团收容队上来,一个不落地过河!”
接着翟团长又吩咐段九儿搞点吃的,说是“弄点热乎的”,还笑着对我打趣:“咱热汤热水让人家吃饱,好让人家赶夜路回文工队,咱们这里条件差,看委屈了人家……”
“哼,人家还不如你那匹黄骠马重要嘛!”我撅着嘴说,破涕为笑。
其实,段九儿一听说团长要等收容队上来,知道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早已经在几块石头搭的野灶前蹲下去点火烧水忙活开了。原来,段九儿随时备有一小捆干柴,用雨布包得严严实实,就是准备应急用的。现在,段九儿点火烧开了水,撒进炒面,熬成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面糊糊。那时,我解开自带的搪瓷碗,让段九儿给我盛了一碗。算一算,一连七天没进热食了。我端着热面糊饭碗的手激动得发抖,扑面而来的热香气味儿引得我从心里发慌——轻轻啜一口咽下,香气满口,热流沁入肚腹!呵!在夜幕降临雨声不歇的洪水河畔,在遥远而陌生的朝鲜荒野,喝上一碗热面糊,真不亚于人间任何美味……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体味到幸福的滋味儿。
夜雨阵阵,打着我们头顶撑起的雨布,响起一片细碎的声音,犹如折断一捆细柴枝。马儿喷着响鼻,嚼着草料。不远处河水呜咽。偶尔响起一个士兵的吆喊。四周袭来凉气和树林浸雨后散发的酸腐气味儿。我在棚布下和翟团长对面而坐,喝着滚热的面糊,望着被夜色包裹着的他的微驼的身影,忽然心头撩起谈话的欲望,就对着暗影憧憧的他,断断续续地讲了起来……讲到过鸭绿江搭鼓动棚,讲到行军两脚磨出大泡又被雨水泡烂,讲到女同志解手多么不方便,讲到一连七天吃不到一口热饭……后来,翟团长扶我躺下,给我搭上了一件雨披。他说,要我睡一会儿,啥时候渡河再叫醒我。然后,他打着手电筒走向河边渡口……
我被从睡梦中摇醒时已是半夜。段九儿和汤云早已收拾停当。二人扶我上了黄骠马,来到渡口。黑黝黝的河面上,人们拽着一根绳索缓缓涉渡。绳索由河两岸固定,河中隔几步设一人固定绳索,帮助掉队的疲弱者依次渡河。翟团长在岸边等我。那时雨小些了,淅淅沥沥。翟团长没让我下马,他让汤云牵马,他和段九儿两边护着我,送我渡河。那时我刚刚睡醒,淋湿的衣服冰凉地贴在身上,我坐在马上裹紧雨衣,两脚蹬紧马镫……马儿踢起水花,马蹄蹬翻了河底的石头。我的小腿浸入了冰凉的河流。但是我并没有紧张——前边有汤云牵马,左有翟团长右有段九儿护着,我坐在起伏摇晃的马背上过河,有如坐在船上……
——从这天开始,我就成了一团司令部行军队伍中的一员。有时昼伏夜行,有时冒雨日夜兼程。大多数时候,我都骑翟团长的黄骠马。也有时摸黑走险峻的山路,山雨路滑,牲口都会失蹄落入山涧,便只有弃马步行。宿营时我便挤在团部首长用的帐篷里胡乱睡一夜。那些日子,骑马骑得我腰酸背痛,大腿内侧被马腹磨破,屁股也被马鞍硌得生疼。不过,再怎么着,骑马总强过徒步跋涉呀!知足吧,我这么对自己说。想想看,有马骑,有帐篷睡,时不时还喝上碗热汤热水的,这比连队战士白天冒雨行军、夜里时常露营的境况不知要好多少倍了。因此,在一团行军那些天,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尽量忍着,不给别人找麻烦,免得别人说我娇气。有时大雨中走山路,前后队伍都是男人,一侧山岩,一侧山涧,绕来拐去,无法解手,我憋不住,只好尿在裤子里,反正身上被雨快淋透了,留到宿营时再换洗。那时我真恨自己为什么不是个男人。
最令我担心的还是如何与翟团长平安相处。那些日子,我俩还处于新婚期。由于对怀孕的恐惧,使我有意逃避与他独处的机会。好在整日泥里雨里行军,宿营时众人共挤一座营帐,和衣躺下立刻会酣睡入梦,所以许多天来我俩倒还算相安无事。
但是作为已婚女人,这一劫还是没有躲过。
在顺川以南宿营那天,阳光很好,人们在帐篷外的林间松软的草地上休息。翟团长坐在一个树桩上,让理发员给他刮脸;蔺副团长又在摆弄他那台破半导体,沙拉沙拉响着,他时而拍拍,时而贴耳细听。钱之茂抽着烟,和通信参谋盯着架在帐篷外的电台。通信参谋以指节敲击电键,向师里发出宿营报告。那时我在树枝上晾晒昨夜大雨淋湿的衣裤,看见不远处林间阳光射进的地方,汤云和段九儿正搭建一个小棚子。
“好消息!”蔺有亮忽然大喊一声,将半导体贴在耳边,得意地向大家宣告,“李奇微同意和谈啦!听,同意咱们彭总的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谈判,他们的代表开车过来,挂白旗为标记……哈哈!”
“挂白旗不就是投降了吗?”钱之茂两眼发亮,“还准备打六次战役呢,这恐怕打不成了……”
“打不成?想好事吧!”翟团长已刮完了脸,抹着光光的大下巴说,“这和谈一开,日子就短不了,想不打都不行!”
“那照你说,和谈没意义吗?”钱之茂反问翟团长。
“要是不谈,嘁里咔嚓打,把美国人推到海里算完事!这一谈嘛,就不那么简单喽……”翟玉祥摇头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过去跟国民党就是这样,怕该耗日子喽……”
翟团长说罢,迈动两条长腿去看汤云和段九儿搭棚子。他用视察般挑剔的目光找出这样那样的缺点,看着汤云和段九儿尽心竭力地把小棚子搞得结实而舒服,然后满意地朝我走来。
我晾完湿衣后,正把从背包里拿来的一小袋柴灰向几个月经带儿里填装。这些柴灰是我前日在段九儿燃柴烧水时收集的,预备来月经时用。今天,我预感月经快来了,如不准备好,怕行军路上遇到情况来不及应付,便提前开始准备。
“你偷偷摸摸干啥哩?”翟团长走到我跟前,狐疑地望着蹲在一株树后忙碌的我。
“你别管!”我装好一个月经带,用别针把盛柴灰的开口处别好。
“我知道了——”翟团长看清我的“工作”内容后,狡黠地一笑,“你前天要那些柴灰,我就知道了,你快那个了……小那会儿,我娘我大娘她们也用柴灰……”
“知道了就别问了!”我给他一句。
“那就不问了。”他说,又问,“知道我要跟你说啥?”
“我不住那个棚子。”我头也不抬地说。
“你得住那棚子。”他肯定地说。
“不住。”我不想让步。
“得住。咱们要在这休整两天,你一个女的,混在大帐篷里,你不方便,别人也不方便,男人们爱脱个衣裳抓个虱子,说个男人的笑话啥的,都不行。见了你,心里都痒痒,脸上还得紧绷着,你住小棚子,让别人放松一下。”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
“那你别忘了结婚前答应的条件……”我不放心地盯着他,“你可别害我怀上……”
“你放心吧。”
他让我放心的意思我后来才明白:夜里他强行脱掉我的衣服时,他一再说:“你别怕,你快来月经了,别怕,我打听明白了,女人,来月经前那几天,行房就铁定怀不上……”
那时我对避孕常识一无所知。我拼命挣扎,挥舞双手将他的脸抓破。对怀孕的恐惧加上战场环境的恶劣使我不愿满足他。我认为他让我放心的解释无非是想泄欲的说辞。
但是,如同入朝前的临战娶亲一样,最终失败的还是我。我在惊叫与呻吟之后,忍受着下身的疼痛,轻声的啜泣中告别了我的少女时代。那时,夜暗中他满足于将洞房花烛夜未能完成的行为终于付诸实施。如雷的鼾声宣告了入朝前那场结婚典礼的正式结束。在我即将蒙眬入睡之际,隐约听到棚外拴在树上的马匹的踏蹄声,还有林边哨兵的一两声喝问……一九五一年七月上旬在朝鲜顺川附近山林间的一处临时搭建的草棚,是终结我处女之身的地方……
第二天降雨,部队放弃原休息计划,提前出发。因为白天冒雨行军比夜间行军视线要好,而且还能借雨幕云雾躲避敌机的轰炸。
部队冒雨在崎岖的山道上前进。那天,我骑的是另一匹白马,翟团长骑他的黄骠马,与其他几位团首长一同骑马行军。那天,翟团长显得精神很好,不时打马前后奔跑,大声催促部队。昨夜在草棚中,我的拼力挣扎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此刻并不知道,自己昨天刚刮过的脸上出现三道整齐的抓痕。他得意洋洋地策马小跑,嘴里还嚼着牛肉干。
“翟团长,你的脸怎么啦?”钱之茂政委故作关心状问,“昨天刮脸理发,还光光的,跟剥了皮的熟土豆蛋子似的,今天咋就跟猫抓了一样?”
翟团长一听这话,用手摸摸脸颊,回头瞪了我一眼。我扭转头,忍着不敢笑出来。
“嗯,昨夜那蚊子厉害!”翟团长说,“老叮我脸,痒得厉害,挠的……”
“哎呀,这蚊子,太大了!”钱之茂继续调侃,“把苦夏同志叮得又喊又叫的!”
四周人们哄笑起来。
走在我右前方的蔺有亮也笑着,还回头看了我一眼,就在我与他四目相对时,我感到他的目光有些异样,脸一红,低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