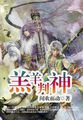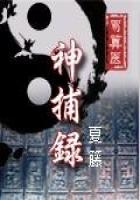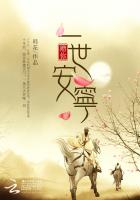写作永远伴随着困境。对我来说这困境带来的既可能是沮丧,也有面对挑战的兴奋。小说写作是一次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一条无限之路,需要我们的想象、耐心、勇气和洞见。我理想中的小说是人性内在的深度性和广泛的隐喻性相结合的。它诚实、内省,它从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出发,但又具有飞离现实的能力。它自给自足,拥有意想不到的智慧。它最终又会回来,像一把刀子一样刺入现实或世界的心脏之中。
2003年2月10日
关于公共想象问题
不久前,我从网上看了众说纷纭的《十面埋伏》。没有看完。但玫瑰坊的场景是看完了。我看到那些乐工,在章子怡跳舞的时候,在击鼓助兴。那鼓放在盛满了水的盆子里面。当然,这一切都有着张艺谋式的煞有其事。我怀疑这又是一个伪风俗。可是,即便是伪风俗,我还是得承认,像大红灯笼高高挂、像水中击鼓这样的场景,确实十分中国。至少,它符合我们关于中国的公共想象。在这个公共想象中,“中国”是奇观的代名词,“中国”是怪异的,腐烂的,也是性感的。事实上,这也许不是我们的公共想象,背后有一个西方的视野,但现在,我们早已不知不觉被西方改造,他们的公共想象自然也成了我们的公共想象。
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一不小心就会落入这样的公共想象。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这当然是一部好小说,但王安忆因为有了这部小说而被人同张爱玲联系在一起。当然,王安忆不喜欢这样的联系。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系?我想可能同我们对上海的公共想象有关。是公共想象在起作用。现在关于上海的想象,特别是对上海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想象,基本上有着像公式一样准确的话语。王安忆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也逃脱不了这种话语。可我有时候会有怀疑,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那个30年代繁华的上海真的存在吗?他们的日常生活同今天又有什么区别呢?可是,在我们对历史的想象中,这样的生活被湮没了。这是另一种话语的霸权。这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感到悲哀的地方。丰富复杂的上海,最终简单地变成了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就这样被命名了。
一个小说家,他可能受到几种公共想象的左右。一种是历史想象,来自于既定的历史话语。比如“文革”,由于右派作家们的叙述——这个叙述和主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现在关于“文革”的想象总是停留在这个大的认识上。另一种是文化,所谓文化其实是我们对某个地域的公共想象。在这个想象里,似乎有一种使小说人物变成某种类型的规约。这种想象在我看来,是很可疑的,它只能把野生的生活格式化。比如,现在,西部差不多又成了一个新的神话,成了又一个公共想象:西部是雄性的,是生机勃勃的,是史诗般的,或者是苦难的。而任何的公共想象导致的可能就是大量的复制。在这些小说里,西部人一个个都像是吃了壮阳药,紧张、激烈,情欲旺盛。
我对所谓的文化一直抱着警觉的态度。当然,我知道有一种以文化见长的小说存在,但在我这里,我更喜欢那种最直接地深入到时代的真相里面而不是被所谓的文化格式化的小说。小说中的文化情怀,很可能会把生活彻底地改造,我认为那是另一种意识形态为先导的写作。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西方想象中的东方,它芜杂、斑驳,我们所处的语境比西方更复杂,更纠缠不清。如果西方人怀着东方的梦想来到中国,那一定是要失望的。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其实很难依靠我们的传统资源去认清它。《红楼梦》当然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可它面对今天的生活可能是无效的,我们很难依靠它。我们也有这样的实践,比如贾平凹的《废都》,它所展示的生活,它的趣味,它的语言形态,确实十分中国,但《废都》展示的经验,真的就是我们的现实经验吗?从这个文本中,我看到传统趣味,那种文化想象改造现实生活的惊人能力。
目前,我们国家的小说写作确实不怎么依靠传统资源,中国作家更多依靠的是西方资源。这些西方资源,现在成了中国作家公共想象的另一种来源。面对着这么浩大的西方文本,我们的想象几乎很难逃脱这些前文本的影响。特别是关于城市的小说更是如此。现在的城市小说有很多在复制西方经验。那几个轰动一时的着名文本,看上去像是西方文本的复制品。
吊诡的是,这种建立在西方文本基础上的“公共想象”可以复制出一种“真实”的生活,一种完全西方化的“公共经验”。今天的所谓小资生活,他们的生活似乎源于这样的公共想象。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活是由我们的想象决定的,如何想象才会如何生活,然后再复制出共同的经验。反过来,有了这样的公共经验后,那样的公共想象得到了强化。我还发现,如果作品要畅销,要尽可能地符合公众的公共想象。很多关于西藏的作品,与其说是写出了一个真实的西藏,不如说它写出了一个公众和西方期待中的西藏。
在这里,我要提一下批评问题。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批评往往远离那个微观而饱满的世界,喜欢奔赴一个宏观的目标。批评似乎对符号的兴趣更大一点。这同文化性格倒是一致的。文化是如此之“大”,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在有关小说的批评上,有着一种类似于“文化”的批评方式。这其实是一种批评的集体无意识或惯性。批评总想在“公共想象”中找到一个稳妥的答案。
我承认,文化的力量大于小说这种艺术。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当然更看重生命的丰盛及精神的深邃,可是,对于宏大的历史,小说家看重的鲜活的生命形态根本比不上几个简单的符号。中国是什么?在这个符号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人可以不见,留下的可能只是长城、旗袍、故宫、脸谱这样的视觉形象,它们代表着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一种文化观念上的批评比小说艺术的鉴评更有市场。小说要获得好评,似乎也应该符合这样的一个公共想象。还是要用《废都》为例。《废都》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奇怪的文本,是一个另类,但它符合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所以,这本书在法国获奖也不是奇怪的事情。
这样的评价存在于今天的文化秩序中,可能也是我们的后人的评价方式。我有一个歪想,几百年或者几千年以后,我们当然成了古人。那时的中国人也许早就成了西方人,但这不等于说,他们没有东方想象、东方情怀。也许,他们会像今天的西方人一样想象我们这个时代,在他们的想象里,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同明清那么近啊。他们肯定会用这种公共想象期待我们。可是,我们今天的文学肯定不符合他们对故国的想象。当然,他们还是能找到一些的,比如贾平凹的《废都》。找到这个文本后,他们也许就可以放心了,这个时代还是他们的故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废都》可能是这个时代的经典。
当我说出这一切的时候,我深感那个所谓“公共想象”的强大,也许我没有足够的才智不受这种“公共想象”的影响,但我会对此保持警觉:我写下的这一切就是历史或现实的真相吗?这一切真的纯然是个人的感受吗?这有点儿像堂吉诃德,但我想,面对那个强大的存在,只有诚实地感知才能解救我们。
人及其时代意志
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开始趋向于文本的构建,趋向于脱离我们目前这个复杂的语境,而迷恋于文学的游戏性。在这里,我不想否认文学的游戏性,文学就其基本功能来说,它应该是容纳及拓展人类经验的一个容器。当我们把日常生活可能或不可能的经验放入这个容器的时候,是有游戏的成分的,是有着极大的乐趣的。80年代开始的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给文学减负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是没有意义,这个过程让我们的文学从被单一意识形态控制的状态中挣脱出来,给文学以新的自由和可能,使文学承担起文学应该承担的那部分。
“文学承担起文学能承担的那部分”,这种提法本身也许没有错,但是,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一句顺口溜,成为一句空话。什么叫“承担文学应承担的那部分”?“那部分”是什么?是永恒的人性,还是对文本的拓展?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样一种说法下面,文学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弱小。“个人化”成为一尊新的文学之神,任何写作都可以在个人化的神只之下合法化。
当然个人化或边缘化的出现是有历史根源的,同80年代知识分子热衷于参与的思想启蒙的受挫或失败有关,也同90年代欲望化社会的到来有关。80年代的思想启蒙实际上和主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关系,到后来才慢慢分道扬镳。知识分子的受挫感导致了一个个人化或边缘化时代的到来。本来,个人化也好,边缘化也好,表明了一种自觉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至少是对80年代的一种逃离或反动。但在实际的写作实践中,个人化或边缘化迅速地画地为牢,成为一种看上去像是自得其乐的潮流。边缘化成为一种对边缘人物的过度描述,在新生代的代表文本中,最多出现的是落泊的诗人、艺术家或流浪汉,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现实被摒弃在文本之外,边缘化成为“边缘世界”。在很多作品中,我们只看到一个自我放逐的“个人”。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但我一向对这样一种消极自由持怀疑态度。也许你可以说这种态度是我们当今语境下最为自由的方式,但我想质疑的是,这已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在复制千篇一律的人。况且,在中国语境中,轻带来的不是生命之重,而是轻快的逃逸,是自得其乐,是一场全民想象中的自我消费和自我狂欢。
我曾经撰文提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这种所谓的‘个人化写作’,有值得反思的东西。在某种艺术至上的趣味下,我们的写作已失去了同现实的广泛联系,变得自说自话。加上‘后现代’和相对主义风潮的兴起,我们似乎满足于发现意义的碎片。许多写作者的心中已没有‘国家’、‘民族’这些宏大的词语。这导致现在我们的写作充满了‘小事崇拜’,没有对时代对现实作整体性发言的气度。90年代文学在艺术上有着长足的进步,但在整体气象上,可能过分小气了。在90年代的写作中,缺少一种承担,一种面对基本价值和道义的勇气。”
我现在还是坚持这样的判断。我们的文学正在目前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现实面前失语,无所作为。写现实的作品不是没有,我们有很多写工厂、写下岗、写商战的作品,但这些作品除了经验的堆积,它所构成的现实依旧是可疑的。有人说,我们目前这个现实,有着无比复杂的经验。关于这个判断我基本同意,但我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经验都是无比复杂的,都是无比丰盛的。我认为写作不应停留在经验层面。经验是需要处理的,并通过经验去洞穿这经验背后存在的真相和价值。我们经常认为自己的经验有多独特,其实,作为历史中人,我们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在控制我们,我们的经验更像是被时代拷贝出来的,很多经验其实是相互的模仿和复制。因此,我觉得从经验出发去洞穿时代意志,看破时代的重重机关,并由此体恤人的真实处境,才是写作的根本。写作不应该停留在经验的层面。
我这里并不是想否定“个人化”,“个人化”当然很好,任何写作都是个人的,从个人出发肯定是写作的起点,这似乎也用不着过分强调,但如果“个人化”走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极度抽象的写作,那就会有问题。人不是孤立的,人处在各种力学关系中,这种力学的相互作用才决定他具体的表演。人是易变的,只有在关系中才能相对地确定。说起关系,其实小说中最大的关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小说永恒的主题,不知被多少人写过了,都写滥了。小说写作者其实一直存在着困境,我们经常说这个时代的经验无比丰盛,但是说到情感,人的纯粹的情感就这么几种,即使有同性恋,人的情感反应也大致差不多。小说如果写人性越纯粹,最后只留下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没法写。所以,小说必须走相反的道路,从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出发,成为一个独特的男人和一个独特的女人,这样,人必须和所处的时代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这种关系越紧密,人就会越具体越复杂。
每一个时代,人都会面对特别具体的问题和困境。这些问题绝不是那种“一个人的房间”的写作可以洞穿的。人是被时代劫持的。比如说到欲望,这欲望就有时代性,有着全民共同想象的成分。个人的欲望是被时代的共同想象带动的。
我们谈文学是离不开中国问题的。比如谈到自由,这自由就有大小,比如一条鱼,它在小鱼缸里是一种自由,在大海里也是自由。我们恐怕还是要探讨小鱼缸里那条鱼的处境。这就是我说的中国问题。再举个例子,鲁迅先生,他其实一辈子就在讨探那小鱼缸里的鱼,而冰心却在写大海里的鱼,她提出的比如和平、博爱等,确实是普世价值,但中国有着自身无比复杂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没资格在这些问题上同国际接轨。这样一比,大家都明白,鲁迅的伟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谈中国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小,但却是作为中国作家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概念,叫时代意志。我们都是历史中人,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意志的左右。我所说的时代意志非常复杂,它可能来自权力,来自意识形态,来自全民的共同想象,来自发展这样的历史逻辑。而一个时代的人性状况取决于此。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以我的小说《俘虏》为例。这部小说写了一个俘虏的故事。俘虏所处的社会,它的时代意识形态就是仇恨,这种仇恨已深入血液,支配了他全部的行为,这些行为肯定是反人性的。但这样的人,其基本人性、凡人应具有的情感反应他依旧存在,当他和一个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比如和美国人托马斯的关系,他对托马斯不是没有情感,但他内心本能的情感会使他非常困惑,他会陷入人性和意识形态的困境之中。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处境,一种激烈的处境。是一种仇恨时代的人的可悲的处境。
这个故事的人性挣扎有其时代的独特性,它和中国语境紧密相联。我基本上不相信所谓的永恒的人性。但我相信人的内心结构千百年来是一样的,即所谓人性中有善与恶,有罪与罚等等。变化的是时代面貌,是加在人性身上的“力”,正是由于这个“力”,人性就会变形成另外一种极端的状态,如果说你能触及人性中最隐秘的部分,那一定也触及了这个“力”,有时候,这个“力”就叫做荒谬或荒诞。这就是我所说的同现实广泛联系的意思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