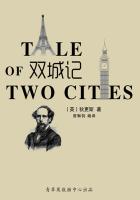父亲只是粗通文墨的武将,想必不会设置过于难解的字谜。他在那样的场合将秘藏托付给义女,既是郑重托付却又不说所藏为何物,那就不会留下过多的迷障。
我靠着偶然的指引找到了韩府那棵梅树,而她要找的却是另一棵。这金陵帝都有无数棵梅树,韩公墓所在的梅岭冈也有满山的梅树,我如何找到父亲指定的那一棵?
耿先生在我身上写下四方之神的文字,她说只是为消除我的鬼风疹,我却阴差阳错地找到了那秘画。若说那只是偶然的发现,那么,另一种偶然又会导致怎样的发现?
父亲最先付托的人是她。后世明智的有心人啊,你们当会看出这个“她”指的是黄保仪。她是李后主的“保仪”,可她又是我的什么人?在那样一个悲凉的秋夜,她与我有了那样的肌肤之亲,而她也是我父亲的义女。请恕我这支拙笔无以写出那得体的称谓,依我有限的学识,我也无法从先贤的典籍中找到一个合适的称呼。我确实难以在此后的忆述中将她称作“黄保仪”,倘若使用那样的称谓,我就感觉写的不是她。姑且暂用这个“他”字吧,且为避免这种拙笔,我将尽快结束对她的追述,而她将是我铭心刻骨的记忆。(编者注:原著这段文字中用的是“他”字,而“她”是现代文学家刘半农先生所创的新字。一九二○年九月,刘半农在《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情诗中首次使用了这个“她”字。现代白话文运动遭人诟病,但这个“她”字却是为人称赞的创造,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白话文运动惟一值得称道的成果。)假如我不是如此这般偶遇她,我就全然不知父亲对我还另有一重托付,父亲要我找到更重要的秘藏。
她要寻找的也是一棵梅树,但显然不会是韩府的那一棵。或许她要找的梅树就在这后宫,但若在这后宫,那就更像是给她的托付。我来到这里,只是一种偶然。
“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她若有所思地把玩着诗扇,“这‘归来’二字怕是大有理解,莫非是说……是说回到原先的那梅树?”
“曹溪?若说原先的梅树,那就是在曹溪……”
“念佛参禅数如尘,认得曹溪有几人!”
“可是南汉已亡,岭南已是宋国的地盘,听说宋主赐名‘南华禅寺’了……”
“有时我也思想,那秘藏会否就是无尽藏的真身?人说那女尼真身还在曹溪,然则又一想,就算还在,也只是个肉身……”
我望着她手中的诗扇,这是父亲留给她的诗扇。栖霞山上,舍利塔前,义父义女匆匆相见。他们等待了十几年,而片刻之后或许就是永别。我想象着他们相见的场景,那经幡,那风铎,那塔室倚柱上的偈语。我也曾经站在那里,那个女道人将我唤住,那时我正站在舍利塔前的一株梅树下。女道人在那里送我一枚诗签,父亲在那里送义女一把诗扇,而诗签和诗扇上皆为同样的诗句。我从那里开始了这番找寻,而她也是在那里领受了这重托。我想象着父亲向她赠扇时的情景,我看见兀立在她身后的那棵树。
“你与父亲会面时,你身后就有一棵树。”
她惊愕地望着我,我却故作镇静地拿过那诗扇。我右臂的伤口依然在隐隐作痛。她满含期待地望着我。
“你确是想到了,我想也是的,这‘归来’二字实有所指。”
“那是一棵梅树么?”
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在这衰迈枯槁之年,我的忆念笼罩在一片梦幻中,亦因那真切的经历恍若一个梦境。蔷薇院就是那梦境。我在昏迷中醒来,就发觉自己躺卧在那绣床上。我与那女子交欢,浑然忘却外边的世界。直到那侍女庆奴回来,我才从那梦中惊醒。
庆奴说禁军在宫墙外发现了我的尸身。那里发生了一场鏖战,耿先生带林公子出逃时,有几十号禁兵被杀,林公子却也没能逃脱。那些禁兵的尸体有的顺着护龙河漂走,更多的就堆在那宫墙下。他们发现了一具面部摔烂的尸体,小长老确认那就是林公子,他能认出那衣袍,因他曾与林公子换穿过。庆奴说罢便冲我挤挤眼,我立时就明白了她们的用心。
“难为你送去那脏袍子。林公子已死,我可以从此隐身了。”
“只是难为耿先生了,只为让你隐身,她却成了逃犯。”
“不知耿先生往何处去了?”
“奴儿听说……听说追兵去了城北……”
我眼前闪过耿先生那飞跃宫墙的身影。她本是早就能够轻易脱身的。庆奴送去我的衣袍,那显然是在我昏迷之后,也许是在她们为我拔箭疗伤之后,如此看来,耿先生定是又重返那宫墙外。她来去自如,自然也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行踪。追兵北去,或许是她的有意误导。倘是如此,难道这只是为掩护我逃命么?
耿先生也曾说,对于史虚白、韩熙载和林将军之间的秘传,她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今三位护法都已离世,那墓中谶图也非最终的秘藏。耿先生引我找到了那秘图,而今她又以这易装之计使我隐身,她依然对我有所期待。
此时此刻,她确是在为我作掩护。
“此一去天各一方,未知相会却在何日……”那女子哀伤地站在一旁,噙泪望着庆奴为我换上禁军的箭衣。
三名禁兵已来蔷薇院接我。他们就站在那蔷薇架下,那花架缀满深红色的花朵,那些花叶沾着晶亮的露水。在这离别之时,我这颗心却因伤痛而麻木。
我匆匆走过花径,走出院门,竟也不曾回望一眼。
国主的后宫仍是一片混乱,有人在百尺楼上敲锣,有人在花树间乱窜。澄心堂仍在燃烧,禁兵们便破例进入后宫巡值。灾变并未终结,我难以料想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变故,而我要尽快赶往栖霞山。
申屠令坚曾任禁军都虞候,三名禁兵接我出宫,这自是他的安排。我与他们走成一列,抄捷径快步走出这后宫。
他们在后宫前廷的界门处并不停步,那守门禁兵恭敬地放行。我随他们疾步穿过前廷几重殿廊,又走过太医院和御马监,前方便是皇宫的东门。
门楼上响起五更的鼓声。伴着这沉闷的鼓声,远处传来报晓的鸡鸣。
宫门外停着一辆双马大车。车厢高大沉实,外壁包裹着防箭的铜皮。他们一径将我送到马车旁。
厢门打开,里边就是那虬髯阔口的黑面大汉。
我右臂受伤无法向他行叔侄礼,而他伸出大手一把将我拉进了车厢。这浓眉巨眼的申屠令坚,此刻他面色铁青,眉额紧蹙,满脸憔悴忧煎之气,双眼发红似要冒火。他一把按我坐下,我看见前边的长案上有几只盐水鸭。我强忍着不要哭出来,申屠令坚性如烈火,而此刻他只是恨恨地磨牙裂龇,那大手又猛地抹了一把泪水。
“吃!”他强忍悲恸塞给我一块鸭腿。
“侄儿要先去妙因寺,还得劳苦世叔。”
“随你去!耿大侠说你长成人了。”申屠令坚探身冲着驭卒喊,“栖霞山!一径东去!快快!”
申屠令坚声如响雷,这个豪爽朴直的黑大汉,他曾在林府的球场上放怀大笑,我想今生是再难听到那样的笑声了。
“吃饱再说……”他的声音忽然有些哽噎,他又从案下拽出一壶烧酒。他已是满身酒气,案上的两个酒壶早已倒空。
我咬一口鸭肉,竭力使自己平静些。他仰头猛灌一气,又把那酒壶递给我。
“去过妙因寺,我就回家看阿母,不知她眼下……”
“有你婶母在陪着……夜来她不茶不饭,水米不沾……”
“我要回家去……”
犹如万箭钻心,我强使自己不哭出声来。我垂首无语,泪水模糊了我的眼。当我从家中的复壁惊慌逃离时,母亲也是强忍着泪水。母亲就站在那栀子花树边,她只是缓缓地伸出一只手,那手势像是要拭泪,也像是在向我挥别。(那时我竟未想到是诀别,不然纵使为救父亲而逃亡,我也绝然不会那样匆匆离去。那时的我竟是如此的愚钝!我至死都难以饶恕自己这罪过。)
“我不能放你去送死!”申屠令坚在大口吃肉,转瞬间他就吞下了一只盐水鸭。我抱起酒壶喝一大口烧春,这才感到略有些神智。
在这颠簸疾行的马车上,申屠令坚对我说起这场灾变的原委。给父亲派送毒酒者不是别人,而是大将军皇甫继勋。皇甫继勋与内侍监相串通,他们惟恐夜长梦多,而国主又是优柔无断之人。申屠令坚带人劫狱,岂料还是迟了一刻。
父亲遇害当在二更三更之间。那时刻我走下韩府的柳堤,灯笼的烛火忽然腾起尺余高。那时我恍若看见父亲接过一樽毒酒,又看见他双手摘下头盔,摘下自己的头颅……
烛火为一阵阴风所吹灭。那便是父亲的离魂之征了。
我望着车座上的头盔,这是为我预备的行头。林公子从此已成死人。此刻我身着禁军箭衣。他们再难辨认出我是谁。
那本该是万无一失的营救!申屠令坚说起他与耿先生的几番筹划,那些筹划不可谓不缜密,我忽然想到她在山上和酒楼两度现身,她在史虚白墓室再度现身,我曾疑心她的诡秘无踪,而她其实是在为营救父亲而奔走。申屠令坚劫狱失败,他却不知彼时耿先生正在韩府,而待他得知耿先生带我进宫,便先是派人在澄心堂放火策应,尔后又按约接我出逃。
耿先生竟也有如此的失策!她本以为内有宫人为命灯添油,外有申屠令坚带人劫狱,而劫狱者既有申屠令坚原先的部属,亦有她本人结纳的江湖好汉,这番营救应是有绝对的胜算,是以她虽明知那宝匣所在之处,只因劫狱时刻尚早,便仍要给我那番历练。
而我依然疑惑不解,耿先生究竟为何要带我进宫?难道是为让我送死么?
申屠令坚说,凭耿先生的神力,那些禁兵决然不是对手。耿先生带我进宫是为面见国主,即使劫狱有万一的意外,她仍可说动国主手下留人。耿先生自恃与元宗帝有交情,她实指望国主能顾及先皇的情面。(编者注:据吴淑《江淮异人录》记载,元宗皇帝曾召耿先生入宫,特处之别院,且尊其为“先生”。“先生幸于元宗有娠,谓上曰此夕当产神孙圣子。夜半烈风震霆,室中人皆骇惧,是夜不复产。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惊问之,先生曰:昨夜雷电中生子,已为神物持去,不复得矣。”在编者看来,耿先生与李煜父皇的交情确非寻常。林公子叙述至此却有意省略,虽无伤大雅,但也难免有为尊者讳之嫌。抑或是,吴淑所记只是道听途说。)
我说最早告发父亲的人是朱铣,申屠令坚便猛一拳砸下:“杀!”
申屠令坚忽然脑袋一沉,立时就有鼾声大作。从吉州到金陵足有两千里,这位北方大汉竟是三天三夜驰至,驿马累倒数匹,终来却是一场徒劳。父亲本是神武军统军,申屠令坚也曾是神武军都虞候,前方战事吃紧,国主却欲节制武将,先是调林统军兼南都留守出镇洪州,后又委任申屠令坚为吉州刺史。(编者注:吉州即今江西吉安。)父亲遽然接旨回朝,申屠令坚恐有不虞,便晨夕兼驰两千里来救。有这样的生死之交送别,父亲当感欣慰。
天色破晓,栖霞山依稀在望。苍峰翠屏,逶迤连绵,云天相接,景色空濛,望去好似一轴山水。那伞状的山巅雾霭缭缈。那伞峰之下究竟遮蔽着什么?
梅树就在那里。我的命运就在那里。我望见它在雾中的身影,那是显现在晨雾中的虬枝和疏影。这并非梅树的花时,那苍劲的枝干虽有冰姿玉骨,远望却像是一棵枯树。枝柯横逸,风姿夭矫,那风姿中亦有一种清泠。山风袭过,那树影愈显荒寒和孤绝。
似曾相识的景物。我曾见过这株梅树。就在那幅《栖霞无尽图》的立轴中,就在那幅画面的近景,就在那座石塔前。这是我所忽略的画笔,我曾看见过画中的这棵树,但我并未看清这是一棵梅树。
此时此刻,展现在我眼前的景色正是那幅《栖霞无尽图》。梅树,石塔,寺院,山峦,云气,还有那溪水。
栖霞无尽图。这是画轴中的栖霞山,也是我眼前的栖霞山。或许这并非董北苑有意为之,画师只不过是画下他眼见的山水,也画下他心中的山水;或许这只是父亲的选择,他选择了一幅最合适的画留给我暗示;或许这只是我愚蠢的推测,但我确也难有别一种破解。那画题中的“无尽”二字分明也有含义。三百年前的那位比丘尼,她的法号是“无尽藏”,她的禅诗出现在耿道人的诗签上,出现在韩熙载的诗轴上,也出现在父亲留下的诗扇上……
我沿着清澈的溪流走近这风景,三百年前的那位女尼,她在寻春回来时拈花微笑,那时她就站在清澈的溪流边,那溪流会是眼前的这道溪流么?那梅树会是眼前的这株梅树么?
寺院老住持对我说,这是一株晋代的古梅,那位南齐隐士舍宅为寺时,这梅树就已在此地了。老住持说,那位隐士号为“栖霞”,此亦即栖霞寺名的由来。
这确是一株古梅,非有数百年时光,树干便难有这般的苍古。
既是一株古梅,树下就未必有秘藏。韩府那株梅树下也无秘藏,那梅树将我引向近旁的墓丘,我在那墓室里发现了金塔,那秘图就在金塔的地宫里。那座金塔与眼前这座舍利塔形制如一。如此看来,这梅树或是要将我引向这白塔,引向这石塔下的地宫。
我无法进入这石塔的地宫。这是父亲十几年前主持改建的石塔,当年改建时也并未打开地宫,这地宫里该是藏有隋文帝从神尼手中得到的舍利子。佛骨固然是旷世宝物,但栖霞山佛骨并非世间惟一的珍存。隋文帝将舍利子分送与八十三州寺院供奉,而普天之下也有更多高僧大德的舍利子。父亲拒献的恐非是这佛骨。父亲原本也是奉旨改建此塔,这寺院本就是皇家的林山。
地宫之上的这座舍利塔是实心塔,若想进入地宫,恐是要推倒这石塔。这七级八面的石塔凌空高耸,这也是天下最高的舍利塔。我难以想象父亲会指望我推倒这石塔。这石塔亦非人力所能推倒。
巨石雕凿的构件,它们严丝合缝地接合成坚固的塔身。仿木造型的密檐,刻琢精细的雕像,须弥座式的塔基,这石塔的表层也难有藏物之处。
我沿着这八角形的塔基缓缓绕行,八面基坛是八面浮雕,这是一些有忍冬花镶饰的精美浮雕,这些石雕刻画的是释迦牟尼八相图:投胎、诞生、出游、苦修、降魔、成道、说法、涅盘。
申屠令坚并不近前,此番上山他只为保护我,却也并不探问我要找的是何物。此刻他正坐在那梅树下犯困,他的身边放着一柄八棱紫金锤。
我绕塔三匝,默然伫立。我仰望塔身这尊披坚执锐的武士像,这武士扬眉怒目,胡须飞扬,一手攥拳向上,一手前伸紧握,这身形酷似一个执凿挥锤的石匠。我恍若看见父亲的身影。
父亲离家前那最后的姿势。
这是我似曾相识的姿势。
石匠的姿势。
我又细察这幅释迦牟尼涅盘图。这位默立于卧佛身旁的菩萨,正是我能认出的弥勒菩萨。释迦牟尼是现世佛,弥勒菩萨是来世佛。弥勒的神态令我想到父亲拿走的那尊金佛,一样的敛目低眉,一样的妙相端严。我望着这色泽黝亮的弥勒像,就见他的衣纹中隐现出几个小字:立地成佛。
这阴刻的小字并不醒目,却是显得很怪异。我再回看前边七面浮雕,却都并无类似的题刻。而更奇异之处还在于,这是父亲的笔迹!
这显然是新刻的文字,笔道粗重的凿刻,虽是未经精细打磨,我却依然能确认这笔迹。父亲是行伍出身,平素从不轻易以字示人。他的书法虽不能与那些文雅之士相比,却也刚毅凝重,自有一种劲峭沉雄的风骨。那么,这几个字是父亲自写自刻么?父亲投军前也曾做过石匠……
——立地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