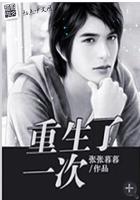消息传到刘首辅和肖侯爷那里,两位顾命大臣都没有别的话讲,一是在珍宝斋一案,武景行的功劳是抹不掉的;二是勇毅伯无嫡子,只有这么一个庶出的儿子,千顷田一根苗,如今瞧着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自然是能扶持就扶持;三是皇上已然下了旨,就算他还没有亲政,这样只是升任一个人做近卫,并非涉及国家大事,没有皇上头一天下旨,顾命大臣就说不成的。
有这三条理由,武景行升任一等侍卫的明昭,在腊月二十八各衙门封笔之前,连同着表彰锦衣卫衙门、九门提督、京兆尹的明昭一起发了下去,众人都各有封赏,可若论实惠,自然是武景行的官升两级,又成为天子近卫最为实惠。
武景行欣喜之余,心里却还是放不下管仲明一事,趁着朝会悄悄地将父亲勇毅伯叫到一边,将许樱的话跟勇毅伯说了,勇毅伯却道,“张家庄的案子早就被定成是管仲明一伙人犯下的血案,锦衣卫早就问过张大户十余次,若是管仲明真是有一条腿是木腿,锦衣卫自是早就知情,他们如今不说,却将那人认成是主犯,你此时揭穿此事,怕是极为不妥。”
“可是……”
“你放心,锦衣卫也怕管仲明在外面犯下什么案子,将他们牵连进去,自会私下严加查访,那管仲明经过此事,怕也是要远走高飞隐姓埋名了,你如今刚升任了一等护卫,要细思如何为国尽忠卫戍圣上才是。”武景行升任一等侍卫,又入了天子青眼,这世上怕是没人比勇毅伯更高兴的了,自家妻子不冷不热态度暖昧不明、公主咄咄逼人,连二弟都态度暖昧,自己想要庶子承爵仅有五成不到的把握,如今儿子得了圣上青眼,这五成把握自然是涨到了八成,连带公主都收敛了许多,怎能不让他高兴。
武景行听着父亲的话,心里也知父亲说得是实情,只得感叹官场纷繁复杂,万事暖昧不明,自己身在局中,抽身不得。
腊月二十八这一日京城的百姓晨起推开门,便瞧见自家的院子、房顶、树梢、院子里、灯笼上、都盖着一层厚厚的雪,天空中飘飘飒飒刮着细如盐面的雪花,昨日刚粘好的春联也被雪沾湿了,有些被大风吹得有一半飘了起来,只有一半顽强地粘在门楣上,只得拿出昨日剩下的浆糊,一个一个重新沾过。
许樱因知晓管仲明漏网而郁结的心思,因外面的瑞雪略好转了些,山不转人转,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在,总有一****能替许榴报了这血海深仇。
连成璧自衙门里回来,见她推开窗站在窗边瞧着外面的雪景发呆,嘴角上挂着笑,不由得坏笑了一下,将自己冻得冰凉的手一下子贴到她的脸上,“呀!”许樱吓了一跳,转身瞪了他一眼,“好凉!”
“夫人都腊月里开窗了,怎能嫌为夫的手凉。”连成璧笑嘻嘻地说道,略踮起了脚,越过许樱的身子,将窗户关上了。
“探花郎,您的对子还没写呢。”许樱笑道,“您若是不写,为妻的就谴人去街市上卖了。”
“自我十岁起,连家就没买过对联,若非我懒得写,连外面商铺的对联都不用旁人动手。”连成璧板着脸道,“来人,拿裁好的撒金红纸来,老爷我要写对联。”
许樱见他如此,不由得笑了起来,“再将我收着的红梅贺春的墨拿出来,我亲自替老爷研磨。”
丫鬟们齐声应了,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拿来了文房四宝,也拿来了早就裁好预备写春联的大红撒金纸,许樱亲自替连成璧研磨,连成璧想了想,因是春联也不需什么咏志表情,他看了眼门外的大雪,写了“东风迎新岁瑞雪兆丰年”偏想不起横批要用哪一个了。
许樱瞧他有些着急,接过他手中的笔,写了天遂人意四个字,虽说有些不工整,合着今年一个冬天未下雪,偏腊月二十八下了一场大雪的情境,颇有些趣味。
他接下来又写了十几个福字,让丫鬟们拿出去交给男仆们去贴,他与许樱少年夫妻独立门户在京里过年,倒也过得有滋有味。
到了下午的时候许昭龄派人来传口信,说是因年前事多,他乞休的折子并未批复,山东的老太太身子已然是不行了,他们夫妻决定提前回山东,因走得仓促未曾当面辞行云去。
唐氏……快死了?许樱从心里往外想笑,可是到了嘴边却只觉得苦,这样的一个祖母,整整两世对她除了伤还是伤,与其说是亲人,不如说是仇人,她费尽心机才将她扳倒,眼看着她从威风八面到了后来众叛亲离威风扫地,有唐氏在,就似是有人在她心里扎上一根刺,每每得意忘形这根刺总会疼起来,疼得她忆起上一世种种苦楚不堪,如今这根刺死了,就要被拨出来了,她只觉得心里发空。
连成璧知道她与唐氏的心结,他这样自幼失母在祖父母跟前长大的,虽说是被泡在蜜罐里的,也晓得不是旁人说是亲人就是亲人,有些亲人不如仇人,唐氏阴损毒辣几次想要害许樱母女,虽被一一化解了,想起来却也是凶险万分,连他这个旁观的都替许樱一个小女孩捏一把冷汗。
“你刚才写得横批不好,拿出去怕要被人耻笑,不如再写一个吧。”连成璧故作泰然状。
“就这般拿出去贴,世人都晓得这是探花郎的府邸,要笑也是笑探花郎文笔不通。”许樱侧头娇笑道。
“怎能说是我文笔不通?你那字写得秀气圆润但凡认得字的,都能瞧出是出自妇人手笔。”
“妇人手笔又如何了?”两人半真半假地吵了一会儿,唐氏的事被这么一打岔倒显得不那么要紧了。
大年初二许樱就打点了礼物同连成璧一起往杜家三位舅舅家里去送礼拜年,大舅舅杜德年听说了连成璧将杜家老三杜家俊荐给了山东的杨老先生,颇有些不高兴,当初他的长子也是杜家的长子嫡孙杜家成一样是个读书的种子,偏偏身子骨弱些,生生地被熬死了,也未曾见好外甥连成璧帮一帮,怎么二弟的次子,大排行行三的杜家俊就有这样的运气,明明资质平平,竟得遇了明师?
因此见到连成璧夫妻来了也不甚热络,颇说了些酸话,杜家大太太却与他不是一般的心肠,她心里惦记的还是自己的女儿惠萍,连使了几个眼色给杜德年,让他多跟外甥说几句好话不成,便借口前厅乱得很,将许樱叫到了自己的房里说话。
“前日我听人说,亲家老太太有些不好了?许亲家回了山东?”
“祖母大人原就有中风的毛病,听说又重了些已然瘫在床上了,虽说有我母亲衣不解带的伺候,也不见好,我六叔和六婶怕见不到她最后一面,没等朝廷的批复下来,在孟掌院面前陈了请,年都未过就离了京,我也是日夜悬心,盼着山东来信,又怕山东来信。”许家那些恩怨,许家人自己知道就好,外人知道了徒曾笑谈。
“唉……”杜大太太摇了摇头,“若是中风之症,我可是知道厉害的,我娘家伯娘就是中风去的,一开始是嘴歪眼斜,后来便是半边身子不能动,到最后就是瘫在床上,屎尿便溺全不由己,我们这些个做晚辈的瞧着也是心疼,后来她去了,我大伯父说去了便去了吧,她这是受罪受到头了……”她说到这里见许樱脸色未变,知道是说到了她的心里,这才放心,“唉,这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别瞧你大舅舅脸色不好,他那是有心事,你大姐姐又大了一年,已然十八了……还是高不成低不就,你大舅舅心里不喜,又不好当着孩子的面发火,这才……”
许樱听她这么说,心里就明白她的意思了,大表姐惠苹年龄实在是大了些,除非苦命连赶上几个孝期,这个时候还未定亲的女子实是少见,她又想起连成璧瞧见惠萍时的眼神,这个大表姐和自己的嫡亲婆婆长得太像了,若是没有个好归宿,怕是成璧也是不安心的,“我们夫妻年纪轻,见识少,在京里认得的人也不多,大舅母若是不嫌弃山东山高路远,我倒可以让成璧写信回去问一问,还有哪个亲朋故旧家里有年长未婚的,总能找着个才貌双全的来配表姐。”
“你既有这话,我就放心了。”早几年她都不嫌弃山东山高路远,更何况是现在,只是有一宗,“不瞒你说,你舅母我自从嫁到杜家,就未曾过过一天好日子,唯愿惠萍能找一个家资殷实为人正派的,是不是初婚我都不挑,那怕年长些呢,知道疼人会赚银子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