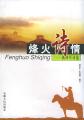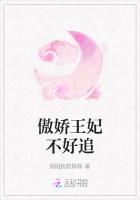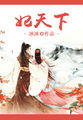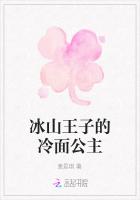李渔之前,也有不少人界定词的特点。例如李清照倡言词“别是一家”:“……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可以看出,易安居士主要从两个方面阐明词与诗的区别:第一,是从填词须合音律的角度,把音律上不太“正宗”的词(即她所谓“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和音律上比较纯正的词相比较,以见出词不同于诗的特点--这是她花费较多口舌所强调的重点,不惜罗列众多具体事例予以肯切、详细地论述。这是比较明显的方面,人们很容易看到,也很容易理解,以往学界所注意者也多在此。第二,是从词与诗这两种不同体裁样式的比较中,见出它们在题材、内容、风格上的差异。李清照对这层意思说得比较隐晦,寓于字里行间而不怎么显露,若不特意留心,它可能在人们眼皮底下溜掉,以至古往今来学者大都对李清照话语中的这层意思关注不够。其实它对区分词与诗的不同特征,甚至比第一点更重要。请注意李清照“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这句话。我体会所谓“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的意思,乃谓填词相对于作诗,是“作为小歌词”;后面“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中,又一次提到填词是“作一小歌词”。很明显,李清照特别突出的是词之“小”的特点。这“小”,主要是题材之“小”,另外也蕴含着风格之“婉”。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是艳科。词善于写儿女情长、风花雪月之类的“小”题材,词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婉丽温软。几乎从词一诞生,人们就给它如此定性。如果说李清照认为像“欧阳永叔、苏子瞻”等善于赋诗的“学际天人”倘填词(“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小之又小;那么,与填词之“小”相对,作诗又当如何看待?从“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的相反方面推测其言外之意,她显然把作诗看得“大”许多。倘填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则作诗应该是大海航行般的“大”动作,是写“大”题材,用今人常说的话即:“宏大叙事”。李清照的这个思想也贯穿于她自己的创作中。兹以李清照写于同一时期的一词一诗相互对照说明之。绍兴四年(1134)九月,金军进犯临安(杭州),为避难,孤苦伶仃而又秉性坚毅的李清照逃至金华。第二年即绍兴五年暮春,写下《武陵春》词,紧接着,在春夏之交,又写下《题八咏楼》诗。《武陵春》词曰:“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题八咏楼》诗曰:“千古风浪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洲。”李清照的这首词和这首诗,不但写作时间相近,而且写作地点相同。最近我到金华开会,有幸登临八咏楼。此楼乃南朝齐东阳郡太守沈约所建,位于双溪江北岸,拔地而起数十米,巍巍峨峨,矗立于群楼之间如鹤立鸡群,在今天仍然是庞然大物,若在千年之前,肯定是当地第一高度。站在八咏楼上南望,词中所说的“双溪”--即从东南流来的义乌江和从东北流来的武义江,正好在脚下汇流成婺江向西流去。李清照当时已年过半百而孑然一身,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江山破碎,物是人非,此情此景怎能不感慨万千!其愁其苦,非一般人所能忍受。李清照在这种情境之中写的词和诗自然不能不涉及到“愁”,而且于国于家于己,都是大苦、大悲、大愁。但是,请读者诸君将这词和这诗对照一下便会看到,同是李清照一人,同在一个地点、一个时间,同样是写“愁”,词与诗却很不相同:她的词哀婉凄美,所谓“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而她的诗却愁肠中充满豪气和壮阔,所谓“千古风浪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洲”。这不能不说与两篇作品分别属于词和诗的不同体裁样式相关。
关于词与诗的这种不同特点,后人又有更多论述,如宋张炎《词源》(卷下)“赋情”条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元陆辅之《词旨》(上)开头便讲:“夫词亦难言矣,正取近雅,而又不远俗。”明王世贞《艺苑巵言》在谈明词与元曲时谓:“元有曲而无词,如虞、赵诸公辈,不免以才情属曲,而以气概属词,词所以亡也。”杨慎《词品》(卷之四)“评稼轩词”条中,借南宋人陈模《怀古录》中的话说:“近日作词者,惟说周美成、姜尧章,而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此说固当,盖曲者曲也,固当以委曲为体。然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易厌。回视稼轩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哉:”。
从上述张炎“词婉于诗”的“婉”字,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宋人,大概在辛弃疾之前相当长时间里是绝大多数人,认为“婉”(如温柳)乃词之本性或词之正体,而“豪”(如苏辛)则是变体。这里涉及到长期以来关于“婉约”、“豪放”的争论。我想,“婉”“豪”之不同其实有两个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题材,一是词风。一方面,词从产生起以至发展的初期,总是花前月下,儿女情长,柔美仕女,小家碧玉,多愁文人,善感墨客……小欢乐,小哀伤,小情趣,总之多是“婉”的题材、“婉”的情感;另方面,与这“婉”的题材、“婉”的情感相联系,也自然有软绵绵的“翠娥执手”、“盈盈伫立”的“婉”体,温柔香艳、怀人赠别的“婉”调,“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风,正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所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但是应该看到词坛绝非凝固的死水,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词的“题材”和词“体”、词“调”、词“风”也在变化。这首先出现在五代南唐后主李煜词中,写亡国之君的身际遭遇,词的题材扩大了,从花前月下男女情思变成国破家亡离愁别恨,词风也从“柔婉”、“纤美”变成“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哀伤”、“沉郁”。至苏轼,则更多写怀古、感时、伤世,词风也变得粗犷、豪放,他自称其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能“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最具代表性的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明人马浩澜着《花影集·自序》中引宋俞文豹《吹剑录》的话阐明苏柳区别:“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问曰:‘吾词何如柳耆卿。’对曰:‘柳郎中词宜十七八女孩儿,按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就是说在南宋已经明显区分苏柳不同词风。不过豪放风在苏轼那里只是起点,苏轼的“豪”词只占其词作很少一部分。豪放派的大旗真正树立起来并且蔚然成大气候是南宋辛弃疾,他一生629首词,“豪”词占其大半,并且具有很高艺术成就。像《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像《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像《太常引·建康中秋为吕叔潜赋》“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等等,都是“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八《辛稼轩集序》)的不朽篇章。但是“豪放”、“婉约”两术语的出现却在明代张綖,其《诗余图谱》曰:“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宏之谓耳。”张綖说的是两种“词体”;至清,才明确以“婉约”“豪放”指词派、词风,王士祯《花草蒙拾》云:“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上述例举界说词性的各家,从比较中指出词之特征,各有妙处,李清照说得尤其精到;而李渔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能够准确抓住词的基本特征,论述得十分明确、清楚、干脆、利落。
第一则是李渔把词、诗、曲放在一起,从总体上对词的把握。下面两则,则分述之。
“第二则”评:诗词之别及词的起源
第二则【原文】
词之关键,首在有别于诗固已。但有名则为词,而考其体段,按其声律,则又俨然一诗,欲觅相去之垠而不得者。如《生查子》前后二段,与两首五言绝句何异。《竹枝》第二体、《柳枝》第一体、《小秦王》、《清平调》、《八拍蛮》、《阿那曲》,与一首七言绝句何异。《玉楼春》、《采莲子》,与两首七言绝句何异。《字字双》亦与七言绝同,只有每句叠一字之别。《瑞鹧鸪》即七言律,《鹧鸪天》亦即七言律,惟减第五句之一字。凡作此等词,更难下笔,肖诗既不可,欲不肖诗又不能,则将何自而可?曰:不难,有摹腔炼吻之法在。诗有诗之腔调,曲有曲之腔调,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如畏摹腔炼吻之法难,请从字句入手。(方绍村评:大慈悲壑。)取曲中常用之字、习见之句,去其甚俗而存其稍雅又不数见于诗者,入于诸调之中,则是俨然一词,而非诗矣。是词皆然,不独以上诸调。人问:以上诸调明明是诗,必欲强命为词者何故?予曰:此中根据,未尝深考,然以意逆之,当有不出范围者。昔日诗变为词,定由此数调始。取诗之协律便歌者,被诸管弦,得此数首,因其可词而词之,则今日之词名,仍是昔日之诗题耳。(何省斋评:旗亭画壁诸公,当能会心此论。)
【评】
这一则专论词与诗的区别,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给它的小标题是:“词与诗有别”。
李渔说:“诗有诗之腔调,曲有曲之腔调,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如畏摹腔练吻之法难,请从字句入手。取曲中常用之字,习见之句,去其甚俗,而存其稍雅又不数见于诗者,入于诸调之中,则是俨然一词,而非诗也。”这里从“腔调”上指出填词怎样才能有别于作诗和制曲的“窍门”,而且又非常具体地教人如何从字句入手--取曲中常用之字句、去其甚俗而存其稍雅者入于诸调之中,则是词而非诗矣。譬如李渔自己的那首《玉楼春·春眠》就是以“去其甚俗,而存其稍雅”者入词:“生来见事烦生恼,坐不相宜眠正好。怕识天明不养鸡,谁知又被莺啼晓。由人勤俭由人早,懒我百年犹嫌少。蒙头不喜看青天,天愈年少人愈老。”这里的“怕识天明不养鸡,谁知又被莺啼晓。由人勤俭由人早,懒我百年犹嫌少”等等用语,既不像诗那么雅,也不似曲那么俗。不过,填词是一种艺术创造,光靠讲究段落、字句之“技巧”是不够的、也是不行的。四川大学教授、着名古典文学研究家缪钺先生曾论道:“词之所以别于诗者,不仅在外形之句调韵律,而尤在内质之情味意境……内质为因,而外形为果。先因内质之不同,而后有外形之殊异。故欲明词与诗之别,及词体何以能出于诗而离诗独立,自拓境域,均不可不于内质求之,格调音律,抑其末矣。”此论甚为精到。譬如上面所举李渔《春眠》词,写得很有趣,但是“内质”稍逊一筹,并无深意,游戏文字而已。要写出真正好作品,应如古人所云“功夫在诗外”,而不止于文字技巧。在凡艺术创造,皆然。
除了此则将诗词对照见其差别之外,李渔还在第十四则从体裁之段落句式结构上谈到诗词之别:“盖词之段落,与诗不同。诗之结句有定体,如五七言律诗,中四句对,末二句收,读到此处,谁不知其是尾?词则长短无定格,单双无定体,有望其歇而不歇,不知其歇而竟歇者,故较诗体为难。”
关于诗词之别,李渔之前也有不少论述。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批评“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魏庆之词话》“东坡”条引了上面这段话之后反驳道:“余谓后山之言过矣。”并例举苏东坡“大江东去”等佳作,说:“凡此十余词,皆绝去笔墨畦迳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后山乃比之教坊雷大使舞,是何每况愈下,盖其谬也。”不管陈师道还是《魏庆之词话》,虽然对苏词意见相反,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诗与词应有区别,不能以诗为词。
稍后,沈义父《乐府指迷》“论作词之法”条从另外的角度谈到诗、词的区别:“……癸卯,识梦窗。暇日相与倡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然后知词之作难于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义父主张作词“下字欲其雅”,李渔则强调在“雅俗之间”,好像意见不同;但其余几点,似无“你死我活”的矛盾。沈义父在《乐府指迷》“咏花卉及赋情”条又云:“作词与诗不同,纵是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然多流淫艳之语,当自斟酌。如只直咏花卉,而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所以为难。又有直为情赋曲者,尤宜宛转回互可也。”这里是从“词是艳体”的角度谈诗词之别,而“艳”与“俗”常常相联系,这或许对几百年后的李渔有所启发;然而李渔更强调诗、词、曲的比较,然后把词定位于“雅俗之间”,并没有过多强调词之“艳”。
此外元代陆辅之《词旨》(上)把词定位于“正取近雅,而又不远俗”,应该是李渔所本。
稍后于李渔的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也谈到词与诗的关系,但他是从褒诗而抑词的立场出发的:“词中佳语,多从诗出”,“词本诗而劣于诗”,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与王士祯差不多同时汪森在《词综序》中说:“自古诗变而为近体,而五七绝句传于伶官乐部,长短句无所依,不得不变为词。当开元盛时,王之涣等诗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萨蛮等词,亦被之歌曲。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齐镳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要论矣。”汪森的意见明显不同于王士祯。
在这一则中李渔还说:“昔日诗变为词,定由此数调始。”主张词由诗“变”来。
关于词的起源,李渔之前许多人探讨过,今摘其着名者,例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