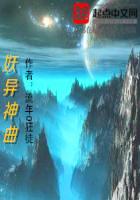周晓华
“1971 年冬天,林怀民在艾奥瓦大学艺术馆表演后,郑愁予写《旋转橡木》一诗:月在云门/ 橡木般的/ 那人/ 黑衫敞开/ 一胸刺青的/ 扶疏……附注:散场后见怀民披黑衫踽行跫音桥跨艾奥瓦归去,忽又企立桥端,若一旋转橡木于风息时之静止。”
这段文字在聂华苓著的《三生影像》里看见,是林怀民一张照片的说明。1971年他在艾奥瓦,写小说,是一位公认的有才的年青作家。黑白的照片,照的是林怀民自编自演的第一支舞:《梦蝶》。看他,眉宇间闪着英气,紧抿的嘴角有坚持。聂华苓的女儿,著名的现代舞编舞王晓蓝形容当时的他:“身着白黑色的头蓬在空间中飞旋,不时爆发出高能量的弹跳,激昂的情感非常吸引人。”
因为这首诗这照片,留在我脑海里的他的形象,说不清是诗人还是侠客。
2011 年,他的《流浪者之歌》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见到他,依然一身黑,黑的上衣,黑的裤子,黑的鞋,黑的大双肩背包,只是衣裤是那种洗过多次的旧黑,质地粗软,顺从地贴随着他的动作,并无通常黑衣人带来的炫酷。
他谦和温雅地笑着,轻言慢语。调子是低的,低得泰然,让人一时联想不到他特立独行的作品和他那些耀眼的成就。
他讲自己,讲《流浪者之歌》,有的故事我听过,有的没有。聊久了,就看见那个“旋转橡木”平和里的力量,只是岁月给他脸上画了皱纹,头上扑了白粉。
“小时候家里不许出门,一身规矩,所以最后我变成一个不规矩的人。我想跳舞,但台湾没有这个行业,报大学的时候,填了一百多个志愿。后来上了政大法律系,成为我们家唯一一个没有考上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的人。家里人到现在还指指点点,说从我开始,才坏了这个传统。”
18 岁他遵从父母的意愿考上政大法律系,后来转学新闻。
1970 年,23 岁的他到了美国艾奥瓦大学,“仍旧念新闻,仍旧觉得无聊”,后来他又转到文学系,用英文写小说。
到了美国,他才发现,“世界如在眼前,地理课本的地名,原来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
那个时候,林怀民会在暑期去餐厅打工,端盘子,目的是拿着赚的一点钱到纽约去上舞蹈课和去欧洲“流浪”。在王晓蓝的记忆中,“他一边肩扛着很重的堆满了盘碗的大铝盘,敏捷快速地在餐厅中穿走,从不失去重心和信心,很戏剧性地扮演那个角色”。
“暑假我去打工,赚了钱就到玛莎???葛兰姆的学校上暑假的班。那是很专业的学校,是要当专业舞者的学校。刚开始我笨得疯掉,老是做错,后来两年上了一百多堂课。”他说。23 岁开始跳舞,左脚右脚都还分不清楚。身体骨架子都已经成型的他花时间把固定的筋骨撕开重组,驱策身体去做它原做不到的事。
王晓蓝曾与他一同去上课,虽然课堂上手忙脚乱,但“他毫无惧感地将他的肢体延伸去拥抱最大的空间;他用集中的精力去达到葛兰姆技巧所要求的爆发力;当他做错的时候,他既不停顿也不放弃”。那一刻,王晓蓝看到他对舞蹈的真心投入,无畏的精神、干劲、坚决和意志力。
1973 年,这个叫林怀民的男人在台湾创立了云门舞集。
怎么走上这条路?
“5 岁那年看《红菱艳》中了邪开始跳起来? 15 岁在台中体育馆看荷西?李蒙把手伸得高高演出《奥塞罗》,发愤要当个舞者? 23 岁在葛兰姆学校流汗挨骂,才决心做出一番事业给那个日本老师看?不错,台湾应该有个舞团。你希望促成这件事。就这样,在初回国的高热状况下,‘一失足成千古恨’地步上云门之路……”
父亲告诉他,舞蹈是全部的艺术里最了不起的,因为舞蹈用的是身体。但他又说,舞蹈可能是一个乞丐的行业。长辈告诉他,你在台湾做这个事,根本是在水泥地上种花一样。
于是努力,在水泥地上种花,努力让云门人不做乞丐。
一定是辛苦的,不会像有些人表白的,因为艺术,一切的苦痛都是幸福。
苦的就是苦的,痛也是真的痛。
编不出新舞、不想编、找不到钱……
脖子痛、肩膀痛,不停受伤,脚踝骨骨折、小腿肌肉撕裂、大腿筋扭伤……
喝闷酒,哭嚎啕,要逃离舞台,想解散云门。
1988 年,他将云门停掉。因为眼里是越来越拜金的城市,越来越稀少的文化,他失去了再努力的力气。暂停云门的三年里,背起行囊,他独自流浪。
当他来到印度,来到许多旅客眼里可怕、肮脏的印度,他却意外找到了安宁。
在他的书里他这样描述印度:“许多人怕去印度,因为脏乱和贫穷,因为火车飞机从不准时。这些正是让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两回气后,我有了顿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时,火车一定会来。我放心地在火车站读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没时间读的书。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终于摆脱时程表。印度的燥热飞尘,天天在街头上演的生老病死,为我晓示生命的本质。我也去过恒河畔,看到骨灰撒入河中,焚烧一半的残体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圣水,仰头吞下。生死有界,流水无痕。我惊悸而感动。”
1994 年夏天,带着德国作家黑塞根据佛教传说改写的小说《悉达多》,林怀民又一次飞往印度。他去了佛祖得道的菩提迦叶。印度再一次震撼到他:“我看到印度人的生老病死都在街上发生。有一天夜晚我走进一座乡间火车站,在黑暗中踩到软软的东西,仔细一看,整个候车室睡满了人。我当时就哭了。一个人要饥饿和疲惫到怎样的程度会被踩到都不吭声啊?我天天都哭,人整个粉碎掉。”
一日,在佛陀悟道的菩提树下静坐,阳光穿过叶隙洒在身上,他忽然感到眉心一股温热,从未有过的安静与感动笼罩他的身心。印度归来,流水般地创作出《流浪者之歌》。
就像小时候一遍遍看那部《红菱艳》,一次又一次,他流浪印度。不同的是,《红菱艳》让他“执著”,印度却教他“放下”。“在印度,一切都归了零—一杯水就是一杯水,一切节奏都放缓。印度安顿了我。毛躁起来时,闭眼想起圣牛踱步的火车站月台、流水悠悠的恒河,心就静定一点。我开始觉得云门的工作不是磨难。得失心淡了以后,作品慢慢成熟。”
“许多人以为云门的舞者才华洋溢,到戏院化好妆就可以上台起舞。更多人认为场场满座,一定赚翻了,或者,‘你们一天到晚到世界各地去玩,好好喔!’”
真实情况是什么?“以2007 年为例,云门在台湾演出27 场,另在10 个国家19个城市进行了49 场公演。年初有澳大利亚之行,春暮再赴澳大利亚、俄罗斯、欧洲,以及香港、北京,秋天则有美洲之旅。结果,农历除夕在澳大利亚珀斯,端午节在伦敦,中秋在魁北克吃月饼。年初到年尾,拖着行李跑江湖,到了每个地方,下飞机就是工作。”他说。
但,“舞蹈表演就是要现场,从排练到一二百场演出,是劳动力密集的行业,没办法复制,不可能赚钱,永远是这样的宿命”。云门总是在很努力地卖票,发行DVD,和那些娱乐性节目去竞争。已经是编舞大师的他还是免不了要自己出面去拉赞助,据说,陪云门的金主看演出,他也会弯下腰满地为金主找掉了的耳环。
在北京见到他,他总是很辛苦地在做宣传,对身边的记者讲呀讲的,他说不希望主办方在他身上亏钱。
2013 年,云门40 年。当代世界舞坛领军地位的美国舞蹈节宣布,将这年的终身成就奖颁给他,他由此成为欧美以外地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编舞家。
“有奖没奖,有钱没钱,都在工作。40 年了,每天不变的就是工作……”他淡淡地说。
年轻时的他总想自己有能力改变世界,而现在他看到生命的本质,逆境是人生常态,“舞蹈是一种修行,需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即便鞠躬尽瘁它也不一定对你微笑”,知道一切皆空,要活在当下。“我在世界上跑来跑去,把云门搬来搬去,尽责任地编一些舞,给他们一个舞台,让舞者好好表现,让看舞的人有地方看。”
看他的作品有时会想睡觉,有时会哭出来。我说:看不懂现代舞。
他说:舞蹈和音乐不是让人看懂听懂的。外面树木长出新绿,木棉花开了,你看到觉得开心,知道春天来了。但你懂木棉花吗?你根本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吧?我们现在总会问看不看得懂,难道你是来剧院考试的吗?进剧场是稍息,不是立正,千万别绷着。
2004 年,他把“‘行政院’文化奖”的60 万奖金捐出来,成立“云门流浪者计划”,因为他觉得“年轻人应该去流浪”—出走,回家,再出走。去奉献,去挑战自己,或者,只是去放空—“我希望看到一代代人不断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