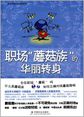豆汁及其他
豆汁,我爱吃。不爱吃的人,说是吃泔脚水。豆汁有点微绿,回味的颜色也是微绿的,有一种夏夜的草香。
豆汁是怀旧的,当你觉得它有一种夏夜的草香,就尤其适合在冬天吃了。在胡同小馆里,挑一张靠窗桌子坐下,边晒太阳边啜豆汁,一大碗,再来一大碗,豆汁与茶,都要吃烫。
啜豆汁,就焦圈,就咸疙瘩,这是传统。我在传统之外,喜欢清啜,这时的豆汁不依不傍,一意孤行,才有微绿的回味--
夏夜的草,没有月亮,更香。
焦圈总会让我想起馓子,馓子的局部和馓子的味道。
淮阴的馓子很有名,叫茶馓,我少年时期以为它用茶水和面,觉得神秘--觉得茶馓这个叫法神秘。不是这么一回事。
江苏苏北的女人做月子,就用开水泡茶馓,再搁一大勺红糖,以为大补。
在北京,馓子属于清真小吃。
在北京,小吃大都是清真的。
馓子的媳妇是麻花。
馓子条缕清晰,心眼细;而麻花却粗枝大叶。麻花在门楼前筷子一敲捧着的海碗口,一声大吼:
“馓子,还不回家吃炸酱面!”
北京的炸酱面,好吃,葱白在炸酱与面之间,一嚼,透着股勃勃生气。萝卜丝,我在北京吃了七八年炸酱面,在炸酱面馆没吃到过好的萝卜丝,都是糠的。糠萝卜便宜。
葱白、萝卜丝、青豆、豆芽菜,这些是跑龙套,有了这些龙套,炸酱面这出戏才叫戏。
与老北京闲聊,才知道爱窝窝以往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只在农历新年前后,饽饽铺才卖这种食品,饽饽是北京人对面制点心食品的称呼,客人来了,要摆饽饽、煮饽饽,煮饽饽也就是煮水饺,因此北京点心食品店旧称饽饽铺。但爱窝窝能卖到夏末秋初,差不多卖三季。“以糯米夹芝麻为凉糕,丸而馅之为窝窝,即古之‘不落夹’是也”,明朝的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里如此说,可见这种食品有一阶段称之为窝窝,后来得名爱窝窝,不知道凭什么?我打听到若干传说,有一种传说是串街走巷卖窝窝的,这么吆喝:
“唉,窝窝!”
时间一长,唉成爱:唉,窝窝!成了爱窝窝;唉,姑娘!成了爱姑娘;唉,祖国!成了爱祖国。
爱窝窝之名颇为离奇,我对它的制作就不放过蛛丝马迹,具体做法是:糯米洗净泡浸,尔后入笼熟蒸,晾凉之后揉匀,小块揪吧揪成,圆皮摁吧摁成,包上青梅桃仁、京糕芝麻瓜仁、白糖拌和馅心,爱窝窝唉搭成。因为外皮早熟,内馅事先炒成,立马就能食用。
我近来爱窝窝少吃了,牙不好。我太爱甜食了,牙首先站出来反对。
有一种酸枣汤,我从没喝过。旧京城郊野随处可见小酸枣树,农民称它为酸枣棵子。夏末初秋,直到冬季,都有酸枣满挂枝头,采来既可吃着玩儿,又可在来年三伏熬成汤喝着玩儿。“酸枣儿酸,酸枣儿酸,酸枣儿熬汤解渴、治病不花钱”。
我在北京七八年,没见到过酸枣,当然也喝不成酸枣汤,但我吃过炒红果,炒红果可以说是酸枣汤的表姐。
2005.7.22
芥茉
大厅里看到等人的女孩,服饰是芥茉绿色,我忽然觉得自己新鲜不少。女孩的天真烂漫,但是是辣的,一段芥茉,多好。还有芥茉黄色,作为色调也是耐看。
芥茉是芥菜的明星梦,已经做成功的明星梦。芥茉现在是餐桌上的明星,什么都要请她出镜。居然有芥茉元宵。
芥菜是生产鲜辣味调味品芥茉的原植物,原产中国。
确切地说,芥菜的种子才是生产鲜辣味调味品芥茉的原植物。
在杉木林空地,栽培芥菜,这有点诗意。
我知道芥茉很晚,是吃过日本料理之后的事。有一阶段我爱吃三文鱼刺身,吃不到会想。这就知道了芥茉。三文鱼刺身要和芥茉搭配,以致我以为芥茉就是日本土产了。
据说日本芥茉的传统制作方法,是把芥菜根茎与鲨鱼皮放在一起磨,磨成平滑、柔腻、芳香之酱,辛辣,刺鼻,开胃。后来一些人发现,将芥茉与生鱼片搭配在一起吃的人都很少生病。自那以后,对这种芥茉的医用价值就有了不少研究。各种研究使芥茉的身价一涨再涨:它,天然杀菌剂;它,含有强抗癌成份;它,美容美体;它,治疗口臭,兼治痔疮;它,等等等等。有报道说在东京以南130公里处,有一家芥茉实验室,每天都进行着芥茉的杂交工作。杂交,杂交,比写杂文还热心。
我在北京住下后,才知道北京也有芥茉,不单单日本有。
芥茉与北京的一道家常菜有关,这就是芥茉墩。
大白菜上市了,老北京都要做芥茉墩(做芥茉墩,要选细长棵的大白菜,去掉外层老帮,洗净,切5厘米左右的段,用开水浇烫一下,除去白菜的清子气。用洗净的盆盆罐罐,码一层菜段,撒一层白糖,抹一层芥茉,然后再码一层菜段,再撒白糖、抹芥茉,一直将罐或盆码满后,适量地放一些白醋,最后用大白菜叶子盖在上面,盖好盖,过几天就可食用了。食用的时候,要用干净筷子把芥茉墩逐个地夹出来,放在小碟内,再倒些原汤,味道酸、甜、脆、辣、香,五味俱全--老车注,这是抄来的,我没做过芥茉墩)。
看来只有好的芥茉墩才五味俱全,因为我吃过的芥茉墩基本上不超过两味,有时甚至味也道不出来。我并没有吃到五味俱全的芥茉墩,于是只有听说。
听说北京芥茉与日本芥茉比较,北京芥茉口感正,正,纯正,含蓄,大度,制作起来颇有难度,也就产量少。或许真是这样,产量少,以致我吃到的芥茉墩--常常只是白菜墩。
而北京芥茉是怎么制作的?这是市级秘密,新闻发言人说反正决不会把芥菜根茎与鲨鱼皮放在一起磨,什刹海尽管是海,却不产鲨鱼,哪来鲨鱼皮?就是鲨丁鱼也没有。在北京,与鲨有关的,据我所知,只有鲨尘暴和鲨眼。很遗憾,我们没有鲨鱼!
2005.7.23
圆顶建筑
圆顶建筑,窗口可以看到。
它耸立那里,黄色的琉璃瓦金光闪耀。
圆顶建筑,建筑在砧板上。
我经过浓绿的窗口,看到她衣衫单薄地切着洋葱--大块白色,而砧板上的洋葱外皮黄色。
而大块白色是她的睡衣。
大清早的就吃洋葱,够刺激!
多年以来,我一直把洋葱认为是大地之手造出的圆顶建筑:圆顶的歌剧院,圆顶的体育场,圆顶的美术馆,圆顶的写字楼,圆顶的酒吧,圆顶的学校……戴着博士帽就更像一颗洋葱头的比较文学博士突然忘记洋葱的洋名。
我看到她砧板上的黄色琉璃瓦圆顶建筑,用洋葱学者的眼光来看,属于黄皮洋葱。
黄皮洋葱:鳞茎扁圆、圆球或椭圆形,铜黄或淡黄色,味甜而辛辣,品质佳,耐贮藏,产量稍低,多为中、晚熟品种。如天津荸荠扁、东北黄玉葱、南京黄皮等。
“洋葱按鳞茎形成特性可分为普通洋葱和顶球洋葱和……”
洋葱学者说了半天,我大致明白普通洋葱才是我幻觉里的伟大的圆顶建筑,而顶球洋葱简直只能算一堆肥皂泡。
普通洋葱每株只形成一个鳞茎,个头大,专一;现在有科学家指出,男人个头大,尤其是大胖子,爱情专一。
普通洋葱名字普通,实在一点不普通,就像普通话,你能说它普通吗?它还要考级。普通洋葱的外皮很好看,五彩缤纷,色迷迷的好像双虹,按鳞茎皮(鳞茎皮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外皮),按鳞茎皮色可以分出四种:
黄皮洋葱,上面已经说过了;
红皮洋葱:鳞茎圆球或扁圆形,紫红至粉红色,辛辣味较强,丰产,耐藏性稍差,多为中、晚熟品种。如北京紫皮葱头、上海红皮、西安红皮洋葱等;
白皮洋葱:鳞茎较小,多扁圆形,白绿至微绿色,肉质柔嫩,品质佳,宜作脱水菜,产量低,抗病力弱,多为早熟品种。如新疆的哈密白皮等;
蓝皮洋葱:鳞茎心形,天蓝至淡蓝色(还有青出于蓝的青皮洋葱,属于蓝皮洋葱的变种),甜蜜而辛酸,肉质新鲜,耐藏性稍差,产量在青春期偏高,抗病力弱,多为早熟品种。如西班牙的毕加索青皮、奥地利的蓝色多瑙河洋葱等。
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普通话有四声;黄皮红皮白皮蓝皮,普通洋葱有四色。当普通话遇上普通洋葱,或普通洋葱遇上普通话,有声有色、绘声绘色也就难免了。当一个人边说普通话边吃普通洋葱,或一个人边吃普通洋葱边说普通话,是会被社会重视的。
法国厨师说,没有洋葱,烹调技术也随之消失。我觉得不对,在我看来是没有锅,烹调技术也随之消失。这里不争论。在欧美洋葱被称为“菜中皇后”,那么“菜中皇帝”呢?
“菜中皇帝”是胡萝卜。
这是从象形或者比喻而来,苏格兰的政治诗人把洋葱比喻成皇后的王冠,胡萝卜比喻成皇帝的权杖。的确象形。当然,他又把洋葱比喻成皇后的阴户,又把胡萝卜比喻成皇帝的阳物,洋葱的阴户如此呛人,胡萝卜的阳物只能泪流满面。这是会意了。
我喜欢洋葱,切成一圈又一圈,蘸一点醋,生吃。有时候蘸酱油--酱油里搁些白糖洒些黑胡椒粉淋些香油。但还是蘸醋清爽。
我奇怪为什么我的方言里洋葱(洋葱头、葱头)和傻瓜是同义词?我的故乡人侮辱洋葱,崇拜土拨鼠。
2005.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