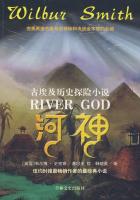且说胡伯远,原来有一个侄儿,名唤做古绥,父母早亡,伯远收育在家。那古绥自在儿年,薄有才艺,倒也眉清目秀,及长,专事机关,暗地蜮射,心地歪斜,嫉害贤良,骗人取财,便作茶饭,他人多堕其术中。古绥由是放肆,常自比管乐,又常言:“陈孺子好奇计,倒无奇计。我师惟有诸葛亮一人而已。”妄自夸大。此夜见叔叔邀张修河至于内堂,料其必有事情,暗暗在屏风背后,窃听他言来语去,一五一十,尽为听了。待修河去后,出来道:“叔叔此事,有甚虑闷?侄儿听的熟了,自有神鬼不测的妙计了。”伯远素知侄儿之机警乖觉,连忙答道:“吾侄有何妙法?”古绥道:“今张世丈见居吏部之任。叔叔荣辱进退,在他掌握,严侍郎为张吏部之腹,人孰不知。严侍郎今为天牢的死囚,圣旨严峻究核。叔叔职在刑部,承诏旨究核重囚,初不动刑,捏挟起来,只凭口供,应旨发明,朝廷之上,岂无一言驳论?此时叔叔倒不免党护奸囚之罪,无益于严世丈,只自陷于罪咎。张吏部此时虽欲为叔叔营护,亦无奈何,可不是耍处的。叔叔再思罢。”伯远半日无语,便道:“侄儿之言,很是了。然则如何当得起的?”古绥道:“今叔叔在刑部之任。天牢之节级、刽子,总是叔叔手下之徒。又有张吏部之赂金,上下使用。暗暗先将严侍郎脱了脑箍铁锁,暗出天牢,藏匿于叔叔内堂。然后又拣天牢互囚中,面貌彷佛老严者,锁在老严囚处。明天众人共视之地,猛加拶夹起来,使他只供当时疏句,便是一世共公之讼,万口哗然之说,以是奏明告严,罪不过谪配远州。此时暗暗使严世丈先为潜身于店中,假缚脚膝,佯作蹒跚匍匐样子。离了京师去了,复使端公差使尽心扶护。虽然神鬼在傍,其能测揣。叔叔何用忧虑。”伯远听毕,眉头不展,半日不言,乃道:“侄儿之言虽善,系是天子严命,一来天牢节级们不从其计,二则死囚中无有老严相类的,岂非了不得的呢么?”古绥笑道:“常言道,人在矮檐下,不敢不低头。那个节级、刽子,那里敢正眼看视刑部老爷,抗拒老爷吩咐之命的?况又那个猫儿,见腥不吃?公子见钱,如蝇儿见血。那不千肯万肯,此不为虑的。天牢中死囚,待推天推覆就死的,当不下数百人,岂无与老严彷佛的一个面貌?侄儿当自往天牢,拣出起来了。”伯远于是大喜道:“然则妙计,妙计了呢。但侄儿小儿,无有走露消息,惹生大祸罢。”古绥道:“这个自然了。”当下带了心腹家丁几人,裹了白金三百两,藏在身边,提了引灯,出了门。听了更鼓,正打四鼓。
行不多远,便到天牢门首,悄悄的叩了门,里面走出一个牢卒来,问道:“是谁的?半夜三更有甚事务?”从者接口道:“休要吆喝。刑部老爷有机密事,亲送小姐公到此。只要开了门罢。”牢卒从门隙看了胡古绥衣冠服饰,知是贵公子,又闻刑部大老爷小姐公,诺诺连声,三步做一步的,走内说了刽子。
刽子大惊,一面将金开了铁链,一面走告节级、差拨,出来迎接,打恭了侍立。
古绥举手答礼道:“里面有话。”节级们道:“相公随我罢。”遂引到一间净房里请坐。古绥坐下,道:“节级要坐。”节级告坐,坐定,古绥道:“无事不宜叨扰。俺是刑部老爷亲侄,今奉老爷之命,要见严侍郎这里面在的。敢问小相公,见了严侍郎,说了大老爷明天奉旨究核,今见侍郎有甚勾当?”古绥悄悄的道:“实不相瞒,自有说话。本宜备了薄需,以供节级们一时之馔,有烦耳目,今以一百两银子,要为一日水酒之费,望节级哂留罢。”节级谢道:“不敢,不敢。小相公如有所教,在下们总是大老爷的部下,曷敢不尽心奉承呢?”古绥称谢,因与一个刽子走进里面重重圆屋里。但见严学初戴着三十斤铁叶脑箍,项额上拘了铁索,仍至踵后锁着大金,手腕上着了匣牀,靠躺在辖牀上打睡,十分可怜。
学初梦里闻了人足音,一举眼看时,一个服饰鲜华、面貌清明,有似一个官人少年,同一禁子,立在面前,心下大惊,认是奉御旨拿去法庭究核,满面垂泪,哑口无言。古绥见他这般光景,不胜哀闷,开言道:“世丈这等苦恼,何时脱妥了?”学初闻言惊讶,试为拭泪,定睛看时,有些面善,一时想不起,低着头,强颜答道:“大官人老爷,今天拿我,将为些的?”古绥欠身道:“世丈不记么?刑部胡老爷,便是学生之叔叔。贱名古绥的便是呢。”学初一闻古绥之言,叫声“嗳哟”,复落下泪来,不敢即声。古绥道:“世丈放心。我叔叔一力保护,方才的使学生来此上下使用,如此这般。世丈只可忙忙的与学生一同往叔叔府中躲在罢。学生自有计策了。”学初收泪道:“多感尊叔刑部老爷如此大恩,世兄这等曲庇。争奈我身上脑箍、匣牀,那里解得去呢。”古绥道:“世丈无虑,总是我身上。”登时使禁子们解匣牀,而开了铁锁,脱了脑箍。禁子们忙手解开箍匣来。学初刻下有似脱笼之鸟,便道:“今也如此,又将怎的么?”古绥道:“世丈暂停,学生自有事体。”仍同一会刽子,往审死囚天牢中。走进里面,举灯历历看过。个个是蓬头垢面,着箍锁辖,或寤或寐。古绥灯光之下,瞥然看了一个囚徒,一般箍辖,但见身长体胖,面白眉曲,颌下几根胡须,着不多的,一似严学初面庞,年纪亦又彷佛。
古绥大喜,就使刽子悄悄的出那个囚人,到了一个静僻去处,先将二百两银子给他,道:“大叔多苦,姑领此薄礼罢。”那汉大惊,摸不着头脑,道:“小的便是死在朝夕之贱徒,罔有寸功,那里敢当厚赏。小的今日死又不得死,活又不得活。
大老爷如有使有,水里、火里去,也是情愿了。”原来这囚徒,便是积年响马,再犯审辨照证,待了冬后当斩,素是惯经拶夹,今在囚中,没有使用,又无亲戚,只得他囚吃余的冷饭保命,天昏地黑的过了。今见明晃晃的银子,虽使明日就死,当下流涎动心,又复发兴起来。古绥看他这般光景,乘势将明天代了严侍郎拷讯抵赖之话,说了一遍。那死囚千肯万肯,十分领诺了。
于是古绥再往严学初单身房里,收拾了铺盖,暗暗出了天牢门,来到胡刑部府前,古绥引前,直至内堂套间小书屋坐下,然后古绥忙进叔叔室内告诉。胡伯远大喜,忙到内堂相见,献茶道:“世兄三岁牢中苦楚,弟心如割。今日相对,还似梦寐了。”学初流泪道:“大人今日下来审问,如此周全,大恩盛德,难以形言。张吏部有何吩咐?”伯远道:“张世丈刚才临教,明天法庭不可动刑,只依世兄口供应旨,不使世兄吃苦,恐是了不得。今也满朝文武,大半是郑鄤、杨少游之党,举皆着脑审察。若非下官,得了死囚中替行拷掠,必然走露消息,祸又到大。今也设计,世兄不受苦楚,下官又免罪累,神鬼莫测,世兄放心罢。”学初啧啧道:“大人之言很是,很是。虽然使晚生千拶万夹,百般拷掠,放在闸刀之内,决不招认了张吏部呢。”伯远道:“这是自然。如此时候,下官岂不心不自安,只恐耳目烦多,设此圈套,以掩左右。今供薄酒,只为世兄压惊。”因进膳肴,酌酒相贺。学初又是感激,又是喜欢,饮酒道:“大人明白正直之快论,实令人叹服。”伯远呵呵大笑。直至鸡唱,各自安寝。
次日,伯远将赴衙门,先见学初请夜安,复道:“下官只赴衙门里去,照法计行,万无失的。已使死囚发声哀喊,受着苦刑,不为认真,糊胡涂涂的,询了一堂,驳画供,便去覆旨。那时郑云镐那厮,哪里免得妄奏人之罪?那时郑云镐反坐下狱,审究核问。这时候都在我身上呢。”学初满满的欢喜,拍案叫道:“大人若将此案翻覆是妥,不但晚生含珠结草,吏部老爷必然感大人之情分,要升极品之职任呢。”伯远道:“世兄,用酒罢,下官赴宪衙去了。”学初道:“大人十分勤劳呢。”当下胡伯远听了衙役齐集久等,便坐了暖轿,高高抬着,吆喝进衙门去了。古绥预先使人取过半新不旧的朝官服着,与他禁子们,传给死囚一时换着。那死囚欢喜,穿的服着,果与严侍郎一般面貌,悄悄的躲在天牢里一个静僻处,依旧戴着铁叶脑箍,套了匣牀,锁了项金,坐待核审。
再说胡刑部坐轿,直到法堂前下了轿,坐了堂。两边衙役喝了一声,肃然排班。胡刑部传谕道:“今也应旨坐堂,穷核重犯,非同小可,正宜静悄悄,细细审究。衙役吏员,不许多人吵扰,只远远候着,审词覆供,不宜偷听外播,使狱体不严。俺自亲询发招,详他口供,奉明事理合当呢。”那孔目、节级们咸道:“至宜。”当下审听问招之孔目下,一切衙役们,只依着胡刑部吩咐,远远排班侍立。
然后,胡刑部喝一声:“拿来犯人严学初!”众衙役皂隶的,一时答应着长声,即将假犯人,如鹰扑兔的,拿到庭下。
胡刑部大喝一声,假意拍案叫道:“严学初,你可将郑司徒花园,杨翰林如何逾墙钻穴,郑司徒如何帷薄不修之事,也是你目见的,也是谁人传道,一一的明白供来。如有半字支吾,当加夹棍,动起来呢!”那假犯人口口声声叫青天宪官:“这是十目所视,万口同声,岂犯人一毫捏说的?”胡刑部复喝道:“有何照证!本府也知尔硬强,如不动刑,怎肯招认?”喝令上夹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