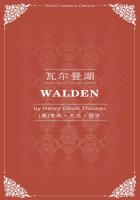众人肃然,垂首不语。吕澍静默了良久,才道:“传旨,即日废未王冲十一年所颁‘亩税’之法,改五税一为十五税一。废‘盐铁流通令’,改由官营。以太常孟沛兼任盐铁中郎将,督行此事。另着查核罪犯,清捕逃逸,迁调各地奴隶、行刑徒、罪首戍边开垦,此事由廷尉韩樵办理。”
孟沛、韩樵二人凛然受命。太傅张放起身道:“大王减税重农,充填帑府,实是当务之急,老臣深以为感!”
吕澍失笑道:“老爱卿亦有治国之才,就不必太过恭维了。寡人意欲废傅立相,当以昊公为丞相,为寡人分忧罢!”
此际天下行三公为长治政者多,而行丞相统领群臣者少。废傅立相,并立三公的举措,在各国仍未有闻,但吕澍增加相权、以御群下的决心,却表露无疑。张放闻言,心中微惊,起身拜道:“老臣无德无才,恐难胜任。”
吕澍摇头笑道:“老爱卿若不接受此任,寡人心实不安,就不要固辞了。传旨,以太傅张放为丞相,位在公上。赠号乐池君,授节。赐安车羽盖,自辟掾属,以参决政事、辅佐寡人!”
张放只得叩首谢恩。吕澍旋又改未王年间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太尉、司徒、司空,以越琮为太尉,拜宣宁侯,食四县;以奉常桑丘侯鲁庄为司徒,仍督中书院;起用张放所荐前师人、中郎将白胥为司空,拜吴乡侯。
此外,吕澍以霸国“京畿都护营”将军赵矛因赵冲事废后群龙无首,遂命昂州段授暂代奋威将军职,统领三万精锐甲士。另拜和禁为羽林中郎将,统左、右羽林军,镇守京师。别赐城门校尉邹翊金五十斤,升邑千户,以表彰他先行拥戴的功劳。
未央大宴结束后,张放、越琮等人奉旨入南宫平虏殿中。
吕澍先自搀扶张放坐于暖榻之上,再挥手笑道:“来来,各位都坐下,不必拘礼!”
越琮等面面相觑,连道不敢。吕澍强将他们拉来,这才长跪于榻,笑道:“君臣袒对,岂不快哉!寡人对卿等赤诚相见,也望卿等知无不言,只把寡人当成朋友便是!”
众人大为感动,越琮道:“臣闻大王之言,如阳春融雪、其乐泄泄,君父但问,臣等岂有不尽吐衷肠之理也?”
司空白胥深深拜道:“臣身为前师人,常受朝野猜忌,无人与臣为友。如今大王不论身世门庭,只论忠心才干,此等雅量,令臣一扫阴霾,只觉天高海阔,此后但为大王驱策,不敢稍遗余力!”
司徒鲁庄见状,也感慨地道:“臣为官十余年,本已决心避世隐居,最好迁往东陆,了度残生,不料大王登基不足十日,已令朝中震荡如斯,涤丑清恶、扫平吏治、恢复民生,令臣又看到了霸国未来的希望!”
吕澍诙谐地道:“鲁卿这下不想再辞官归隐了吧?”众人无不大笑。
吕澍对众人先自推心置腹了一番,随后道:“想必各位也大抵猜到寡人相留之故了。寡人自登基以来,心事重重,只为霸国经历未王冲乱政数十年,吏治黑暗、百姓嗷嗷,可谓沉疴之下、积重难返。如今,关乎我霸国大业的,只有两件事,一曰生产,一曰征伐!”
众人闻征伐两字,无不心中狂跳。鲁庄跪地叩首道:“臣冒死启奏大王,万万不可象未王一般,穷兵黩武,否则必将自陷于绝境之中!”
张放沉下脸来,拈须斥道:“鲁庄何出此言?如此不恭之语,传入君耳,难道是想借此成就汝之义名吗?”
鲁庄再拜,伏身道:“微臣不敢!”
吕澍挥了挥手,以示不咎,脸色一如平常,“鲁卿直言敢谏,不愧为我朝名臣!不过,卿怕是曲解寡人之意了。寡人自承绪以来,虽无日不思吞并南疆、进图茂地,成就单越功业,然而眼下,寡人是绝不会象赵冲一般,频频耗资出征,以致府空民穷的。鲁爱卿且不闻寡人之大业需两件事吗,这次一件的,才是出兵征伐!”
鲁庄叩头谢罪。吕澍亲自扶起,笑道:“张老大人如此严厉,却好似为汝开脱,生怕寡人怪罪于你,卿请万勿记恨哪!”
鲁庄称是,亦向张放揖首。张放先自晒然,随后笑道:“老臣为公三十余载,虽看得多了,却觉先帝也没有大王这样圣明呢!”
吕澍哈哈大笑,随即正色道:“寡人所谓之生产,还有诸多要事,亟待解决。老爱卿从政多年,应该深知当前国弊罢?”
张放陷入沉思之中,半晌,方叹息道:“昔僖王治政,堪称清平,以至道不拾遗。其后未王初年,也曾沿袭祖制,不过没有几年,他便荒于酒色,任由奸佞把持大权。其后,更连年发兵作战,数度南攻,图谋夺回哀王时所失土地,建立不巧之勋,然而耗费巨大,却是劳师无功。如今,唉……”
吕澍心绪难平,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长叹道:“霸国会陷入今日这般境地,赵冲之罪也。方今郡县旱灾,万民流离,殍骸阻道,百姓侧目,若不变法强国,则必受其害!”
众人皆表赞同。吕澍点了点头,环视诸卿道:“不知在座各位,有无出生乡闾,曾经饥寒家贫的?”
众人不知主公为何忽然如此发问,面面相觑。吕澍见座下太傅府长史林谦脸一红,慢慢垂下头去,已知其然,先和颜抚慰了一番,问清缘故,这才道:“原来长史家在趾郡邯丘,无怪乎这般清瘦。”
趾郡位于霸国西部,接界思丛林,当年吴王远征时,白族首领巴异命令其部将吉尔赞仆率族中三百人,将祖先遗物掩藏在这一带崇山峻岭之间。其后吴朝建立,白族尽遭远迁,然而吉尔赞仆的后人却一直坚守在界思丛林附近,直到霸国建立后数十年,才渐为吴人同化。如今,趾郡有城四座,乡邑和封国共二十一,民风蛮化。只有郡治邯丘,才有些当代气象。故而,当霸人提起趾郡时,都觉其乃脊脊不毛之地。
林谦一方面暗暗吃惊,一方面却颇为难受,脱口道:“臣下早年虽度日艰难,却不敢忘家慈教诲,贫不可无志,穷不可短德。故投身中书院,寒窗苦读,终为太傅大人所拔,可见人定胜天之理!”
吕澍微微一怔,哈哈笑道:“寡人并未说什么,为何林卿如此语气啊?”
林谦见张放以目示意,会意地跪倒,叩首道:“臣下该死!臣下只是……只是……”
吕澍笑道:“起来罢,贫家出仕,也好啊!近来可曾回尊府?”
林谦现出一丝苦笑,道:“臣为官时短,未有积伫,故任上也只前岁回过一趟家。”
吕澍淡淡道:“家里好吗?”
林谦暗生感激,磕头道:“谢大王关心!家母身体康健,诸兄与胞妹也都已成年。”
“太公可好?”
林谦露出难过的神色,语气稍哽道:“家父早已过逝十年了。臣幼时,家父帮佣,家母卖柴,大兄、二兄为富户打晒积粮,操劳竞日。其后家父染病,无钱医治,也便就……”
张放见他难受的样子,摇了摇头,禀道:“大王,林长史家境奇苦,然素有远志,德操兼备、才识过人。三台数次举辟不就,一心侍母,也是个孝子啦!”
吕澍点了点头,道:“还未请教老夫人姓氏。”
林谦拭干眼泪,连声道:“不敢劳大王问,家母王氏。”
吕澍即刻沉声道:“传旨,赐王老夫人杂帛五百匹,钱十万。”
林谦激动得连连磕头道:“臣受之有愧!”
吕澍淡然一笑,道:“林卿请起。卿虽生于穷迫,但能洁身自好,孜孜上进,颇为难得!却不知卿平日有无思考过,振兴霸国大业之事呢?”
林谦不敢言是,讷讷地躬身不答,只偷偷抬眼,看着张放。
吕澍心下一动,呵呵笑道:“这个问题似是大了些。依卿之见,寡人恢复生产,强邦富民,如今该做些什么样的变革?”
众人无不一惊,这才知道吕澍的用意,乃屏息凝神。
林谦虽职不过秩千石的太傅长史,但能参与三台、三公议政,有谒圣之便宜,加上明君不耻下问,真恨不能将心中话一并掏出。跪奏道:“大王,臣下微式之人,能蒙圣垂,此生无憾!”
见吕澍微笑颔首,胆一壮,语声激越地道:“臣以为,未王执政二十余年,生灵涂炭,而今社稷祈盼明君,百姓祈盼明政,人心思古,皆愿我主能励精图治,恢复霸国昔日强盛之貌也!臣斗敢奏事有三,一曰减税、二曰还田、三曰革奴,请大王钧鉴!”
吕澍略解其意,顿觉人才难得。笑道:“这三条从何说起啊?”
林谦拜道:“未王年间,田赋增加到五税一,各地豪强大贾,仍不肯减轻盘剥,纷纷制订私税,佃奴生不如死。如今大王下旨,减赋为十五税一,足见仁爱之心!然而,除此田赋之外,小民还当缴纳算赋、口赋,征兵役、徭役,至于佃奴,则受害更深。大王欲致力农事,便应颁布律令,禁止私税、私赋,革除苛捐,否则地不留民,颗粒无收,此国之大害也。”
他见大王频频点头,信心大增,继续道:“还田者,即将百姓赖生之田亩归还之意也。臣早年困顿,眼见豪族、贵胄圈地养佃,强占公田,以至一郡之中,私田七,公田仅有三成!如此,豪族即可匿税不报,国库钱银,白白流失。清查田亩,还地予民,是乃方今治政首要之务也,民殖田愈广,谷愈多,仓愈足,国愈富强,可谓百世之功业也!”
“所谓革奴者,即将牲隶释以为民,造福国家。当初,先君驱使奴隶,建城筑都,开山辟渠,塞河为路,皆见其功。然而,如今一方大豪,贵胄族氏,孰不以蓄奴为乐?强逼硬买,甚至令人家破人亡,所图何也?只为奴价贱费少,所值颇多故也。一家养千奴,十家万奴,百家十万,而奴只知效主,不知效君,其所得,供于主家,不供于国。霸国有奴又何止十万之数?其中弊处,还请大王明察!”
众臣无不为林谦直言上谏而捏了把汗,见吕澍脸色越发不谐,不禁皆有寒芒在背的错觉。不料,林谦刚一说完,便听吕澍重重拍几,欣喜地大叫道:“好,好啊!林爱卿所言,与寡人无不相投!赐坐。”
林谦眼眶再次湿润,连连叩首道:“臣下迂腐,所议未必恰中时事,只愿大王能采纳一二,已很是满足了!”
吕澍偶然问及这个年轻长史,竟发现如此才俊,心中的喜爱无以言表。暗道:此人入仕三载,便已拜太傅长史,假以时日,恐怕会登临公、相,超过玉况、冯勤之辈呢。
慢慢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绪,颔首笑道:“卿之议入木三深,可见非一时所兴。目下适逢天灾人祸,寡人粗略统计,各地惟司郡月余谷十万上下,其他皆只出不进,连年告亏。寡人以为,农商之事,不可稍缓。励政革制,当务之急!工欲专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利则不宜商耕,不利则国有蠹害,不利则律行而不效,故寡人欲先行制诏,作劝农、劝商、减捐、削赋、释奴五法,不知诸位爱卿意下如何?”
群臣无不称善。吕澍忖度着道:“寡人将置中卿,名大司农,行罚赏、督农商,直属于寡人。本意令丞相代为谋主,督办此事,不过老爱卿日理万机,已极操劳,不宜再加烦芜,使之牵肠。诸位爱卿以为,孰可担当此任?”
司徒鲁庄道:“臣以为,此乃百世之业也,故宜择选贤良,以德高望重、才智兼备者为最恰当。”
吕澍也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是淡淡道:“卿此议甚好,不过这样的人选,恐怕难以遽得啊。”
其实吕澍也有其私念,不足为外人道。霸人聪慧,才杰倍出,吴陆诸国,罕有出其右者。然而,吕澍毕竟生于霸而长于昂,长期离乱,加之政治与战争频繁的角斗,使他坚信手握军权、培植亲信的重要性。如今虽贵为国主,但羽翼未丰,党徒未建,仍然是他一件极为忧心的事情。
所以,吕澍欲借亲政之机,荡平阻力,逐除异己。一方面,却仍不得不倚重霸国原有的臣僚队伍,以“不论门楣、宗亲,不论邦域,惟才是举”的贤君面貌,出现在国人面前。
在革除劣制、颁行善令、恢复生产、强国富民的口号下,吕澍更欲推出自己的心腹,以树立威望,故令群臣择选大司农不过是个幌子,真正执行君命的,应该是他的直属手下。鲁庄之言对他来说,未免大失准绳。
张放三世老臣,老于政治,对此岂能不察,拈须缄默,并不发言。
越琮心下不解,却因并非文臣,故亦不语。而司空白胥,虽颇欲表现,但自问身世、名份皆不如鲁庄,而大王心意难以揣摩,遂也只好装聋作哑。
吕澍心中一顿,暗暗后悔自己话说得太过急躁,遂欢笑道:“鲁卿老成谋国,朝之幸也,不过此事并非德高望重便可急就,欲收大效,还须快刀斩乱麻之法,卿意何如啊?”见鲁庄恍然大悟,连声称是,再转头笑问道:“老丞相意属谁家?”
张放沉吟片刻,道:“臣举荐北阳人,中书院监崔延。”
群臣一听,无不吃惊。这崔延乃未王时名著一方的名士,曾教学于雪岭之中,有弟子五百多人。后受辟于司徒何奕,上书陈策八条,未王不用,遂专心著书,有《政论》、《君鉴》二十余篇。此人以清议出名,却不敢触杵权势,甚至降尊纡贵,以求交往,为时人所鄙。
丞相张放推出这么个人物来,显是大出众人意料。事实上张放身边,有迟湛、李抗、令狐淼等人,皆是名臣,尤其是建策侯、尚书左仆射令狐淼,精练干达,政绩斐然,功胜同僚。他亦自觉有望,未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吕澍显然对这个崔延有所风闻,知其是畏首畏尾、不能成事之辈,也便装聋作哑,顺水推舟地笑道:“老爱卿所择,必能不负君望,寡人允准了!”
张放郑重其事地出席叩谢。
吕澍笑道:“平身。寡人即拜崔延为大司农,开府辟属,以竞其策。另着林谦为司郡屯田校尉,督办畿辅农桑。擢用伏氏冯勤为治粟校尉,清查土地、安置流民。敕王兄刘辛为律令中郎将,严惩不法,以免释奴还田令行不畅。此三人皆为大司农僚属,给秩各比二千石!”
群臣闻旨,无不作色,揖手称命。当下,吕澍便即刻召见崔延等人,待大兄刘辛上殿叩恩时,他亲自下阶搀起,笑谓之道:“寡人为王而御弟不侯者,恐怕自你、我开始罢?”
刘辛奋然拜道:“无功不受禄,更何况人君之赏!臣愿为大王毕躬竭力,以效圣明!”
吕澍哈哈大笑,顾群臣道:“寡人以社稷为父母,众卿为兄弟,赏功罚过,但求公平!还望众卿无不以此自励,莫要辜负了寡人的一番苦心啊!”
群臣出殿之后,皆先恭送张放登车回府,这才各自散去。当日晚间,新拜大司农崔延命人到丞相府表达谢意,赠送薄礼。
使者乃崔延弟子,司郡人韦睿。此人祖上乃吴朝杜陵太守韦道,道之孙竞阳尹,曾孙为少师参军,算得上三世二千石。到了这一辈,韦睿父官拜郡中贼曹从事,因事而免,然家道殷实,仍能求学于都,来去从容。
睿字怀文,侍母极孝,为太守举辟都官从事,后辞官入中书院学习经科,立志要做经世济民的人才。他精通《魏臧子》、《太衡论》,深得崔延看重,故而在霸国朝野,具有一定的名声。
府役通报上去,过了片刻,只见一中年人便装而来,隔得老远便拱手笑道:“却不是司郡韦怀文韦老弟么?”
韦睿一见,也连忙回礼道:“原来是张大人,晚辈失礼了。”
来者乃张放的第二个儿子张谘,字伯求,官拜马乡侯、安郡太守。张谘在任上极有政绩,曾征辟韦睿,虽因事未成,但两人的关系却非同一般。
张谘为人忠厚稳重,曾任燕陵功曹、趾郡长史。李即之乱平定后,越琮等力劝张放举不避亲,终使张谘得掌霸六郡之一的安郡。此次,他奉旨回京觐圣,其父为避亲疏,命他不得入宫,使他多少生出不满之心。
韦睿来时,张放正在会客,吩咐不见。张谘思忖与韦睿颇有故交,入京后又无机会见面详谈,所以自作主张,将韦睿迎进偏厢。
主人一面吩咐门下看茶,一面笑道:“韦怀文是为大司农崔延之事而来礼谢的吗?”
韦睿欠身道:“正是,不知张老丞相能否见纳?”
张谘拈须摇首道:“家父恐怕不会收下这份礼物。”
韦睿闻言,却未有意外,只是淡淡道:“师命难违,故此前来。张丞相门禁森严,若非大人,小子只怕很难跨进尊府半步。”
张谘苦笑道:“怀文老弟何来此言?别人不知我,汝还不知我吗?老弟他日成就必在我上,你我只兄弟相称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