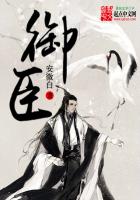司马光没有听错,确实是苏轼在叫他。
苏轼自从元丰七年正月离开黄州,一路游山玩水,访朋问友,到金陵已是七月,这之后去真州,继而游镇江、扬州,到常州任上时,已是元丰八年的三月。几天之后,赵顼驾崩。与各州县官吏一样,苏轼也在引颈鹄候京都的消息。到五月中,诏书来了,苏轼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接到诏书便离开常州去登州,到得登州,已是九月了。一路上走了四个月,还算是没有多耽搁。但到登州只五天,诏书又到,召苏轼回京任礼部郎中,刚到汴梁,又转任起居舍人。苏轼已饱经忧患,受尽困顿,身处密近,骤履要地,真正是心有余悸。其时蔡确尚未辞相,苏轼找他请求外放,蔡确没有答应,话也说得很客气:“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这之后不几天,苏轼又迁中书舍人。此时,苏轼的弟弟苏辙也回到京城,任右司谏。兄弟俩在汴梁团聚,又各任要职,竟然是喜忧参半。
苏轼既然能在举目无亲的黄州用不多时间便融入其间,东京汴梁是旧游之地,朋友又多,又有弟弟苏辙相伴,日子过得欢娱乐和,再与黄州相比,不啻天壤了。苏轼又举荐黄庭坚为校书郎,举荐秦观为太学博士。黄庭坚和秦观,与当时同在史馆的晁补之、张文潜均为一时俊彦,风流儒雅,照映当时。这四人追随于苏轼左右,苏轼虽未以师道自居,其道德文章却也算得上是诸人的领袖,天下后世便称此四人为“苏门四学士”。因苏轼的“乌台诗案”而贬黜的王诜、王巩也被起复回京,所谓兄弟聚首,友朋凑集,文酒赏适,苏轼是乐在其中了。
如果苏轼在公务之余与友朋或登临宴饮,或诗歌赠答,或由侍妾朝云泡点密云大团龙茶以之品茗闲话,并且乐在其中倒也罢了,偏偏他又管起了闲事。
司马光上疏言免役法五害,请罢免役法,苏轼不以为然。苏轼在杭州是通判,因当时杭州没有知州,苏轼便是事实上的知州。之后在密州、徐州、湖州都是知州之职,他对免役法利弊的理解比司马光要客观得多。他没有上疏言事,而是直接到通议事都堂找司马光理论。他走到离都堂不远处,见司马光送蔡京出来,正返身要回都堂,遂出声叫了一声“君实”。
司马光闻声转过身来,对苏轼笑道:“原来是子瞻,来都堂找我吗?”
苏轼走得离司马光近了,拱手笑道:“轼见过大丞相。”
苏轼从舍人院到都堂见司马光,是冠袍带履穿載齐整的。他与司马光的关系算得上是亲厚,便是从登州回京也是司马光举荐的。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时,因章惇时常戏侮,弄得十分头疼,又是苏轼对章惇说了话,司马光才得以安。但中书舍人见宰相是下属见长官,行礼却也是必须的。司马光在苏轼面前自然不会以宰相自居打官腔。今见苏轼行礼,也就还了一揖,说道:“子瞻将有何事言于光?”
苏轼说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苦,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苦,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
司马光说道:“依子瞻之意,该如之何?”
苏轼说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苏轼兜了一个圈子劝司马光不要骤罢免役法而行差役法,道理既说得透彻,意思也很明白。苏轼固然上来把免役法和差役法各打五十大板,其间曲意,赞成的却是免役法。他把免役法的役人与农民分开比之兵与民分开,并看作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这个“易”,是指“改变”,即不能再改回去。后面的“盖未易也”,是说“不容易”,这是苏轼把话说得和缓一点,希望司马光能够接受。司马光却还是听不进去。他说道:“免役法之五害,我已说得明白,早一日罢则多一日利,子瞻如何还劝我缓罢?”司马光说这话,语气中透着不快。话一说完,也不与苏轼招呼,转身走进通议事都堂。
苏轼是什么人?司马光把他干凉在都堂之外,他能罢休?苏轼随即走进都堂,对司马光说道:“公固已陈免役五害,然所陈非是,如何便可骤罢?”
苏轼这话已有责问的意思,司马光更听不进去了,忿忿然之色现于脸上,只不理睬苏轼。苏轼不依不饶,又说道:“轼尝闻公言之,当年韩琦剌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琦不乐,公亦不顾。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
苏轼提起旧事,司马光不得不有所表示。他笑了一笑,向苏轼作了一个揖,算是承认刚才态度不好,但对苏轼所言,却仍是不听。苏轼见无可再言,也向司马光拱手后退出都堂。
苏轼在司马光这里碰了一个软钉子,司马光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尤其使他不快。回到家里,边卸巾解带边大声喊道:“司马牛!司马牛!!”
苏辙先已到家,闻声走出,笑道:“大哥回来了,谁是司马牛?”
苏轼说道:“还有谁?司马光是也!”
苏辙又笑道:“原来是君实,果真固执如司马牛吗?”
苏轼说道:“君实做了宰相,脾气也见长了!”接着便把自己如何到都堂向司马光进言,司马光如何不听他劝,硬要以差代雇的情况告诉了苏辙。
苏辙说道:“君实骤罢免役而行差役确是不妥,大哥也不必气恼,君实既不听劝,由我上表陈情吧。”
当晚,苏辙灯下草表,他写道:
差役复行,应议者有五:其一曰旧差乡户为衙前,破败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
然而天下反以为苦者,农家岁出役钱为难。向使止用官卖坊场课入以雇衙前,自可足办,而他色役人止如旧法,则为利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乡差税户可托。然行之十余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之害。
其二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钵太重,未为经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酌今役钱减定中数,与坊场钱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纲运外,却令樁备募雇诸色役人之用。
其三,乞用见今在役人数定差,熙宁未减定前,其数实冗,不可遵用。
其四,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逆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乞仍用雇法。
其五,州县胥吏并量支雇钱募充,仍罢重法,亦许以坊场、坊郭钱为用;不足用,方差乡户。乡户所出雇钱,不得过官雇本数。
对于免役法和差役法,苏辙与苏轼的看法是相同的。苏辙所上五条都是肯定免役法,只是役钱太重。他的办法是用“官卖坊场课入”雇衙前,多余部份雇其他役人。司马光陈免役法五害时说:“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浮浪之人”,拿现在的话说就是街痞混混。苏辙则明白说“行之十余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之害。”仍然是这样:司马光是想当然而言,苏辙指的是事实。
尽管范百禄和范纯仁也反对司马光骤罢免役而行差役,那只是当面向司马光进言,并未上表,真正上表达于太皇太后的只有苏辙。太皇太后看过后,又差梁惟简送给司马光。司马光看了,搁在一边。苏辙之言并不能摇动他罢免役行差役的决心。
王安石初行免役法时,先由吕惠卿制成条例,在条例司反复论难,然后在开封府试行了一年多,又经曾布不断增损才逐渐推向各州县。司马光要在短短几天内废掉免役法固然不难,要复差役法却也不易。各项条贯不能熟讲,靠司马光在通议事都堂里闭门造车,难免有漏洞和错讹。不仅各州县执行起来会莫衷一是,在章惇这里便过不了关。
这是元祐元年二月间的事。为罢免役法事,朝臣众口喋喋,争执不休,连时光也侧目而视,减缓了流逝的速度。春天的脚步也变得迟缓了。它在顾盼,它在慢慢的展示,仿佛有所顾忌。终于,鸭头上的那种绿溶入了金明池的水中,梁园废墟上也已草色青青。春气在涌动着,扩散着,缓慢又坚决。它把柳枝摇得绿软,又浸润了花萼,拂开了花瓣。
紫宸殿却是十余年来(应该说是百余年来)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金装朱漆龙床的左后方垂下了一道软帘。春风从殿门外吹了进来,仿佛是要揭开软帘,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祇是在帘前打了个转,晃动了帘上的流苏,便消失为无形。
软帘的后面坐着高太皇太后,软帘前站着内侍省的押班梁惟简,龙床上坐着小皇帝赵煦。离龙床十步,按品叙班的站着文武百官,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站在最前面。
这是一个朝会日,原本是要在文德殿见百官,太皇太后以为文德殿是皇帝临朝之所,自己虽权同听政,不宜居于文德殿,遂改在紫宸殿见百官。此时太皇太后权同听政已经驾轻就熟,小皇帝的坐功也已炼成,能一动不动的端坐个把时辰。
梁惟简把绳拂子轻轻一甩宣旨:“皇帝有旨,文武百官有事启奏,无事退朝。”
小皇帝赵煦看着梁惟简,他有点奇怪,因为他并没有叫梁惟简宣什么旨。接着他就明白了,是太皇太后在以他的名义宣旨。
“臣有事启奏陛下。”小皇帝赵煦不看也知道,这是司马光的声音。不过他还是龙目闪动,看着抱笏躬身立于龙床前的司马光。
司马光话音刚落,帘后传出太皇太后的声音:“司马大人但奏无妨。”
司马光说道:“臣遵旨。臣前上疏称免役法有五害事,请罢免役而行差役,三省和枢密院既同进呈,皇帝陛下也已准臣之奏。臣复请陛下垂视,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为改更,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
司马光一说完,章惇跨前一步,向着坐在龙床上的小皇帝和帘后的太皇太后拱了拱手,抱笏当胸说道:“臣有本启奏。”
太皇太后说道:“奏来。”
章惇说道:“差役法如何,早则韩魏公韩大人曾有奏事,次则韩绛韩大人亦曾详言。所谓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东明县东王庄王姓老汉以避丁而自杀,此事亦韩维韩大人亲历。是以先帝登御之初,即下诏:‘天下官吏有能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此事人人皆知,而此时王安石尚在金陵,未预政事。其后条例司讲论役法,试行免役法,正为救差役法弊。司马光数免役法有五害,不知差害法有几害?”
司马光说道:“先帝固曾下诏,免役法亦为救差役法之弊而行,然所行非是,转为民害,是以复以差代雇。免役之法,如水之溺,如火之焚,早罢一日则有一日利,何能稍缓?”
章惇说道:“差役法衙前之役重则破家,司马大人何以明知其害而不思其救?”
司马光说道:“衙前役重,本相岂能不知?本相专奏中说得明白,‘可依旧于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业者,并令随贫富等第出助役钱,遇衙前重难差遣,即行支给。’枢密院既曾同进呈,章大人不会不知吧?”
章惇说道:“然则役人之田何人代种?莫非司马大人帮他们种田吗?”
司马光说道:“章大人这是什么话?本相岂能帮他们种田?”
章惇说道:“司马大人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能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不知司马大人视民为何物?视社稷为何物?如此行事,本枢使它日安能奉陪吃剑!”
章惇和司马光在金殿之上――太皇太后的帘前唇枪舌剑争论不歇,人既越来越激动,语声也越来越高。当他说出‘它日安能奉陪吃剑’时,不仅太皇太后震怒,竟是一殿皆惊。在章惇和司马光争论时,小皇帝赵煦看看章惇又看看司马光,以他的学识还不能判定谁是谁非。听到章惇说‘它日安能奉陪吃剑’,觉得奇怪,竟出言问道:“章大人如何知它日会吃剑?”
章惇说道:“臣启奏陛下,司马光欲改先帝成法,臣不敢苟同,故说臣它日安能奉陪吃剑。”
听章惇如此对小皇帝赵煦说话,太皇太后怒极又气极,厉声喝道:“章惇须有大臣体!”
章惇说道:“皇帝年幼,臣不敢欺也;皇帝有所问,臣不敢不答。臣如何没有大臣体?”
太皇太后怒道:“在本后帘前喧悖,何来大臣体?”
章惇说道:“臣与司马光同在帘前争论,太皇太后如何只说臣喧悖,不说司马光喧悖?”
章惇敢在帘前顶嘴,太皇太后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不过此时不要太皇太后亲口说话,有御史代言了。刘挚奏道:“章惇佻薄险悍,諂事王安石,以边事欺罔朝廷,遂得进用。及安石补外,又倾附吕惠卿,至于执政。先帝薄其为人,黜之未久,复为蔡确所引,以至今日。差役之复,三省与枢密院同进呈,章惇果有所见,当即敷陈讲画,今已宣敕命,始退而横议。章惇非不知此法之是与非也,盖宁负朝廷而不忍负王安石,欲存面目见安石而已!夫去恶莫如尽,陛下既去蔡确而留章惇,非朝廷之利。乞正其横议害政,强愎慢上之罪。”
刘挚话音刚落,王岩叟奏道:“章惇廉隅不修,无大臣体,每为俳谐俚语,侵诲同列。陛下诏求直言,而章惇斥上书之人为不逞之徒,其意不欲陛下广聪明也。陛下登用老臣旧德,而章惇亦指为不逞之徒,其意不喜陛下用正人也。今复于帘前争役法,辞气不逊,陵上侮下,败群乱众,盖见陛下用司马光作相,躁忿忌嫉,所以如此。伏乞罢免以慰天下之望。”
章惇在与司马光争论中并未落下风,应该说在气势上稍稍胜强一点。御史一开口,他便只有挨打的份了。御史弹奏,不会有什么好话,甚至于极不入耳,章惇都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在吕惠卿罢黜时他就领教过御史的齿牙。他也知道御史把蔡确和他以及韩缜视为三奸,必欲逐之而后快。在刘挚和王岩叟说话时,他依然神态自若。他偶尔看了小皇帝赵煦一眼,恰见赵煦的两只眼睛正乌溜溜盯着他,眼神之中竟露出了点同情。或许,在他幼小的心里,以为三人骂一人有点不公平?小赵煦的这一眼神,章惇见了不觉浑身通泰畅快。他心里暗骂太皇太后:“老虔婆,你总有归政的时候,这个账以后再和你算!”他抱笏当胸,向着赵煦微微打了一躬。在旁人还以为是因御史的弹奏而向皇帝请罪,小赵煦已感觉到了章惇的这一躬是向他表示谢意。
刘挚一开口,司马光松了一口气,太皇太后则是嘘了一口气。在司马光,御史是为他理论;在太皇太后,御史是为她出气。御史说完,事便议毕,可以退朝了。
在章惇和司马光争论时,韩缜原本应该和章惇同仇敌忾,向司马光发难。但他没有说话,他怕惹火烧身。再说,他本无所谓免役法或差役法。就在梁惟简走上一步,打算挥动绳拂子时,吕公著说道:“臣有本启奏。”
太皇太后说道:“奏来。”
吕公著说道:“司马大人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章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体。乞选差近臣三、四人,专切详定奏闻。”
吕公著说话做事四平八稳,虽偏向于司马光,章惇也还接受得了。他说的详定,这里面就还有文章。但此事不只朝中之人,便是司马光和太皇太后,也想不到这么多了。
太皇太后问道:“以卿之意,何人为宜?”
吕公著说道:“范纯仁、韩维、苏轼甚善。”
太皇太后说道:“准奏。”
这时梁惟简得太皇太后暗示,挥动绳拂子,扯起嗓子喊道:“退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