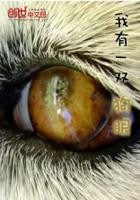你有没有骗过—个人—而再再而三可是你真的,只为了让她幸福、
一「紫簪:」
有时候我们的爱情,真的,也不过就是一瞬间的电闪雷鸣。
2003年,我的生命中有两桩大事,一件是大学毕业,另外一件,便是爱上尘寰。
就算很多年以后,我想我依然会记得那个刻骨铭心的四月午后。在学校对面的地下通道,阳光自第六级阶梯开始隐没。是一个明暗交替的清晰界限,我记得那样清楚,他往上,我向下。他的脊背挺得笔直,是一贯低头的淡漠姿势,细碎刘海垂落,遮住他半边骨骼的嶙峋面孔。他的身躯都还陷落在黑暗里,但因迈步幅度而约略摆动的额头上,已经有最先抵达的地面阳光,浅浅金色,温暖闪烁。然后他停下来,就是在自上而下第六级的阶梯上,他停下来,对住脚底看了一会,整个身子蹲下去。我看到他的面前,有三只懵懂仓皇的小狗。
神情麻木的老人,面孔是粗粝的古铜,蜷坐在宽大石阶的最右侧。看了一眼他手中捧住的白色小狗,颤巍巍地比出三个手指头。他未曾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举止,从钱包里抽出钱,利落地付了账。然后就小心翼翼地将那纯白色小生物抱起来,贴近自己的胸膛。
我站到他的身边,亦满怀友善地朝它观望。小小躯体有一点点瑟缩,但是神情乖巧温顺。我用手指点它微微湿润的冰凉鼻尖,轻轻地笑出声。他突然就转过脸来看我,是一张叫我措手不及的浅淡笑脸,带着与有荣焉的骄傲。他对我说,你要不要抱一下。
那是一个我如此陌生的顾尘寰。温柔地,欣喜地,沉郁嗓子可以湿润地掐出水来。他在四月春光的半明半灭里,抱着一只狗,对着我笑,好像手心里已经聚拢了全世界所有的珍宝。他的牙齿那么白,正午艳阳在那一刹那劈啪作响,如碎屑般溅落于他的眼眶。我的一只手在身后握紧成拳,听到有风声暗自涌动和血液扑扑流窜的声音。他的笑意像仲春南方一场兜头而来的充沛阳光,躲不掉了,所有心头防备都是一张脆弱的纸,轻轻一捅,丢盔弃甲般地碎裂,我直直地凝视他,微笑着点头,然后眼眶里突然蓄满了泪。
我22岁的初初萌生的爱情呵,虽然来得有点晚,却终于还是在那个仲春四月的寂静午后,在地下通道的明暗交接处,在他澄澈如孩童的笑脸里,辛酸而迅猛地到来了。像枝头一朵昏昏沉睡的蓓蕾,终于在花季的末尾,陡生的力量从根部滋长膨胀,终于,拼尽全力,啪地一声,开放。
这个同学四年的男孩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宿舍卧谈的话题。他的神秘和疏离,他的沉郁和镇定,他喜欢坐在窗口的位置,用黑色的炭素笔作笔记。下课铃声一响,便合上书本匆匆离开。他对着电脑敲击键盘的时候,神情肃穆,心无旁骛。他独自一人住在校外,大一拿特等奖学金,大二入选学校的研究室,大三开始在本市一家企业做兼职。他的身躯,总如标枪般挺得笔直,瘦削面孔,窥看不出悲喜动容。他不参加集体活动,不热衷班级娱乐,他的一双眼,自刘海掩映里,对焦于虚空。我亦有时候会想:他会笑吗,他会爱吗。他会专专注注地看一个人吗。他像坚硬寒冷的一块冰,他会融化吗。
可是我终于看到他笑,心无城府地,无限满足地,将一只小狗小心翼翼地放进我的怀抱,所有嶙峋的棱角都已经融化,我甚至闻到他身上温暖而潮湿的味道,我自他干净温存的面容,分明窥看出了满盈的爱。
他爱上那只雪白的狗,而我,爱上他。
年级的毕业晚会,在学校A段的礼堂举办。人很多,气氛在最最起初像一处繁茂的菜市场。楼上楼下,连过道里都塞满了人。声浪汇集起来,像一股涌动澎湃的潮水。我坐在正中的第三排。因为四年来一直都是校会文艺部的骨干,所以如今轻而易举地受到了优待。周遭很粘稠,节目很精彩,互动热烈。四处大灯,亮如白昼。可是我静默微笑,心不在焉。
终于等到8点20分,一个利落的休止符,所有的光亮在那一刻毫无预兆地熄灭。我在急速扑入眼眶的一蓬黑暗里,突然感觉呼吸的哽塞。一束小小追光打在舞台中央,吉他琴弦开始拨动,人群在一刹那的震荡之后,变成鸦雀无声的寂静。然后歌声响起。
他没有开场白,歌声是所有想要倾诉的语言。过往青葱岁月的句点,我们人生起初那场澄澈而忧伤的爱恋。此去经年,表白过的,都已止息,未开口的,都会沉默。青春是一本合上的书页。可是要怎样的悲怆躬身,才能同我们的旧日作别,渐行渐远。
是我很早就听过的旋律,在午夜的收音机里,叶蓓嘹亮如雨水的忧伤,老狼沉郁沙哑的呢喃:是谁的声音唱我们的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你走后依旧的街总有青春依旧的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都说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
都说亲爱的亲爱永远,都是年轻如你的脸,含笑的带泪的不变的眼。
他一个人坐在台上唱,所有的人屏住呼吸在台下听。吉他和民谣,是我们青春最后永不能平复的伤口,就像我们曾经的那些执著而艰难的热爱。他唱完最后一句的时候,琴弦还有微微震荡的余音,他垂头静默的姿势犹如沉溺的雕像。时间在那一瞬间,仿若凝滞成永恒。然后他终于站起来,在微弱的灯光里,朝台下鞠躬,退场。这样高傲而忧伤的少年呵,将熔岩般的热情封闭在淡漠的表壳里,我最美最好的时光末梢,惟一一个爱上的人呵。在整个礼堂如云朵般乍起的掌声里,我的眼泪骄傲而悲怆地落下来。
我跑去后台,他刚离开。我急忙推开后门追出去,五月的夜风,暖煦醺然,有花朵沿路盛开。纯棉裙摆在小腿处晃荡纠结,我捂着心口喊他的名字,顾尘寰等一等。
他停下来,转过身,视线是一簇清凉的月光。世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银白古朴小路,宛如时光河流。我就这样一路逆水而上,来到他的身旁。我有那么多的话要和他说,像有无数细碎的气泡,在喉管处争先恐后地尖叫,可是我张开了口,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二「蓝:」
我们的目的地,是尘寰的住所。这么多年,他终于由一个陌生人,告诉我他所有还在履行的从未放弃的诺言。
2003年的年末,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一把温柔女声,彼时,我甫从大会议室推门出来,将滋滋作响的手机贴在了耳朵边。
茶歇间里有一排宽大透亮的玻璃窗,我站到前面去,因电话那头支离破碎的描述,微微地蹙起了眉。整个城市刚刚平息了一场大雪,天空晴朗。北京冬日阳光,有慵懒浑厚味道。高楼下连绵马路,人群如蝼蚁营役忙碌。我伸出一只手轻轻按压自己的太阳穴,终于点头说,好的。
T85次列车,自暮色弥漫的北京站拉响汽笛,出发。抵达南京时,早上五点不到,天的底色仍是乌黑,有些微柔弱的白色晨光,于明暗交替处蠢蠢欲动。南方的寒冷与北方不同,温度虽始终未曾有零下几十的骇人,但它的这种寒,带着沁人的湿意,簌簌地,在骨骼血液中游走流窜,初初还不以为然,俄顷,便是浑身齐齐翻滚的寒。这种阴柔的侵蚀,比之北京铺天盖地扑来的剧烈,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热爱后者。
我将衣领竖起来,只提了一只包,走向出站口。已经有一些早起的人们聚拢在前方守候,或者是旅客的家人,或者是接站的朋友,亦有沿路拉客的出租车司机。我走到前面的时候,再次听到那把细弱温柔的女声,她唤我的名。她说,林蔚蓝,我是苏紫簪。
她看着我的眼神有一点点惘然,然后如梦初醒地朝我微笑,谢谢你能来。
车子在凌晨无人的街道上奔驰,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这一南一北的两个城市,有一些共通的贯穿气息。都是这样古朴的,陈旧的,带一点点历史残渣的风霜,有经历年月动荡后深沉宁静的沧桑。城市的道路,是延伸静默的伤口。我们的目的地,是尘寰的住所。
她一边掏出钥匙开门,一边温婉同我介绍。自他大二搬进这里,便一直未曾离开。窗帘桌布都是他亲手挑选。不大的一居,摆设却错落有致。处处是干净的层次分明的蓝,我一路随她自客厅走到卧室,然后看她蹲下身。她仰起脸对我说,就是它了。
一只蜷缩的狗。毛色纯白,趴俯在地毯上。因她手指的拨弄,慢慢地仰起头。在我的视线同它碰撞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胸口处泛起大块大块郁结的痛。是那样漆黑透亮的眼,仓皇和绝望都显而易见,在岁月恢弘手心,卑微而柔弱地,因措手不及的未卜遭遇,而微微颤抖。它的眼,深深凝视我,然后迅速蒙上一层浅浅的泪膜,细碎的波光闪烁,居然泛出微微的蓝。
这就是尘寰爱若性命的一只狗,亦是他出国前,指明要她转给我的礼物。
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捧起,充满爱怜:我连夜这样披星戴月地赶过来,就是为了接你吗?
尘寰把它买回来的时候,它还很小。他天天拿奶嘴喂它,像照顾自己的子女一样。恨不得每时每刻都将它带在身边,生怕它因为年纪太小而出事。我从未见人会这样去对待一只狗,下雨天一定是先把外套脱下来包住它,饥饿时也一定要先替它做好晚饭。睡觉的时候,常常因为听到它一声嘟囔,就立刻从床上跳下来。他那样爱它,它生病的时候,他日夜不合眼地守着它,把它抱在怀里,请求它好起来。他对任何事情任何人都一贯泰然处之,甚至包括他自己。可是这只狗,像一只锐利的箭,洞穿了他的心脏。他甚至会有一些时候,对着它痴痴地发呆。
她站起来,继续微笑着叙述,有那样多的人,渴望着得到尘寰的爱。可是他却毫不保留地将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眷恋,都给了这只廉价的狗。她的声音突然顿住。我回过头看她,她使劲地咬住嘴唇,有时候我会自欺欺人地想,他虽然不爱我,可是他也不爱别的任何人,他只是爱上了一只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他要亲口来让我明了所有事情的真相。她细瘦的手指绞在一起,因为用力而泛起青白,眼睛似要看进我的灵魂里面。她问我,你知道这只狗叫什么名字吗,它叫林蔚蓝。
九点开始熄灯,整个车厢突然陷入黑暗。我将身体折起,背抵住身后的墙,把旅行包摆到腿上,然后轻轻拉开拉链。它在里面,我从来未曾见过比它更懂事的狗。温顺乖巧,一双黑夜里熠熠发亮的泪眸。它或许饿了,或者是渴了,可是它一声也不吭,只张大了眼,忧伤地看着我。我抚摩它,一遍一遍,然后自外侧的口袋里摸出买好的熟牛肉,它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发出任何声音。虽然因为饿,吃得有一点点快。潮湿冰凉的舌头,偶尔舔过我的掌心,涩涩的粗糙,我唤一声它的名字,林蔚蓝,然后眼眶里突然如落入巨大沙砾。
1992年,尘寰在操场后的角落里找到我。放学后的校园,一片寂静。惟有始终不知疲倦的聒噪蝉声,隐隐窜入耳膜。我的身体蜷缩,头埋在膝盖里面,双手紧紧地环住自己,眼泪是暗地崩溃的河流。他站在我的面前,挡住了最后一抹残余的阳光,却不说话。过了许久,我才能故做镇定地抬起脸来,你是来嘲笑我的吗?
他突然跨大一步上前,伸出手,用力地擦拭我脸上犹带的泪痕,11岁的顾尘寰,个子还没有我高,黝黑瘦小,可是他手掌的力气那么大,笨拙地在我面上擦拭,刮得我生疼。他的嘴唇抿紧,眼神冥暗无底,始终,却不说一句话。我不知是羞辱还是动容,突然捉住他的手臂,将自己的面孔贴上去,我的眼泪又铺天盖地地落下,细细哽咽的声音像一只哀伤的小狗,顾尘寰,他们都不要我。你一定是来嘲笑我的,你一直都在欺负我。
自转入这所小学的第一天起,他便对我深怀着恶意。用石子丢我,用篮球砸我,用剪刀剪我的头发,将墨汁甩上我的白衬衣,在桌子上划"三八线",一旦我手臂不经意触及,他便雷厉风行地用手肘狠狠地撞我。我揪住他的一只手,哭得不能自已,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要这样地对我。
他浑身僵硬如石块,终于艰难地开口,他说,蔚蓝,我再也不欺负你了,我也不会让任何别的人来欺负你。
真的吗,我仰面绝望地看着他,泪眼模糊,顾尘寰,你不会再欺负我了吗,你以后会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了吗?
他郑重地点头,再点头。我再次大声地哭出来,你不要骗我,请你请你不要骗我,不然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记忆里,似乎那便是我最后一次酣畅的哭泣。如揪住一根救命稻草,在他的面前,毫无保留地,哭尽了此生所有的恐惧和悲戚。直至昏天暗地,直至眼泪干涸,直至上下眼皮肿如桃核。起身的时候,已经懂得扯住他的衣角,看两人一前一后偶尔交叠的影子,心里有影影绰绰的欢喜,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将我遗弃,顾尘寰他答应我,要一直保护我。
一边走,一边问他,是不是像王子保护公主那样。他的面孔突然涨红,恶狠狠地应道,像大英雄保护一只可怜的狗。我扁扁嘴,为什么我是狗,你却是人。
那我也做狗好了。他挠一下头。
以后你要是敢再欺负我,我就养一只叫顾尘寰的狗,天天虐待他。
那我就养一只叫林蔚蓝的狗好了,他的语气顿一顿,声音低下来,不过不管你怎么对我,我会一辈子养着它,照顾它,对它好,除非我死。
他真的养了一只狗,叫它林蔚蓝。养着它,照顾它,对它好,他托一个人来告诉我,他从来未曾忘却过他的诺言。原来我和他之间,我一直才是残忍和自私的那个,我以为他背弃了誓约,我毫不迟疑地将他自我的身旁撇落,我甚至因为自己的爱和信任,而满怀羞辱和愤恨,我那样的恨他呵,若不能遗忘,便要一辈子的憎恨。
我是这么对他说的吧。在大一那年的藤萝架下,站在他的对面,指甲掐进了手心,我一字一句地对他说,顾尘寰,休想我会原谅你。若不能遗忘,便要一辈子的憎恨。除非你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