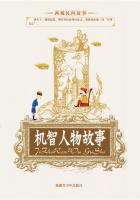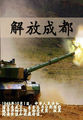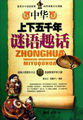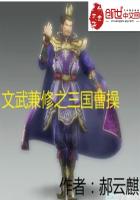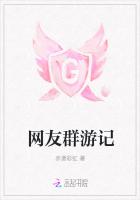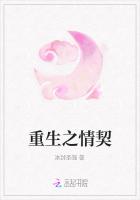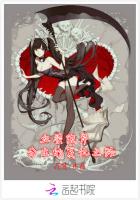1988年,从外地出差回京的陈原在北京站口被告知,陈翰伯先生于当日凌晨逝世。陈原怔住了,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说:“仅仅一个星期前,也就是我去外地的前夜,我们几个熟人和翰伯在一起筹划着编一种冲破海峡人为障碍的出版物。那天,他体力不支,但兴致盎然。临别,他叮嘱我说:你回来再计议。我匆匆走了七天,又匆匆回来了,可是我再也看不到翰伯,再也听不到他那低沉而有力的声音了。”
他回忆说,他与陈翰伯都是职业的编辑,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中,相互支持,并肩战斗。“大跃进”那阵子,陈翰伯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陈原在国家出版局,他俩几乎每天子夜都通电话,谈的都是出版的问题。二十年后,两人的岗位互换,依然保持着夜间通电话的习惯。两人一起去过牛津,去过剑桥,也去过“天涯海角”,在旅行途中讨论的核心问题总是为了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他们该奉献什么,能奉献什么。
陈原说,在最困难的“文革”十年间,两人一起讲“悄悄话”,一起坐过“喷气式”,被编成一个劳改小组,一起打扫过厕所和食堂。
陈原先生的回忆娓娓道来,行云流水,字里行间流露的真情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灵。
书缘结“盟友”
事实上,不仅在陈原眼里,他与陈翰伯是挚友。在他人眼里,他们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对人,因为都姓“CHEN”的缘故,大家称他俩为“CC”。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千余年前,有个桃园结义的故事,那只是兄弟间自发的义气行为,不同于结义的是,CC倒是旁人通过观察给予两个人共同的称谓,显得更加珍贵、自然和真实。而从陈原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想见,造就和连接CC的就是编辑出版事业。
这是一对不简单的CC。
陈原先生除了懂得六个国家的语言,能用各种语言演讲、写论文外,还编过《新华字典》,在“文革”什么也不让干的日子里,竟然从头到尾地读《辞源》、《辞海》;此外,他还懂得工程力学、语言学和地理学。解放前,他长期供职于著名的三联书店,解放后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有人称他为通才,有人称他为时代的殿后者,即“后无来者”之意。也有人说,他是个杂家,最地道的编辑。
陈翰伯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24岁时就任张学良将军办的《西京民报》总编辑。其后先后担任《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六种报刊的总编辑,解放后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
共同的学者情怀与出版情结,近半个世纪的工作联系,注定了这对CC非凡的情谊。1969年,随同文化部六千人,两人一起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2年,又一同奉命调回北京。
两年多的干校生活,这对CC命运坎坷,可是,他们关注得最多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的现状、全民的阅读问题。
陈原在干校期间,夫人在几十公里外的家属连心脏病发作,他拿着电报去请假,结果军宣队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探亲访友?在批斗会上,他的“帽子”格外多:“无时无刻不在反对毛主席”、“每一关键时刻都站在反革命路线”、“用资本家的态度对待青年干部”等等,不一而足,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
特定的历史环境,把读书人都弄得神经高度紧张,陈翰伯的儿子从北京去看他,带了一盒点心,没想到,陈翰伯一看点心,立即面露难色,因为他担心军代表看见又会上纲上线,批评他生活奢侈。1972年春节前,陈翰伯回到北京,女儿回忆说,看见父亲穿着一身油渍麻花的棉制服,手里提个破花布书包,俨然一个地道的农民。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原说:大家的心却是红的,口头上讲,就老死在干校吧,心里却说,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呢?在被打成“牛鬼蛇神”最不堪的日子里,陈翰伯说:“我有三条,第一不逃跑,第二不自杀,第三我将来还干这个”,意思是还干出版工作。
这就是CC,无论个人境况如何,那份坚韧的责任感却永不丧失。作为读书人、出版人,这份责任感最突出的体现莫过于对当时人们无书可读的忧虑。
在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代,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这是个多么可悲和可怜的数据!
书籍的贫乏,人们精神上的荒芜,强烈地冲击的CC的心灵。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缘何沦落到文化上的如此落后。他们私下商量,回去以后一定要办与读书有关的杂志,立志将来“还干这个”的陈翰伯提议,杂志名字就叫做《读书》。
与CC共同商议此事的,还有一个叫范用的出版人,三人在当时有一个共同的称谓:“陈范集团”,意即三人是个反动的小组织、小集体。事实上,如同CC一样,不过是共同的事业与志趣连接起的友谊。
与CC出身科班不同的是,范用仅仅上过四年小学,他唯一的母校就是浙江一个叫做穆源的小学,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中国优秀的出版家。14岁那年,因为躲避日本人的炮火,他逃到汉口,阴错阳差地成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邻居,三个月后,他成了出版社的一名小练习生。其后,他入了党,为党的事业开书店、做出版,最多的时间供职于大名鼎鼎的三联书店。1949年后,他自然成了新中国的出版人。当年那个年龄小、个子小的练习生,成长为共和国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三联书店总经理,也就是成为了国人心中的“大家”。
“大家”躲不过“文革”的狂潮,躲不过下干校的命运。1969年9月底,范用随人民出版社近200人一起来到咸宁“五七”干校。仅仅3个月后,身在北京的母亲就去世了,悲痛不已的范用请假回京料理后事,却遭到严词拒绝,原因是他还属于被监督劳动对象,没有获得“解放”。
与CC一样,范用没有过多地关注自己的痛苦和不幸,而是担忧着人民的阅读问题。多少年前,他们在重庆、在桂林、在武汉……办了多少报刊、杂志。在抗战的日子里,在解放战争的日子里,他们以报刊为武器,传播着知识与文化,点燃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希望。忘不了,他们在解放前办的《读书生活》杂志,曾引导多少青年走上了追求新思想的道路。今天的新中国,怎么可以反而落后了,反而在文化上退步了,人们怎么反而没有书可读了?他们不甘心!
《读书》照神洲
陈原先生在一本《我的小屋我的梦》里专门记述了他的小屋:我的小屋,其实应该叫做书屋。套用古人的名句“环滁皆山也”,我这里是“环我皆书也”。斗室中除了我就是书,真可以说,几乎没有转动余地。旧时描述自己家穷,说什么“家徒四壁”,我家不富,可也不能说穷。但我却“家无四壁”,四壁都被顶天立地的书架所掩盖,确实看不见一点墙壁。
范用在一篇《书香处处》的文章中写道:小时候,先是在学校的图书室借书看,后来到五州图书馆借书看……进一步,通信借书,上海有个蚂蚁图书馆,只要买本该馆的图书目录,查出要借的书,写封信附去邮资,不出一星期书就可以寄到。由于读书甚广,他曾领到一个特别的工作任务,就是给毛泽东同志搜集各类书刊。
带着一份对书的痴迷,他们成为出版人,不仅自己读书,更为别人出书,引导人们阅读,让更多的人享受读书的乐趣。
1972年,身在干校的范用接到回京的通知,原来,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刚刚召开,要从各地干校调部分司局级干部抓马列著作的出版发行。这对范用而言,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当时多少干校学员眼巴巴地盼着回京呢。可是,当范用后听说他所在的十三连只调自己,第一反应就是:“那不行,还有许多有经验的行家在干校,光调回我一人有什么用?”
回到北京后,范用到外地拜访一些尚未解放的老专家、老教授,请他们为重振国家的出版事业献计献策。然后又想尽一切办法从干校调人,并促成了他的同盟陈原和陈翰伯的回京。回到北京的陈翰伯与范用一样,极力呼吁把文化部干校的干部都调回来工作,当时的说法是“去干校不过十年八年”,陈翰伯大声疾呼“人生有几个十年八年哪?”于是,批“陈范集团”的大字报又铺天盖地起来……三人无言,但他们坦荡,他们不是为了朋友的私人感情,而是为了振兴祖国的出版事业,为了人民能够有书可读!
1979年,经过一番精心的酝酿和准备,《读书》杂志终于创刊。这是共和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作为中国读书人、知识分子精神上的亲密朋友,“陈范集团”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心愿。三人紧密协作,力求把《读书》办成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最好的杂志。差不多每个月在陈原那里开一次会,谈如何组稿的问题,稿件最终由范用确定下来,定稿再送给陈原看,重要的事情向陈翰伯请示。那个熟悉的“CC”称谓又回来了,当年遭到猛烈打击的“陈范集团”,为中国文化的又一轮启蒙乐此不疲地劳作开了。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杂志,从创刊之初,就承担了一份巨大的社会责任,在书籍几尽荒芜的时代,《读书》引导与鼓励人们走进阅读的世界。创办之初,范用曾立下军令状:万一《读书》出了问题,责任全由他一人承担。在杂志的第一期上,就石破天惊地刊登了一篇《读书无禁区》的文章,文章痛惜地指出: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文章大力呼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在“文革”刚刚过去的时候,在人们的思想还普遍在禁锢中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与思路,实在够“大胆”的。而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这种提法又是多么适时和有意义!在杂志创办两周年之际,陈翰伯专门撰文《两周年告读者》,重申“读书无禁区”的主张。此时,他已经是出版局的高官,很少为下面的杂志写文章了,但是,这次他一定要亲自动笔,因为,那是他用心血浇灌的杂志,他要用心呵护。
2009年,在《读书》创刊30年之际,不少人写了评论文章,有人称《读书》创刊号已经成了一个集体记忆;也有人说,《读书》是中国改革开放在思想领域里一个标准的诞生物。在那个精神世界经历了长期禁锢而刚刚得到释放的年代,《读书》提供的思想营养、文化视野以及人文关怀精神整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由此也被视为“新启蒙时代”的象征之一;还有人说,《读书》一度作为中国绝无仅有的思想传媒,赢得了一个时代。
众多的赞誉告诉人们,《读书》在它所处的时代里成功了!这是对“陈范集团”最高的精神奖赏!
从推动反思到繁荣书市
作为承担历史文化责任的出版人,“陈范集团”所做的远不止这些。《读书》顺应时代的要求与知识分子的愿望,对“文革”进行了有力和成功的控诉。作为“文革”的亲历者,“陈范集团”把眼光盯向对“文革”全面的反思与拔乱反正。
1978年10月,陈翰伯在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不可以写母爱?母爱有什么不好?”顿时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一些女编辑激动得热泪盈眶。长时期缺乏人性的禁止,人们连正常人的思维都不敢表达了,他们太需要陈翰伯这样的领导出面说句心里话。
在领导全国出版工作的拨乱反正的日子里,陈翰伯殚精竭虑,甚至筋疲力尽。据其女儿回忆,那时候经常见到父亲下班回来“吃不动饭”,要躺一会儿才能吃饭。
巴金先生对“文革”反思的系列文章开始是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范用看到后,毅然主张在国内出版,而且做到一字不删,最后定名《随想录》,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巴金在给范用的一封信中说:“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文明’书市的。”
1994年,曾下放咸宁“五七”干校的陈白尘先生去世,范用得知陈白尘去世前曾将当年在干校的日记选编出来,取名《牛棚日记》,却遭到种种阻力不能出版,他立即约见陈白尘的女儿。就在这天,他不幸被自行车撞断了腿骨,卧床五个月。但是,他躺在病床上读完了书稿,果断决定出版。书出来后,他拄着拐杖把书送到陈白尘图书展览会上,亲手交给了陈白尘的夫人,表达了他对能讲真话的陈白尘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他也通过此举让更多的人了解“五七”干校的历史进而深刻地反思。
而实际上,我们熟悉报刊杂志,熟悉巴金,却有多少人知道陈原、陈翰伯或者范用。虽然因为他们,我们享受在好书的海洋里。
他们不在意这些,说:“我是给人家出书的。”
因为出书,因为爱书,他们把关注的眼光送给了更多的读书人,为了提高全民整体的科学文化水平,他们曾忧心忡忡,也曾殚精竭虑,夜以继日。
陈原在读《陈翰伯文集》后写道:“今日展读遗文,却仿佛回到从前那战乱的年代,火红的年代,悲伤的年代,我们两个在半夜里电话谈心一样——一样的愉快和兴奋,虽然多了几分寒意。我想念他。”
我能理解这份浓浓的想念。在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里,他们携手延续着我们民族的文化薪火。
200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30周年座谈会召开,中宣部、文化部、中国出版集团的领导都来了,新朋老友都来了。然而,“陈范集团”没有一个人到场,无情岁月的流逝,他们或者已经作古离我们远去,或者年老体衰,不再有能力参加活动了。
但是,他们何时真正地离开过我们?在他们绝尘而去的时候,为我们留下了落日飞霞的瑰丽。你不见如今书市的繁荣吗?你不见各大书店琳琅满目的图书吗?你不见今天如潮的各类报刊杂志吗?
当我们漫步在书海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他们?可曾想过一个叫做向阳湖的干校?可曾想过CC、“陈范集团”与《读书》杂志?对于今天的人们,那些都成了一个个的符号。这些符号,记载着我们民族的记忆,有痛苦,有奋起,也有责任,更有期望。
我想起了在网上狂搜《读书》杂志相关信息受到的震撼,很多人在网上求购《读书》创刊号,却没有一个人获得成功!人们要买的其实真的是一份杂志吗?远远不是。一位《读书》杂志几十年的忠实朋友在一篇《几摞〈读书〉,一份旧情》的文章中写道:我会把它们收存起来的,就像收存旧情,收存记忆,收存生活的一部分,收存不复回来日子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