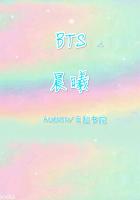各大队各学校的群众、学生队伍按照事先划分好的区域入场坐定后,批斗大会开始了。
主持大会的是兴隆公社工作团的团长任立新。西原县工作指挥部的总指挥和官泰公社工作团的岳志明团长也前来参加批斗大会。
主持人照例宣读了几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之后,就宣布把兴隆公社最大的走资派、大流氓李明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反攻倒算的美女蛇、右派分子齐翠花揪出来示众。一声令下,早已在后台做好准备的四个造反派分别把李明和齐翠花押到了前台。
李明看起来十分虚弱,他站立不住,两腿直打哆嗦,屁股往下直垂,那两个身穿黄军装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左右挟扶着他。他的胸前照例挂着黑牌,牌子上写着“打倒走资派、大流氓、大嫖头李明。”“李明”用红笔打了×。
齐翠花被剃了阴阳头,半边脑袋光秃秃的发亮,另半边头发披在了左耳腮边。她低着头,胸前写着“打倒美女蛇、白骨精勾魂娃”!她照例被两个造反派左右挟持着。
两个批斗对象站定,主持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
打倒兴隆公社最大的走资派、大流氓、大嫖头李明!
打倒美女蛇、白骨精、右派分子齐翠花!
李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勾魂娃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砸烂李明的狗头!
砸烂齐翠花的狗头!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喊完口号,就宣布李明和齐翠花的罪状。
主持人在抑扬顿挫地宣布着两个人的罪状:
李明,男,汉族,现年五十五岁。陕西省武功县人。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走资派,他不仅一贯坚持资本主义立场,而且生活糜烂,作风败坏,早年就与美女蛇勾魂娃齐翠花乱搞两性关系。后来他身为公社党委书记,为了达到与齐翠花通奸的目的,以宣传人民公社成立为由,专门把已经当了右派的齐翠花请到兴隆公社,安排了单独房间,好吃好喝款待,还同右派分子同流合污,同台演戏。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身为党的公社书记的李明,又派人为右派分子齐翠花送炒面送钱,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干部的阶级立场。当造反派明察秋毫,把他揪出来批斗的时候,他又拒不接受革命群众的改造,上吊自杀,以此威胁革命造反派,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实属罪大恶极……
柳毅和齐翠花的脑海里,急促地搜寻着以往的记忆:
他确实喜欢她。为了跟她在一起,他寒冬腊月弃家为红家戏班教戏,少拿工钱;为了追寻她的足迹,他放弃其他戏班优厚的条件,四处寻找红家戏班的演出台口;为了心中的一份牵挂,他不顾公社书记的身份,与当了右派分子的她亲密接触,关心她的生活。可他却始终没有得到过她。他一直把跟她同台演戏,扮夫妻当作一种享受。他同她一起演出过《二堂舍子》、《柳毅传书》、《清官册》、《辕门斩子》……没想到今天竟是以这样的形式与她同台亮相?
站在戏台上,齐翠花也自然想起以往的舞台生涯。以往的秦腔舞台,是勾魂娃的天下,当家花旦非自己莫属。花旦演腻了还会演青衣,演老旦,演小生,甚至演须生,演花脸……可今天演的哪个行当呢?像花脸?像丑角?都是,又都不是。
柳毅啊柳毅,你为什么要自讨苦吃?我齐翠花可从来没有对你动过心。过去年轻时没有动过,就是在你当公社书记时也没有动过。我感激你对我的照顾,但我不能接受你的另一份情意。你为什么不把遗书写给别人,却要偏偏写给我一个接受改造、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右派分子?你不但害了你自己,也连累了我呀?我如今是屋漏偏遭连阴雨呀!丈夫丈夫离了婚(指红富国,田大勇离婚的事她至今还不知道),儿子儿子不争气,红城子那边的批斗和张存女一家的臊毛还没有停息,这边更大的批斗场面又将自己推到了大庭广众面前。如果勾魂娃的名字以前家喻户晓是一种荣耀的话,这一回是什么形象呢?大花脸,阴阳头,像个女鬼一样。传说中的女鬼是要勾人魂魄的,这一回自己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勾魂娃。
她斜着眼瞥了柳毅一眼,只见他吃力地圈着腿,拉着腰,秃秃的脑袋歪向一边,那张刀疤脸显得更加难看,他双目紧闭,狼狈极了。她的心里倏地窜上一股同情感:青年时那么英俊,那么傲气十足,那么喜欢打扮收拾的正生演员、公社书记,如今成了这般模样,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李明(柳毅)回味着他辉煌的过去:正生是自己的本行。扮演的田云山,正义而又机智,面对气势汹汹的湖广总督卢林和会审的布案三司,他不卑不亢,沉着应对,据理力争,终于在儿媳妇胡凤莲(由齐翠花饰)的仗义配合下,使依官仗势的卢林进退两难,丑态百出;自己演的寇准,面对潘杨两家棘手的命案,他在八贤王赵德芳(红立贵饰,齐翠花也演过)的全力支持下,假设阴曹地府,假扮阎王和鬼判官,机智地审清了潘仁美残害忠良——杨家父子的案情,将身为国丈太师的潘仁美处以凌迟;自己扮演的《打镇台》中的王镇,更是刚直不阿,临危不乱,将以大压小,无理取闹公堂的八台总镇李庆若当堂施刑,重责四十法棍,打得他皮开肉绽;自己扮演的孙安,急民所急,为民请命,为了除却祸国殃民的奸贼张存,他抬着自己一家三口人的棺材进京,冒死面君,弹劾奸臣,取得胜利……就是自己当了公社党委书记,也在工作中抵制过上级的浮夸风。如今,面对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面对排山倒海的万名群众,自己实在感到无力回天。他想学田云山据理力争:我不是走资派,我与齐翠花和沙秀红是清白的,我不是大流氓,不是大嫖头。毛主席一贯倡导实事求是,我不能背这莫须有的罪名……但他这会儿连说话喘气的力气都没有。他想学习寇准,向错误路线反攻,可寇准有八贤王支持,谁支持自己呢?他想学习王镇,痛斥痛打这些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大搞逼供信,不搞文斗专搞武斗的所谓造反派,可他提不起这个勇气。王镇喝令一声,两班衙役会如狼似虎地擒拿施刑,可自己喝令谁呢?他想,他唯一能效仿的就是孙安,如果这次能死里逃生,自己一定要冒死上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陈述文化大革命的黑暗面和工作组的颠倒黑白……
轮到宣布齐翠花的罪状了。她耳朵里进去最多的词就是“美女蛇”、“勾魂娃”、“右派分子”。竟然也听到“大破鞋”这个词儿。她心里愤怒了。自己是大破鞋吗?旧社会的是非恩怨能完全怪我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吗?跟红富贵的结合能算是搞破鞋吗?与田大勇的结合,那是自己真正追求爱情的表现,也是一种社会进步。与大勇在延安结婚时,婚礼还是鲁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首长主持的。至于这位李书记柳毅,那实在是天大的误会,自己压根儿就没有那种意思。关于儿子红星的事能怪我吗?我一个戴帽子的右派分子能管住已经长大成人的红卫兵吗?他跟工作队员都能发生关系,我能管住工作组吗?
勾魂娃是自己的艺名,从旧社会一直叫到现在,它是自己的骄傲;右派分子虽然使自己心惊肉跳,但那是没有办法的呀?打成右派,就得让人家叫,美女蛇虽然刺耳,但心理上还是默认了的,最起码前面还有“美女”两个字。至于蛇吗?无非是说自己表面漂亮、温柔,心里毒狠。但蛇里面也有无毒蛇。白蛇修炼成精的白娘子白素贞还是千古赞美的艺术形象哩。白素贞敢爱敢恨,面对许仙,她万般温情,忍辱负重;面对法海,她嫉恶如仇。胡凤莲虽然是渔家少女,但她面对高官污吏的卢林,毫不怯懦,陈述他儿子卢世宽打死父亲的条条罪行,使卢林无言以对,中途退堂;巾帼英雄穆桂英,为了追求爱情,放弃山寨寨主地位,投奔宋营,为了解救被父帅捆绑斩首的丈夫杨宗保,她先礼后兵,要挟父帅杨延景:公爹饶了将军命,桂英尚有儿媳情;倘若不饶将军命,宋营里杀一个满堂红!穆桂英多有气派?自己当年饰演她的时候,一声“你不心疼我心疼”的唱腔,那真格勾人魂哩。还有个李慧娘,人家就是死在恶人贾似道的刀下,变成冤鬼,也与心上人幽会,闹得贾似道狼狈不堪……自己要是有穆桂英的气派,身挎宝剑,也“杀一个满堂红”,方显我勾魂娃的本事。可是这可能吗?看来只有像李慧娘那样,死了变成厉鬼讨回自己的公道……想到了死,她自然想起远在天边的丈夫田大勇和女儿田园。她心里叫道:大勇,你知道我现时的情况吗?园园,妈妈想你呀!大勇,再见了;园园,再见了!
齐翠花并不知道田大勇已经给红富国寄来了离婚的信,她还深深地爱着这个小她三岁的丈夫,当然,更想念丈夫身边的女儿田园。她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她又一次听到了“大破鞋”这个十分刺耳的词。她突然鼓起勇气,大声申辩:“我不是大破鞋,我不是大破鞋!天哪,我冤枉!毛主席万岁……”
只见她掀掉胸前的牌子,一头向左前方的明柱上撞去……
李明正在胡思乱想,突然被齐翠花的喊声惊醒过来,他见她以头撞柱,他也反应过来,也向前方的另一根明柱撞去。可是由于身体虚弱,胸前的黑牌又大又重,他摔倒在地。
会场一片大乱。台上一阵忙碌。
县上指挥部的头头和官泰公社工作团长岳志明在兴隆公社工作团团长任立新的陪同下,正要从后台走出舞台,却被前进大队回族老党员马长林堵了个正着。
马老汉身背一杆步枪,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拿着一本红皮皮《毛主席语录》。迎面给几个头儿深深地鞠了一躬。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把县上指挥部的头头吓了一惊。任立新和岳志明都认识他,就给县上的头头介绍:“这是回族老贫农老党员马长林同志。”
那头头握住了马长林的手说:“你好?有什么事?”
马长林与任立新和岳志明分别握了手,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找你们这些大头头,肯定有重要的事。”
任立新说:“我一看你又背枪又拿灯的架式,就知道你又有什么重要的事。走,回公社再说吧?”
马长林说:“不,就在戏台上说。就三言两语。”
任立新有些不耐烦,就说:“什么事情?你说。”
马长林说:“我们大队的贫下中农造反派都强烈要求把走资派李明和美女蛇齐翠花揪到我们前进大队去好好批斗几天,为我们回族群众给个说法。”
任立新说:“你没看见吗?这两个人现在都是半死不活的,咋样批斗?齐翠花已经送往卫生院了。把她抢救过来了再说。”
马长林说:“卫生院里大夫都当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哩,齐翠花放到医院里怕是没有人管哩。她虽然是个右派分子美女蛇,可她是上头送下来劳动改造的,要是把人弄死,怕是给上面不好交代哩。我们大队的卫生合作医疗站我说了算,保证把人给你们抢救过来,再交给造反派批斗……”
任立新听了马长林的话,也似乎明白了齐翠花生与死的利害关系,就说:“刚才她撞得昏迷过去了。不知道有没有生命危险。走,咱们先到卫生院看看再说。”
几个人越过乱麻麻的人群,向公社卫生院快步走去。
任立新问一位女护士:“齐翠花抬到哪里了?”
那护士说:“抬到太平间了。”
几个工作组头头一听,脸上都露出惊讶之色。任立新问:“她死了吗?”
女护士说:“好像还有气哩。听院长说,没有造反派的明确指示,没有人敢治。”
任立新听了大喝一声:“混蛋,真是一帮混蛋!战场上的俘虏还要给人家治好伤哩,人命关天的事,还明确指示他妈的个×?你们院长在哪里?快叫来!”
一个所谓院长的中年汉子抖抖索索地来了,他欠了欠身子,小心地问:“是任团长叫我?”
任立新劈头就问:“我问你,病人抬到了你们医院,你们为什么不立即抢救,把人撂在太平间干什么?”
那个院长说:“她是右派,批斗的对象,我也是批斗的对象,我怕……”
任立新骂道:“你怕你妈的个×。人死了怎么办?还不赶快抢救……”
齐翠花是抢救过来了。可马长林心里却一直不踏实。他又找到任立新,要求把齐翠花带到他们前进大队合作医疗室护理。
任立新见马长林过分热心这件事,心里就有些纳闷。他说:“老马,这些事情别人躲都躲不及,你怎么放着清闲不享,却要找麻烦?”
马长林把白胡子一抹,把那盏马灯往桌上一放,不紧不慢地说:“任团长,因为我老马是个老党员呀,是个老贫农呀!我不为革命事业着想,总还得为你们工作组着想呀?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哩,要是在批斗大会上碰死了,你想影响大不大?齐翠花不是一般的阶级敌人,她是延安下来的。上面的政策是让她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总不是把她往死里整么?要往死里整,上面早就整死了,还下放到老家农村干啥?这些政策条文你当团长的肯定比我大老粗清楚。我老马为啥关键时刻总是不离这盏马灯,还有这一杆枪,就是要用红军的精神对照当前的事情,让自个儿心里不要糊涂。这盏马灯的来历我给你说过;这杆枪的来历你也晓得,是五一年我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时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奖给我的。周总理还夸我是宁夏的回族库尔班。库尔班你任团长总晓得么?他就是从新疆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的那个维族老汉……”
“行了,行了。这些我都知道。”任立新打断了马长林的话。他怕他再啰啰嗦嗦地重复红军灯和“七九”步枪的辉煌来历,就摆了摆手制止了他:“你老人家还是想把齐翠花接到你们大队去治疗?”
马长林说:“放到我的身边我放心一些。放在公社卫生院我怕把她耽搁了。你也看见了,那个院长正受批斗哩,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做主,他不做主,别人也不好办。我还怕学校的红卫兵娃娃伙儿冲进医院,又做出些意想不到的事来。你任团长又抓革命又促生产的,谋大事哩,顾不上这些小事。把齐翠花交给我万无一失。过一个礼拜,我马长林保证给你任团长交回来一个囫囵的齐翠花来。”
任立新心有余悸地说:“她只要死不了,就派人送回她们官泰公社红城大队去,省得麻烦。”
马长林连连摆手说:“这使不得,使不得。人是咱们揪来的,还没批斗哩,就出了这事。就这么送回去,群众还不笑话咱工作团。等把她的伤治好了,让她再当着群众的面交代一下问题,承认一下错误,检讨一下她自杀的错误行为,再把她交送回去。圆圆满满。”
任立新说:“只怕是她顽固不化,不肯认罪交代。”
马长林用手拍了一下大腿,干脆地说:“哎,这事你不用担心。她齐翠花就是个石头,我马长林也要让她开口说话。这事你就交给我。我用这盏马灯和这一杆老‘七九’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