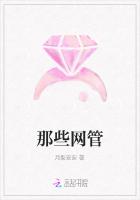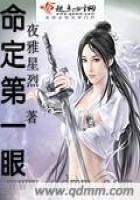因为已经到了放假的季节,即使叫最近的修理工来,也要两个小时,大家只得哈着气跺着脚,跑到附近的一家乡村酒吧去。
这家名为“湖前”的酒吧,有一百平米左右的面积,但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里面有着温暖的壁炉、柔和的灯光、舒缓的轻音乐。在寒夜的雪地中,乡村酒吧散发着迷人的光芒,让我们这些异乡人感到了温暖。
我们的到来几乎让“湖前”酒吧有些沸腾起来,要知道,这个乡村从来没有滞留过这么多外国人,更不要说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了。这家酒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曾断断续续地来过一些外国人,酒吧前台的墙壁上留下的各国纸币,就是一个见证——约3米长、1米宽的墙上贴满了各色的小面额纸币。不得不说的是,的确有太多国家的游客到过这里了,但中国人却是第一次。毫不例外,酒吧主人也要求我们留下一张本国的纸币,签上名,然后交给他郑重其事地贴在墙壁的上方。
令我疑惑的是,这个寂寥、偏僻的乡村酒吧,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游客经过?不,是怎么会有那么多不同国家的游客途经此地,他们出于怎样的原因和心境在此逗留?是探险,是猎奇,是受困,还是只为独享安静的夜晚?这些已无从猜测了。从另一堵墙上贴着的照片中可以隐约知道,这些过路人或是独自一人,或是带着家人和女友,或是和朋友前来。他、她,他们和她们,或有着幸福的表情,或有着黯然和神伤,或有着平静如水的安闲,这些并无例外的属于这个世界的表情,在这个乡村酒吧的一堵偏墙上定格着。
啤酒、炸鸡翅和薯条,就是这个夜晚属于我们的晚餐。十余个人的量,让酒吧一阵忙乱——他们平常很少集中接待过这么多的人。就在我们消费这些食物的半小时过程中,酒吧里断断续续来了十几个人,他们有的是这里每夜必来的老顾客,也有的因为我们而来——我们的到来已经在这个地方传开了——一群年轻的中国男女雪夜受困于此。但他们的好奇中仍带着一份恬然的安静,各自叫了酒,先与我们用目光交流着,然后与合适的对象静静地交谈,国家地理、风土人情、家庭工作,因为初次相遇而好奇,因为陌生而兴致勃勃。于是,这个酒吧显得十分热闹起来,我们也因此消除了沮丧和困顿,变得有些安宁和高兴起来了。
车子当夜已经无法修复,只得考虑第二天换辆车了。说实话,想想都后怕,这样的车子已经无法让我们感到放心。已经过了半夜,这里的人热情地邀请我们合影,然后陆续离去,酒吧里渐渐地又只剩下我们。在酒吧主人的帮助下,导游在当地终于找到了两辆车——一辆是十分漂亮的林肯,一辆是十分舒适的小型面包车。
可惜的是,这辆林肯的空调在路上发生了故障,我们好意将它让给所有的女同志,结果两小时后到达灰熊镇住下时,她们中已有一半人得了感冒。
乡村酒吧的这个夜晚,的确是令人难忘的。
无梦到廊桥
去看廊桥,多半是要带着梦的。
“她看了他不到五分钟就知道她要他,而他也是一生的感觉、寻觅和苦思冥想此刻都到眼前来了。”在小说和电影《廊桥遗梦》中,这样的情景打动了无数的男男女女。梦,多半就是这样如影相随的。
我去看廊桥,并不是寻找什么梦,而是为了看一看山岙深处那些延续已有千年的文化遗迹。那些与大山、与田野、与溪流、与人家融合在一起的带着屋檐的桥梁。那是我故乡温州的一处偏僻的景致,离我很近,又相隔很远。
当然,我还为了寻找一份宁静。
五天的时间,在泰顺的四个小镇,我看了八座廊桥。背着简单的行囊,悠然地在乡野间寻找住处,在清晨和黄昏,看那些雾气笼罩中或者晚霞辉映中的廊桥,你会觉得世界仍是安静和沉淀的。
但寻梦的人,一定要去看三条桥。
泰顺现存各式古桥梁500多座,其中保存完好的木质结构古廊桥有33座。泰顺廊桥唯一与爱情有关的记载,就若隐若现于三条桥内侧桥裙上的一首婉约词《点绛唇》中:
常忆五月,与君依依解笑趣。山青水碧,人面何处去?人自多情,吟吟水边立。千万缕,溪水难寄,任是东流去。
这首词的作者是谁,写于什么年代,都是无法探究的。从墨迹和书法上判断,这首词的写作年代并不遥远,我怀疑是今人之作,故地重游,多半是为了怀念两情相悦时的甜蜜和幸福,而今天地悠悠,纵思绪万千,东去的溪水已难寄这份相思了。
翻阅有关廊桥的为数不多的文章,多半可以看得到对这首词的解读和喜爱,可见来看廊桥的人是带着怎样的梦和遐想。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泰顺的廊桥有千百座,为什么偏偏只有在这座十分偏僻的三条桥上,才可以看见与爱情有关的文字,而且还带着这么神秘的色彩?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试想,作为交通、集市和祭祀的场所,廊桥是多么难以在闹哄哄的民间留下爱情的传说啊,就连惊慌的幽会、匆忙的私奔和片刻的聚散都难以容身!而只有除却了喧闹的集市声音,唯留了溪水的宁静、鸟鸣的清幽、山风的闲淡,才有了时空体会人间的美好情怀,才可以静心面对相悦的欢爱。爱情的私密性正需要这样一座不食人间烟火的廊桥。
去看这样一座廊桥,是需要耐心和情怀的。
从小镇三魁驱车近一小时,才找到一条从半山腰开辟出来的崎岖山路。下车穿过一块稻田,再沿着一段古朴的青石板路行走十几分钟,终于可以看见两山峡谷之间,郁郁葱葱的绿色中突然出现的一条蜿蜒曲折的清澈溪流。顺着水流的方向拐过山梁,远远地才可以看到横跨于崇山峻岭之间的三条桥,几经风雨的桥身带着浓重的沧桑,散发出宁静幽远的古韵。
据泰顺县志记载:“此桥最古,长数十丈,上架屋,如虹,俯瞰溪水。旧渐就圯,道光间里人苏某独力重建,拆旧瓦,有贞观年号。”又据泰顺县文物部门考证,三条桥“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宋绍兴七年(1137)九月十三日重建,现桥清道光廿三年(1843)建”。可见年代的久远和世事的沧桑了。
与雍容华丽的泗溪姐妹桥不同,三条桥没有大红大绿的色彩,只有纯净质朴的本性,只有斑驳、古拙的意味。八个小巧玲珑的白色翼角伸向天空,才给整座廊桥增添了灵动的气质。由于常年栉风沐雨,原来的土色泥瓦渐渐变黑,三折桥裙本应是原木色,现在也变成了灰色,只有少被雨淋的地方才露出木色。四十根圆形桥柱,两根一组,依次排立在桥面的两边,两根柱子间上下各由两根稍小的横木贯穿,呈“井”字形。又有四十根巨大的横梁分两层,上下左右压在柱子上。这样众多的“井”字结构,牢牢将廊桥的各个部件连接在了一起,使这座古老的廊桥历经数百年风雨而不倒。桥面则由硬木巨板铺就,由于未受风雨侵蚀,硬朗依旧。人走在桥上,发出“咚咚”的声响,很深沉,很古朴。廊桥尽头则是一座观音土庙,香炉里插着蜡烛,依稀可见从前浙闽商贾、挑夫走卒行色匆匆的景象,给菩萨烧香磕头,正是为了精神上得到抚慰。
我去看三条桥的时候,三条桥上没有其他的人。两旁是高山,满眼是翠绿。三条古道依旧清晰,东面一条通往三魁,西面两条,左边的通往溪,右边的通往洲岭。三条古道由一条廊桥连在了一起。桥下则是碧绿的溪潭,潺潺的流水过处,满眼是圆溜溜的巨石。坐在溪石上抬头望这座廊桥,淡淡的清风袭来,伴着清新的山野气息,令人生出“前不见来者,后不见古人”的感慨。
三条桥静静地守候在寂静的山谷中,就像孤独的灵魂静静守候着黎明与黄昏。这座桥是那样的纯净,纯净得有点孤高,孤高得有点凄清,凄清得有点让人动了恻隐之心。这里的青山绿水,是这座廊桥孤独的闺房吗?
这座清新脱俗的廊桥,是不是有着无边的哀怨,和着荒无人烟的山野溪涧,和着流水声、鸟鸣声,一起构成了一个凄美的意境?
一首《点绛唇》,显然是难以道尽个中滋味的。曾经的记忆都湮灭在无情的历史中了。
也许,廊桥本来就无梦,寻的人多了,于是就生出了很多梦吧!
顺道去永嘉
那年七月,因返乡之故,顺道去了浙江永嘉的楠溪江。行至瓯北转车复行两个多小时,至永嘉岩头镇。这两个多小时的行车,始终与大江为伴,因为公路依江而蜿蜒,便少了暑气。车子越往里开,山水越见秀丽。少了人家,也少了人,风景这才本真起来。真真切切的山和真真切切的水,一左一右。山是普通的山,当然不如昨天见过的雁荡美丽,可因为依了这条大溪,顿而秀美起来;大溪似巨蟒,卧在鹅卵石上,似乎在听什么动静。有诗这样写道:“水是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细细回味间,车子开始盘山,巨蟒像在甩身,左甩右甩,就是不见首也不见尾。车子还需深深地往里去,我突然很觉神秘起来,这山和这溪,竟都是不见底的。
因为是自助旅行,事先便作了研究,把落脚点选在岩头镇。近可去芙蓉村、苍坡村这些古村落,远可去石桅岩,返可至狮子岩,十分合理。
岩头镇是个有些脏乱却令人感到亲切的小镇。熟悉的脚踏三轮车,满街满巷地窜着;火柴盒一样连过去的楼房,见缝插针地布着小酒楼、私人旅舍。与我从小生长的浙南小镇相比,大不一样的是这里狗多。真是呀,满街满巷的狗,品种并不名贵,多为草狗。狗不怕人,也不咬人,悠然自得地串门、逛街,俨然是这里的主人。大狗小狗冷不防就在你的边上或后头溜过,这架势多半还是有些吓人的。谁会见过这么多狗呀。小时候我在农村生长,一村不过数狗,此处却多得不可胜数。女友怕狗,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无狗的摊头买水果,买好付钱,脚下突觉有毛茸茸的东西,定睛一看,是一条胖乎乎的小狗。再一看,不得了,摊头下有七只胖乎乎的小狗,坐立横卧,姿态不一。付完钱刚要走,里头又跑出一只。想必这里的人都爱狗,而此家主人为最。我们原想找一处无狗的摊头,却跑进了小狗之家,不觉哑然。
夜晚的小镇,并不热闹,安静,也很暗,狗还是多,街面十分脏乱。经人推荐,我们去了旧区的丽水街。这里更安静了,如若没有一排沿河挂过去的灯笼,简直让人摸不着路。一排人家,一律是尖顶的矮房,前面是廊棚。这在江浙一带并不少见,比如江苏的木椟和我的家乡缪家桥。再前面是河,蛙声漫了上来。不过夜里七八点,这里却无人声。一些屋内的灯还亮着,人影憧憧,是平静的乡村生活中的忙碌。沿着窄窄的小道往前走,才发现廊上睡了不少人,以年长者居多,有的还摇着葵扇,另一些则明显睡着了,发出了鼾声。短短的走道过后,回过身再看丽水街,丽水街仿若漂浮在河上的一艘船,船两侧的灯笼轻轻地在风中碰首。
第二天一早,我们雇了一辆三轮车去附近的芙蓉村和苍坡村,在《楠溪江中游古村落》一书中,有芙蓉村和苍坡村较为详尽的介绍。不过芙蓉村终究还是一般。
在浙南的一些村落中,像芙蓉村这样的民居并不少见,我的亲切感即在于,来此仿若回到了小时候的村庄。芙蓉村是齐整的,也是破败的。说是齐整,是因为整个村子成方成块,小路也是平直的,把村落分割成些更小的方块;说是破败,是因为房子中有一些已塌了部分,荷花池内也不长荷花了,蹲着三五条水牛,池水污浊不堪。诸如此类。可也因为破败,这里随意处置的古建筑、旧家什,以及落后的劳动工具,才更加令人怦然心动。
苍坡村却不寻常。在一大片原野中,围墙突然圈出了一个村落。从写着“苍坡村”三个大字的门楼进去,荷花池照旧,望兄亭依然,按照文房四宝形状排列的建筑格局也保持着原貌。村民们依旧和睦地生活在村中,除了村长家的两间新瓦房,其他房屋一律是旧式模样。
村口一个好大的祠堂,从戏台子可以看出曾有的兴旺。
因为是夏日的午后,祠堂的走道上贴地睡着一些老人,更多的人则去了附近的望兄亭,在浓荫处乘凉。走上望兄亭往墙外看,一条小路蛇行而来。可惜,望兄不见兄,望兄亭内的弟弟,也早成了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