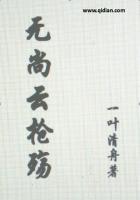或许是因为他们同情心泛滥,也或许是他们好奇心作祟。仓颉和米粒儿最终没有杀掉流光虫,而是让它指引方向,去见一下它所谓的白大人。
看着地上躺着的斑斓蟒尸体,仓颉就无比羡慕查易和仓玉儿了,整个部落,就他们两个人的神器自成空间,可以方便的携带许多东西。
可是他的血牙却没有这个功能,由于妖兽体质的原因,身体都很重,斑斓蟒虽然只有成人胳膊粗细,但是却很长,如果戴在身上很是不便。仓颉只能就地掩埋,等回来的时候,在带下山去。
有了流光虫的带路,他们前进的速度快了许多,周围再也没有随便窜出的妖兽。
渐渐的他们靠近了山顶,米粒儿的情绪慢慢的又低落了下去。
前方就是她父母的尸骨埋葬地,由于种种的原因,她却不敢来到这里,哪怕她的父母为她而死,她也只能在远方默默地思念。
这次如果不是仓颉的带领,她仍然无法到这里来。
有一次,米粒儿偷偷的飞了出来,准备从高空,直接飞入山顶,去看一下她父母的情况。
可是,事情并不是她想的那么简单,虽然她拼命的往上飞,可是她却只能在白云之下打转,甚至都无法飞入云中。
而那大山在白云之上,还有很高很高的一部分。
米粒儿垂头丧气的回到了部落,仓颉也是在那时候,发现米粒儿在偷偷的思念她的父母。
那时候米粒儿已经融入到了他家,仓玉儿很是宠爱米粒儿,甚至都把它当女儿看待。所以仓颉刚能完全召唤血牙,就带米粒儿来到这里,探查她父母的情况。
山顶已经在望,现在的山顶,和五年前比起来,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样子了。
五年前一场大战,山顶完全破碎,那六只当康,不知从哪里掀来了一个巨大的石壁,盖在山顶,整个山顶看着光秃秃的怪异。
也就是那时候,查易在巨石的缝隙中,种下了无数的植物,那是查易在高山植物中采集的种子,生命力相当顽强。
五年后的山顶郁郁葱葱,无数高大的植物矗立其上,那些稠密的植物,也许是为了争取阳光,竟然比其他地方的植物长得更高。
“这些植物完全不像五年的样子,即便有养世决的滋养。”仓颉对着米粒儿说道,“你问问那只流光虫,它的白大人是不是在那片丛林里?”
米粒儿正打算问流光虫,这时候一个白影窜出了密林,只是在枝叶上点击了几下,便来到了远在数百人外的仓颉边上。
那是一直白色的巨鹿,高两人开外,长三人有余,一身白色毛发,柔软光滑,它体型虽巨,却现婀娜之态,轻盈无比。
细看那白鹿,它的头上有四只鹿角,温润如玉,闪烁毫光;它的脖子有一层厚厚的白色绒毛,那绒毛蓬松柔软,使它看起来雍容华贵;它的腿上有红色细丝般的纹路,纹路中似有蓝色的光华闪现,又使它看起来神秘无比。
那白鹿看见仓颉在不停的打量它,不耐烦的说道:“你这人类好生无理?”
“白鹿?你就是它口中的白大人?”仓颉一指边上瑟瑟发抖的流光虫说道。
只见那白鹿眼中凶光一闪,旋即又恢复了平静,微怒道:“你可以称呼我为白大人!我的名字叫白灵!但你不能叫我白鹿!我是夫诸!夫诸一族不是白鹿那等低贱的种族可比!”
那白灵说着还微微点点头,显得绅士无比。
“额!白大人!”仓颉一阵的错愕,没想到他竟然碰到了如此极品的妖兽,明明眼中闪露凶光,却又装的如此高贵。
“白大人!你救救我吧!我是被逼的!”流光虫眼漏恐惧神情,吱吱的叫到。
仓颉不明白流光虫干嘛,但是米粒儿可是知道的,一把抓向流光虫。
正在这时,那夫诸头上尖角闪出一阵蓝色水汽,那水汽快若流光,竟然抢在米粒儿小爪之前,包裹住了流光虫,逃遁而去。
流光虫拼命的点头,不停的发出吱吱的声音,那是向夫诸道谢。
夫诸面漏迷人的笑容,最起码仓颉是这么认为的,那真的是很诡异,你竟然能在一只鹿脸上看出笑容。
流光虫看到那笑容,更加恐惧了,点着头缓缓的后退。
“谁说我是救你了?你是我的奴隶,犯了错也应该是我惩罚你!与别人无干!看你诚心认错的份上,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不要啊!白大人!你放过我吧!”流光虫拼命的哭泣道。
夫诸高傲的看着流光虫,那些白色的水汽中,骤然钻出一个蓝色的冰刺,那冰刺纤细如丝,冷冷的刺入了流光虫的体内。
原本如此细小的冰刺,刺入体内,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的,可是那流光虫眼中,却露出了悲伤而疯狂的神情。
“白大人,我伺候你没有六年,也有五年了吧!”流光虫直视着夫诸平静的说道,“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就因为我把外人带到这里,你就破掉我的妖源!”
“啊!”米粒儿一声惊叫,赶紧用翅膀捂住了小嘴,惊恐的看着夫诸,心中暗道,这夫诸也太狠毒了吧,如若看不惯杀了就是,破掉妖源就相当于,毁了流光虫作为妖兽的根本,让流光虫成为一个有灵智的,却又人人可欺的野兽。
有时候死亡并不能让人恐惧,最让人恐惧的,便是那种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却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
夫诸微笑的看着流光虫,随意的说道:“你们这小虫子,原本是春生秋死,我让你们多活了那么长时间,还不是对你们的恩赐么?”
“哈哈哈哈哈!恩赐么?这些年来,哪一天,我活的不是兢兢战战,为你服务我们可曾有一点自由?如果这是恩赐,我宁愿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小虫子!”流光虫一阵狂笑,疯狂的说道。
要是平时,即便是借给它一百个胆子,它也不敢这么和夫诸说话,这也许是它最后的疯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