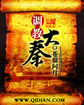下午桑塔纳歪歪扭扭地载回了老板。看来一切顺利。老板一身的酒气。
车队准备进城,却发生了状况:一个打杂的小青年不见了。柔术师拷问了一番,得出结论:这个家伙昨天和同伴玩扑克输了钱,可能是为了赖掉赌债,跑了。柔术师拷问的手段让驯兽师长了见识:他命令那几个打杂的站成一排,自己拎一根小皮鞭,检阅一般地在他们面前踱步,小皮鞭出其不意地从各种刁钻的角度偷袭过去。柔术师使用了自己的专业技能,拎着鞭子的那条胳膊,声东击西,匪夷所思地抽在人身上,造成的疼痛,都远远不及那种令人防不胜防的惶惑有威力。很快就水落石出了。有个打杂的还额外交代说,潜逃者是蓄意的,他早就不满老板对他的克扣了。得出了结论,柔术师就若无其事地蜷进了车里,有种甩手撂下烂摊子的味道。
老板一直扶着一棵树在吐酒。他听到了最后那句交代,止住呕吐,错愕地看着自己手下的这班人马,脸上却是完全被委屈了的神情。最令驯兽师难以接受的是,桑塔纳居然依旧由老板来驾驶。他艰难地爬进车里,一边脸色煞白地压着酒嗝,一边抖索着发动引擎。
车子顿挫了一下,向着前方勉力冲去。
驯兽师的心莫名地焦灼起来。起初他还能够说服自己,力图让自己松弛一点。毕竟,坐在一辆酒鬼驾驶着的破车里,谁都会有一些不安。但是,渐渐地,他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驯兽师听到了狮子的呜咽。相伴多年,驯兽师听得懂狮子的每一种叫声。现在,飘在风中的那一声声低鸣,在驯兽师的耳朵里,就是狮子的哭声。狮子怎么了?莫不是那群京巴狗冲破了两道铁笼,正在群殴一头狮子?怎么会!可驯兽师的心却愈加忧急。狮子的呜咽在风中时强时弱,偶尔颇为惨烈。驯兽师不断将头伸出车外,透过马路上的扬尘回望身后那辆加长的卡车。连身边的小丑也跟着不安起来,嘀嘀咕咕地吁叹:
“赖印——呃——赖印!”
驯兽师要求停车,他要下去看看狮子。这时候车队已经进入了县城。酒后的老板依然能够摆出回绝驯兽师的理由。他一边吞咽着口水,一边说:
“开玩笑,怎么可以在马路上看狮子?吓着交警可不是好玩的!”
狮子的叫声停息了。风中只有渐渐嘈杂起来的市声。
老板已经落实了演出的场地,车队直接驶入了县城的体育场。停车后,驯兽师迫不及待地去探望狮子。车厢里一片阒寂。骆驼们,猕猴们,狗们,共同制造出一种陌生的、压抑的、消极的、还有充满悲戚情绪的宁静。狮子侧伏着,头颅浸泡在一滩浑浊腥臭的呕吐物中,显然是,死了。
一瞬间驯兽师觉得自己和车厢一起飘了起来。猛可冲进他脑袋里的,是他曾经教给儿子的绕口令:
山上有个死狮子
山下有个涩柿子
死狮子吃了涩柿子
涩柿子涩死了死狮子
屈指算来,这不过是驯兽师和狮子上路的第二天。
驯兽师的心神飘在遥远的地方。倒是老板如丧考妣。他用来租借狮子的那十万块钱,现在大概还余温犹在,狮子,却已经凉了。沉郁的柔术师又一次拷问那几个打杂的。他似乎也厌倦了,有气无力。因为事实俱在,基本上不劳他来追究。一目了然,是那个潜逃者用半只鸡毒杀了狮子——它是马戏团里最值钱的一笔资产。
暮色四合。女人在指挥那群狗从骆驼的身下钻来钻去,驼峰上立着呆若木鸡的猕猴。小丑两腿骄矜地迈着方步,嘴里喃喃吟哦:
“赖印——呃——赖印!”
而驯兽师,此刻脑袋里的绕口令已经升级到了这样的地步:
山前有四十四只小狮子
山后有四十四棵紫色柿子树
山前的四十四只小狮子吃了山后的四十四棵紫色柿子树上涩柿子
山后的四十四棵紫色柿子树上的涩柿子把山前的四十四只小狮子给涩死了
驯兽师突然格外想念自己的儿子。儿子在他的记忆里向他发问:
“死狮子……怎么吃柿子?”
这个问题一度折磨过驯兽师。那时候,他不过是一名饲养员,只负责喂养动物园中的大型猫科动物。最先是老虎,后来是狮子。没有人要求他来驯兽,发情期的狮虎常常打架,死了也不会有人追究。实际上,他完全是为了博得儿子的欢心,才开始这么做的:将肉叉在棍子上,逗引狮子来吃。一次次抬高棍头。终于,狮子会随之跳跃了。后来,狮子越过了竹圈。再后来,竹圈换成了火圈。如果此刻驯兽师的心神能够落在实处,他会为自己最初将肉叉在棍子上的那一刻而后悔吧?
老板确凿无疑在后悔。他的酒彻底醒了,使劲踢了一通桑塔纳的轮胎。现在折磨他的事实是:他的十万块钱不到两天就打了水漂。如果狮子是另一种死法,老板会立刻调转车头去向动物园追讨他的十万块钱。但狮子死在老板自己人的手里了。反过来,动物园还有充分的权利来向老板索赔。眼前这个神不守舍、瞳仁中浮映着往昔岁月的驯兽师,就是动物园的代言人,是一个债主。老板过来拍拍驯兽师的肩头,欲言又止,顿了顿,又走开了。
驯兽师怔忪地看到小丑在对着他笑。笑中杂糅着一个小丑特有的悲伤和嘲谑。他看到背对着自己的柔术师出神入化地朝他伸出了手,像是一个来自正面的拥抱。那双无影手在他的鼻子前轻抚而过,悠悠扬扬的气味如同食物一般哽塞了他的喉头。驯兽师倒下去,感到天空翻转了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