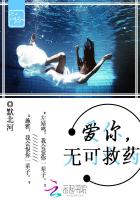第二件,是发生于我们二连的事。
那时候我是新兵和部队其他人住宿舍的第一层楼,最里面的房间是最阴森,阴暗的。
有次老班长说,以前他刚当班长时也住这个房间里,发生过一些事情,他说他一辈子也不会忘。
是一个月光暗淡又朦胧的晚上,房间里很暗最多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
到了半夜,是几点,他已经不记得了。
有个老兵,当时和老班长住一个房间的叫卡卡,他在几天前请假回家有事了,至于是回去干嘛他也不清楚。
卡卡这名字不是他的真名,他其实是姓李,卡卡是老班长给他取的外号,而名字里面的故事就是另一个喜剧故事。
当时部队的很多人都有外号,因为班长喜欢给别人取外号,也是为了消遣时间吧!毕竟部队里除了训练就没什么了,有时真的挺枯燥的。
班长那天晚上睡着睡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就醒了,就是那种睡到一半突然睁开了眼睛,自己也不清楚原因,相信应该很多人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吧!
他眯了眯眼睛,正准备倒头继续睡,就在他挪腰的时候,就看到卡卡的床铺有个人坐在床上。
因为房间太黑,他转头也只能看见那边下铺有个黑黑的影子。
班长以为是卡卡回来了,就问卡卡:“大晚上的坐着干嘛!赶紧躺下睡觉!”
一句话说完,班长以为卡卡就会像平时一样听到指令乖乖睡下去,结果他去看时,那人影就像是没听到他的话一样,还是笔直的坐在那里不动。
班长以为卡卡是迷糊了没听到,于是就更大声的说:“卡卡!你听到没有,我叫你给我躺下睡觉!!!”
这时候,班长上铺的副班长被他吵醒了。
副班长起身准备问班长半夜在喊什么,刚睁开眼就看到了隔着一个床铺的卡卡的床上有个人影坐在床上。
他的喉咙一下子就跟被人掐住一样,准备叫班长的那句话被打断了。
副班长是知道卡卡回家去了,他想了几秒,觉得不可能,卡卡要是回来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班长不知道可能是开会去了,想想他还是觉得奇怪,开口跟下铺的班长说:“卡卡他不是回家去了吗?”
班长听了副班长的话后,才觉得不对劲,卡卡回去了他是知道的,可是他要是回来了他怎么不清楚,真是睡傻了。
明白过来后的班长跟班副两个人一下子就都慌了,等两人再去看卡卡的床铺的时候。
两人瞬间全身汗毛树了起来,内心的恐惧肆意疯长,好长的时间两人连话都说不出来。
只见原本一直都不动的人影,这时候居然转过头来了,静静地盯着班长和班副两人,就像是一个有思想的生命体在看着他们两人。
可那个人影到底是不是卡卡?如果是,为什么他回来了,自己不知道?
如果是卡卡,为什么听到了自己的话不乖乖睡觉?难不成卡卡有梦游症?
可那也不可能啊!以前也没听卡卡说他有梦游症啊!
可如果不是卡卡的话,那会是谁呢?
转头看看其他床铺,其他人都在呼呼大睡呢!自己也不是在做梦啊!
班副回过头来和班长对看一眼,班长此时开口了:“道贵!那个,卡卡是不是还没回来啊?”道贵同样也是他自己当时给班副取的外号,他向班副再次确认道。
“是啊,班长!”道贵很确定的回答道。
“那那个人是谁阿?”班长的声音变得有一丝的颤抖,他再也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恐惧了,他觉得此时的自己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
班长当时没想到,他这句话问出来后,空气,时间就像是被凝固住了一样。
突然间,一切都变得那么的诡异,这种情况根本就不能不让人往那方向去想啊!
“班长,要不我们先别理他,睡醒到早上的时候再说吧!”
班副道贵的声音传入了班长的耳中,他忽然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好办法!
他和班副道贵同时钻进了被子,猛的用被子严实的盖住了头,两人都没再说话了,一切还是那么的安静。
过了没多久,当班长已经缓了会儿后,发现周围还是那么的安静,他开始有了一丝的怀疑。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看见了什么?
他怎么可能会看见那种东西,会不会自己其实是在做梦?
当他透过被子的缝隙再去看卡卡床铺的时候,背脊瞬间冒出了冷汗。
只见那个人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已经双脚站了起来,就立在床上,一动不动的盯着他和班副道贵的方向。
班长吓得赶紧蒙住了被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将自己严严实实的蒙了起来,可也就那样迷迷糊糊的就睡到了早上。
到了早上的时候,宿舍里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班长那个房间除了请假的卡卡,其他七人包括班长,副班长道贵全都集体发烧感冒了。
虽然发烧并不严重,但当时还是在宿舍里传开了。
事后,班长和连长说了这诡异的事情。
最后连长听完了之后却是把班长给训了一顿,说的当然是那些,当兵的还迷信,胆子这么小怎么行等等的话。
连长还和班长说没事不要宣扬这些有的没的,这事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我听班长说了这事后,也被吓得不轻,有段时间我是一挨床就睡,夜里也是除非尿急才会起床。
而听了这事得当天晚上我也是第二哨,站哨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虽然站下来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在时间慢慢过去的时候就总觉得身边阴风阵阵的。
关键还是大夏天的晚上,那天晚上却觉得特别凉!
那晚,月光皎白如雪,大地就像被蒙上了一层白雪一样的明亮。
时不时的不知道从哪里冒出几声猫叫,当时是吓的我心慌慌的。
要不是知道部队总有那些养狗养猫的人,指不定我也会被吓出一身冷汗,而我就总觉得那一哨是我有史以来最漫长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