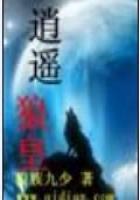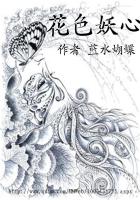苏旷几乎哀求道,白容,念在我与苏国昔日待你不薄的份上,请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么。白容一拍旁边的椅子,冷冷道,过来罢,苏公子,不用我说,这好戏也会告诉你潼涧究竟发生了什么,苏旷听她如此说道,不再多言,径直其身旁坐下,白容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才乖嘛。将手一拍道,可以开始了,紧接着,一名手执黑色丝帛的营士官跪奏道,禀公主,今昨两日,从各地捕获漏网叛逃将官二十名,其中将军两名,副将八名,参将六名,王宫带刀侍卫一名,文官三名,白容随意地拿起名单,朝上扫视了一眼,淡淡道,斩无赦。诺,那名士官领命而去,随即,震天的擂鼓响起,一众囚犯被押解出来,被绑至校场前方的铜柱上,苏旷一见,猛然目恣欲裂,大叫道,住手,白容,快叫他们住手,白容冷冷一笑道,苏公子,干嘛这么激动,这些人犯了叛国潜逃之罪,不处死不足以偿其罪孽,苏旷猛然站起,嘶声道,不可能,决不可能,高叔叔侠肝义胆,守卫王宫二十余载,忠心耿耿,乃是父王的贴身护卫,是最值得信赖的人,还有王权涣伯伯,身为苏国的工部尚书,一生为国,可谓是鞠躬尽瘁,沤心泣血。他们是不可能叛国的。白容优雅地伸了伸蛮腰,轻轻道,谁告诉你他们不可能叛国,只不过这个国字的涵义在你我心中可能有些差别,不妨告诉你,你父亲统治的苏国已经烟消云散,现在的苏国更名为九黎国,哼,这些苏国余孽,不肯归附我新建的九黎国,四处逃逸,妄图东山再起,这不是叛国之罪又是什么,啊,苏旷只觉大脑猛地一轰,一时间有如短路。张大的嘴竟合不拢来,这么血淋残忍的事情自此女子口中轻然道来,顷刻之间他如何能接受,昔日那个安宁平和,广受万民称颂的苏国怎么说没就没有了呢,陡地一声嚎叫从苏旷嘴中发出,好似杜鹃啼血,声音凄厉,让人不忍卒闻。一缕血丝从他嘴角边淌下,双腿已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哀泣道,告诉我,快告诉我,我的父王呢,我的母后呢,他们现在怎样,白容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却不作答。苏旷衣衫散乱,如疯子入般,跌跌撞撞地翻下校台,连滚带爬地来到左首第二个铜柱前,紧紧抱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嚎哭道,王伯伯,告诉我,快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了,那老者一见苏旷,原本面如死灰的脸上顿时泪如雨下,嘴巴大张,吱吱呀呀地,却是完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有鲜红的血流正从其嘴巴内汩汩而出,苏旷凄然瞧去,见那老者的舌头不知如何竟然短了一截,显然是人为割断。满怀怨恨的他狠狠向校台上的女子狠狠盯了一眼,又转身来至第五个铜柱下面,紧紧抱着一个身形挺直,浑身血迹斑斑的青衫汉子,苏旷泣哭道,高叔叔,你受苦了,快告诉我,潼涧究竟发生了什么,那汉子本来一副凛然就义的决决模样,见到苏旷,脸上焦急之色大起,浑身衣裳无风自动,一股股肉眼可见的青色气流在全身上下急速游走,四肢皮肤不断地裂开,绽出血来,只听铮的一下,那紧缚于他的拇指粗细的铁链竟为其一绷而断,青衫汉子一得自由,探手抄起苏旷,负在背后,就欲往校场外行去,而手指也没闲着,不住在苏旷背上勾勒,苏旷仔细感受着背后的痕迹,分明是公子,逃命为上,苏国已不复存在,皇上已陨,主母下落不明,这消息如同利刃般将苏旷心中最后的一丝幻想斩断,呜呃一声,有如野狼般的嚎叫从其心底最深处发出,陡地昏死过去,然而转瞬间他又醒转,一双血红的眼睛侧过头去,死死地瞪着校台上的白容,而双腿更是乱踢,泣哭道,高叔叔,快放我下来,我要报仇,我要报仇哇,然而,青衫汉子的手更加抓紧,身形展开,就往校场一角行去,而这时,周围的兵士刽子手们已合拢上来,青衫汉双腿一盘一旋,身子已经凌空而起,空中俯折,一个旋风八打,最先围上的几个兵士纷纷被踢中胸口,只听得嚓咔骨胳破碎的声音响起,他们手中的武器先后抛落,青衫汉子单手抄起一柄钢刀,精神陡地一振,指东打西,挥南扫北,顷刻之间就将合围的圈子扫出一个缺口,试图突围出去,而众多的兵士们已源源不绝涌至,青衫汉子将手中钢刀挥洒得淋漓尽致,上磕下挡,左冲右突,偶尔刀身一个闪烁,手中长刀竟然脱手飞出,一个回旋,带起七八蓬鲜血,再回到其手中,然而尽管青衫汉神勇无比,无奈兵丁太多,而苏旷在背,更是一个大大的破绽,有好几次,当枪戟刀刺等武器将要击到苏旷时,青衫汉照护无力的情况下,就用自己的身子硬生生挡住,不多时,其全身上下伤痕累累,几成为一个血人,苏旷在其背后焦急道,高叔叔,快放下我,不要管我,独自逃命去啊。然而那汉子哪里肯听,猛地一声嘶吼,生生咬断舌间动脉,漫天血雨四下乱射,有如一粒粒细小的钢珠,手中长刀亦化作无数碎片,四处散开,如此威势之下,前面的兵士纷纷倒地,噗的一下,合拢的圈子终于再次被打开一个口子,从那里已经能够看到校场尽头,青衫汉咳嗽连连,步履蹒跚,想是奋力施展某种秘法,一时已呈强弓之孥势头,然而,剩下的兵士为其气势所夺,一时俱不敢太过靠近,眼见着出口越来越近,汉子的脸上现出一丝喜色。就在这进,校台上一直冷漠观战的白容见状,站起身来,好整以暇地伸出手道,拿我的雕牙馔玉弓来,是,公主,旁边的一位婢女双手递过一张玲珑玉弓,白容纵手抓起,从背后箭袋中抽出一支箭来,脚在帐台上稍一借力,人已腾空而起,穿破杏黄旗帐,空中弓似满月,箭似流星,向着青衫汉子射去,这时,青衫汉与主帐台之间的距离已足有数百丈远,远超寻常箭孥的射程范围,铜柱之上的王权涣见那箭势虽快,但却似乎偏离了苏旷他们少许,心中担忧之情稍缓,而那箭矢也恰如他料想的那样,在两人身边一飞而过,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箭矢在前方百米处竟然转过弯来,当胸就向着青衫汉子射去,刚刚透体而过,而箭势已尽,没有伤到背后的苏旷一丝一毫,苏旷心知其手下留情,鼻子一哼,青衫汉子颤声道,好可怕的弓孥之技,高某心服,只可惜……..,话未说完,人已倒地而死,这时,后面的兵丁早已一拥而上,将苏旷重新押至主帐台前,白容一脸挪揄地笑道,还不上前谢我饶命之恩,苏旷大喝道,要杀便杀,谁要你这假惺惺姑在此作态,你这个狼子野心的蛇蝎女子,连我的父母也不放过,我恨不得喝你的血,吃你的肉才好,想到父王母后,苏旷忍不住悲从心来,伏在地上一时嚎啕大哭不止,白容似乎颇有耐性,丝毫也不来打扰他,待他泣哭完毕,冷冷道,的确,你也不用感激我的留手之恩,你苏家从来只是把我当成兵戎止戈中的一枚棋子,我自然也不会将你苏旷放在心上,何况你本性懦弱,手底又无缚鸡之力,实在不令我喜欢,如今你苏家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我不会有丝毫怜悯,苏旷恶狠狠道,你这个歹毒的女恶魔,所有这一切不是你一手造成的吗,现在偏偏还有脸在此说风凉话,白容冷然道,不错,苏国的灭亡与我九黎部落有莫大的关系,但始作俑者并不是我们,你父亲突然毙命,苏国群龙无首,这才给了我九黎部落可乘之机,苏旷怒喝道,你胡说,我赴考西京之前,父亲还好好的,而且父亲平日身体康健,怎么会突然暴病,分明是你借机害死的,白容叹了口气道,苏公子,现在形势是我强你弱,我还用得着拿话来骗你吗,况且,你刚才哪只耳朵听见我说你父王暴病,他的死乃是突遭横祸而死于非命,与我乃九黎部落一点关系都没有,突遭横祸,苏旷悲愤莫名道,那么敢问白大公主,我父王遭遇了什么样子的横祸呢,白容道,据说你父王乃是为一道从天而降的剑光削去首级,连人头亦不翼而飞,只剩下一具囫囹不全的尸首,苏旷气愤至极地指着白容道,好你个歹毒妖女,你就算是骗,也找个可信的谎言来骗好了,王宫戒备森严,怎么会有从天而将的剑光,难不成是鬼在作法么,提到鬼,苏旷突然觉得自己的底气低了许多,联想到自己此次西京之行中的诸多见闻,突然觉得世事难料,这种情形也并非完全不可能,还有酒仙前辈曾无来由地对自己说过一句话,你和令尊是不是长得很像,现在回想起来,这其中有很大的疑问,酒仙前辈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呢,正费神思忖间,听得对面的白容无所谓道,信不信由你,是或者不是我在造谣生事,你介时回到潼涧后,稍一打听就会明白,当时,你父王正在朝堂上议事,被取去首级时,有诸多文武百官在现场,苏旷咬牙道,文武百官,恐怕被你杀戳得差不多了吧,白容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放心,文武百官中,还有许多识时务者,并不象你的高叔叔,王伯伯般顽固不化,他们自然不会有事,你向他们打听就全都明白了,苏旷嘲弄道,这么说你会放了我,白容哑然道,放不放你,对我来说,又有何影响,你苏国大势已去,而你,手无寸劲,文弱没用,更是如同蝼蚁般的存在,念在我来苏地之后,你们苏家待我尚自不薄的份上,留你这条贱命在世间苟延残喘好了,只是这仇,今生今世你是注定报不了了,苏旷漠望其良久,复低下眼睑,深深地叹了口气,或许你说得很对,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我父王遭此无妄之灾,朝廷动荡不安,只在数日之间,你们九黎部落把控时机为何如此之准,难不成久有吞并我苏国之心,由此看来,你九黎部落将你送至我苏国和亲,乃是一酝酿已久的阴谋。白容俯视着苏旷,冷冷道,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你就好比沙汀上的小鱼,再也翻不起丁点儿浪花,说给你听又何妨,你苏国地大物博,兼且你父王仁义爱民,广积德政,我九黎虽多次搅挠你苏地边境,也只是本着即搅即走的游击战略,真要以部落之力与你苏国相较,十不及一,故而,谋夺你苏国的意图决不会有,怎奈天赐人愿,老天无端端赏下这块大蛋糕,我九黎也没有拒之门外之理,你父王遭此不测之际,朝中自有心怀叵测之辈,意图颠覆朝政,只因自身羽翼尚未丰满,唯有借我九黎部落之力。
同类推荐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