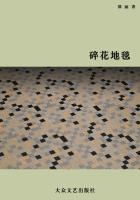由于无须接见内外命妇,乔津亭遂命宫娥为她随意妆扮,尽管是闲时服饰,但也是六幅绛色湘裙委地,裙摆绣就金色牡丹,灿然开放,富丽繁华;翠鬓挽就高髻,玳瑁斜插,步摇微颤,款款行移之间,长裙生动流畅,体态婀娜修长。
迎上宇文川远赞许的目光,扬眉一笑,“怎样?还好么?”
“皇后,朕是不是该说得此天人,此生无憾?”宇文川远大笑,起身拉住乔津亭的纤手,“来,进膳吧,你也饿了!”
帝后对面而坐,乔津亭见御案之上,各色膳食约有数十种,玉碟装就,色泽鲜艳,甚是诱人。
宇文川远举箸,细心为乔津亭布菜,“来,多吃一些!”
转眼,眼前玉碗食物渐堆渐高,青红黄紫,各色齐备。乔津亭有些无奈地放下手中玉箸,“太多了!”
宇文川远不依不饶,无视乔津亭娇嗔的斜视,笑着继续往她碗里添加食物。
不多时,泠弦手捧一方雕花檀木制就的盒子进来,见礼完毕,对乔津亭说:“姐姐,昨夜有人送来贺礼,于叔今早就让人送进宫来了!”
宇文川远深知乔津亭与泠弦等人情意弥坚,见泠弦仍是往日称呼,也不以为意地笑了一笑,倒是泠弦从宇文川远的笑容中回过神来,不由脸一红,屈膝赔礼,“皇上、皇后娘娘恕罪!”
乔津亭一把将泠弦扶住,横了宇文川远一眼,转向泠弦,“泠弦,我还是喜欢你叫我姐姐,不生分!”
望了一眼宇文川远,泠弦抿嘴微笑,低头不语。
“罢了,就照你姐姐的话去做就是!”宇文川远一拂广袖,“何人送来的礼物?”
泠弦恭声回应:“礼物是从沧州送来的!”
宇文川远神情一沉,双眉一挑,凌厉眸色乍现,望之让人生畏。
泠弦一个哆嗦,浑身一颤,不知何处触怒了皇帝。
乔津亭抚慰地握住了泠弦的小手,柔声说:“泠弦,礼物放下,你先去吧。”
看着泠弦默然退下,宇文川远有些焦躁地停下玉箸,举起酒杯,一人独酌,默默无语。
乔津亭好笑地看着宇文川远骤然黯淡的容色,直如一层阴霾遮住了深蓝清朗的天幕般,眼看骤雨将至。“你何必介怀?他仅仅是送了一份贺礼而已,值得你这样动肝火么?”
沧州送来的贺礼,除了英王宇文景微,尚有何人?
重重地将玉杯望御案上一放,醇酒四溢,宇文川远嗓音比深冬雨雪还冷:“这贺礼,他宇文景微理应送上朝廷,但至今不见贺表贺仪,违背礼数,理当重责;现在又将贺礼径直送来与你,这是何意?难道,他宇文景微还不死心?还在觊觎我的女人?”
乔津亭叹笑着摇头,不去看宇文川远冰山将倾的怒色,取过檀木紫盒,打开一看,一阵惊异。
檀木盒的内里是上好的红绸,红绸之上,静静地躺着一只玉笛。
玉笛!乔津亭一阵怅惘,笛声遏飞云,逍遥四海游的日子在今后的生涯中仅仅只能在梦魂中出现,景微,你又是何苦对往事念念不忘?
正想取出玉笛细观,宇文川远已抢先一步,他长手一探,玉笛已经在手,仔细一看,怒火更盛。“啪”的一声,将玉笛往御案上一拍,“他倒是好大手笔!”
乔津亭仔细一看,吃了一惊,这玉笛不是一般的玉石制成,而是用玉石中极其罕见的羊脂白玉雕就。玉笛通体温润坚密、莹透纯净、洁白无瑕,当真是绝世珍品,难怪宇文川远讥讽他宇文景微是“大手笔”,而玉体上尚有细小如蚁的篆书二字:“静好”!
“静好”!这是宇文景微对她的祝福么?
默默将玉笛收回檀木盒中,宇文景微,不惜违背体制,触怒宇文川远,可见对她归于宇文川远是多么的不甘心;而如今在她新婚之际送来贵重的贺礼,可见又是诚心期盼她能静好渡岁,安好无虞,这一番的心事纠缠,想必是翻江倒海,悲喜酸涩难言。与萧珉的淳厚诚挚决心放下对她的一腔痴念想比,景微,显然是任性纵情的。
细看乔津亭的脸色见她微微怅然,眸底略有悲戚之色,宇文川远顿感一股怒火直冲脑门,故意一挥广袖,扫落数只玉碟。
霎时,“叮当”之声不绝,霍然而来的脆响让在一旁侍候的宫人吓得直打哆嗦。
乔津亭不以为忤地淡然一笑,命宫人收好檀木盒,温言相劝,“你何必生气?”
“我……我当然生气,没有一个男人愿意看到别的男人对自己的妻子大献殷勤!”宇文川远别过了脸去,语气虽有所缓和,但脸色依然不悦,左侧的半边脸,背着光线,是淡淡的暗影一片。
乔津亭内心一惊,若是此番处置不当,勾起宇文川远对宇文景微的嫉恨,日后,他兄弟君臣二人之间难免又起波澜。
“你该知道,我对景微,纯粹是友朋之义,你莫多心!今后,我和他是叔嫂之情,你也莫疑虑,明白么?来日,你我以兄嫂的名义回礼一份,表明心境,可好?”乔津亭亲自为宇文川远斟了一杯酒,“来,我陪你喝一杯!”
宇文川远见乔津亭婉转规劝,心火消了大半,也知此事若是再纠缠下去,必定惹得乔津亭不满,还是暂且放下为好。
一连三日,宇文川远陪着乔津亭或是凭栏赏菊,诗酒唱和,或是月下对弈,邀月对饮,或是静默无语,执手相看,享尽新婚的甜蜜。
佳期总如梦,稍纵即逝,新婚的第四朝,宇文川远一早上朝而去,乔津亭也自起来,盛装打扮,接见内外命妇,司行皇后之责。
宫眷不多,但外命妇却是不少,在衣香鬓影中,或是雪清玉瘦,或是圆珠柔润,或是诚心赞誉,或是违心恭维,各色形态,不一而足;在觥筹交错中,一片歌舞升平,一团和气。
乔津亭特意细细打量一身新装、环佩生辉的萧琰,只见她一面的静约、矜持,时而向乔津亭举杯祝酒,时而与贵妇细语轻笑,丝毫不见失意落拓。内心赞叹,当真是身出名门,练就一身荣辱不惊的真本事,与前些日子的怨毒愤恨想比,有天壤之别。
在内侍一声“皇上驾临”的宣告声中,宇文川远一身朝服,威肃端严,阔步而来。
众人起身跪倒相迎,乔津亭仅是微微躬身,含笑注视着深眸在触及自己时眼神瞬间柔和的宇文川远,“皇上!”
宇文川远携着乔津亭的手,一起就座,环视命妇诚惶诚恐,沉声道:“各位夫人都去吧!”
命妇谢过帝后,恭谨低身俯首,鱼贯退出。
萧琰也自随众退出凤鸣殿外,谁知身后传来宇文川远熟稔却又陌生无比的嗓音,“萧贵妃留下。”
诧然回首,方才静水无波的面容在触及宇文川远与乔津亭紧紧相握的两只手时骤然变色,但很快的,将自怜、幽恨、怨毒尽数掩饰在妆容婉约之下,恭恭敬敬地朝帝后深施一礼,“皇上有何圣谕示下?”
乔津亭并没有忽略萧琰眸中的深怨浅怜,心有不忍,悄悄地将手从宇文川远的手心中抽出,谁知宇文川远却攥得更紧,内心暗暗一叹,宇文川远对她,当真是没有丝毫情谊么?
宇文川远面无表情,“自朕登基以来,辛苦贵妃打理内宫事务,如今皇后已立,六宫有主,从明日起,贵妃可以卸下重担,闲适度日了!”
交还六宫权柄,这是萧琰意料中事,此时话语从宇文川远口中冰冷泻出,如冰箭一只,深入五脏六腑,痛极寒极,无情如他,怎值得她些许的痴心眷恋?今后,她与他,怕是夫妻变成势不两立的仇敌!“是,皇上!”
乔津亭望着萧琰僵直的背影,转向宇文川远,眉头一皱。
抬手轻抚乔津亭的眉头,温柔地笑了起来,“累了么?这宫廷礼仪繁琐,也是烦人的,歇着去吧!”
“你对她,当真没有一分夫妻情分没有丝毫的愧疚么?何必决然如此?为了她的颜面,这六宫事务,给予她打理又有何妨?”
“你以为我该对她有情谊么?我该对她愧疚么?”宇文川远端起热茶,慢条斯理地递至唇边,一抹笑意横过清眸,“你若是认为我该对她有情谊,我也不妨对她多加怜惜,享受齐人之福,反正三宫六院是没有指望了。”
明眸有一瞬的黯淡,如薄云笼罩了如水桂华,乔津亭低了头,心头掠过丝丝的纷乱,一会,再抬头时已是阴霾化作了殿外的朗朗清阳,“哼,你敢?”
宇文川远见她下巴微翘,流露一丝平素难得一见的蛮横,不由得“哈哈”大笑,凑近妻子的耳际,细细低语,“我自然是不敢的,也不想,你放心!”
乔津亭乔脸骤红,身为女子,没有人愿意与她人分享自己的夫君,就算是她素来大度,也一样的不能,只是见萧琰已是春暮花残,情怀零落,内心不忍,“你应该知道,她对你,未尝不思慕,思慕而不可得,最断人肠。”
放下茶盏,宇文川远冷然一笑,“她萧琰对我,确是未尝没有男女的思慕之情,但是她萧琰,更多的是思慕尊崇、地位、财富,当初,将我和她紧紧系在一起的,不是情谊,而是利益,所以,乔,这情谊二字,不存在我和她之间,往日没有,今日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乔津亭叹息,宇文川远对她,可谓情深义重,但对于萧琰,却未免薄情,但这又怎能怪得了他?情之一字,原是不能勉强了半分!她乔津亭比之萧琰,幸运了何止百倍?“那,你就让她打理后宫事务,至少,这点颜面你可以给她,也让她有所寄托。”
宇文川远摇摇头,握住乔津亭的手,“乔,无须事事为他人着想,萧家对你对我,何曾心慈手软?如今风雨逼近,你我都手软不得。收回后宫治理权,仅是削弱萧家的第一步,你须知,后宫也是战场,不见硝烟的战场,你要尽快地清除后宫中萧家的势力,明白么?”
愣愣地望着宇文川远,乔津亭有些泄气,“这听着比我行医救人可难多了!”这后宫事务,千头万绪的,她纵然聪慧无比,但也不知该如何下手啊。
安抚着拍拍乔津亭的手,“你放心,我自会帮你,首先,你可先替换宫中重要职务的人选,防止萧家对后宫事务的染指;继而清点后宫财物,断绝宫中财富外流。”
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就是这个道理么?这天下,原本就是宇文家的天下,不管是何人,都不能存了图谋皇权的野心!萧家更是不能!
望着宇文川远眸中暗影,第一次,乔津亭第一次意识到作为妻子的职责就是为她的丈夫建筑一个安稳的家;作为皇后的职责就是治理好后宫。只要后院不起火,他自然可以心无旁骛地治理朝政,让大魏朝的百姓安居乐业,还世间一个海晏河清。
“你放心,我会尽心尽力,做一个让你放心的妻子,做一个尽心尽职的皇后!与你,风雨同舟!”实际上,从他踏进流云山庄的那一刻开始,她就已经通他共进退,同命运!
心头似有花开千朵,芳香四溢,笑容如秋日般暖热,宇文川远牵着乔津亭的手,慢慢走下了御座,走向暖阳深处。同样是四角高墙,但年来苦乐,有人共享,有人分忧,这,已经是人生最大的欣慰。
接下来的日子,乔津亭忙着整治后宫,竟然没有片刻的安闲,好在经过一些日子的努力,成效彰显,也不枉费了一番心血。
朝堂之上,宇文川远着意选拔能吏,分割萧家的权力,进程居然颇为顺畅。萧家,竟然没有意料之中的顽抗。这不能不让人猜疑。
转眼,秋光老尽,暮云掩了残阳,寒冬已然来临。
这些日子,乔津亭出乎意料的贪恋香浓凤枕,热暖香衾。送走一早上朝的宇文川远,她竟然慵懒无比,还倒回床榻之上,沉沉睡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绿芷兴冲冲地像一阵风,卷入寝殿之中,“少主,少主,下了一场大雪,快起来看看!”
一番叫嚷将乔津亭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掀开浅红香绸帐幔,见绿芷明眸如水,层波荡漾着喜色,“真的么?”怪不得天寒如斯,原来是天降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瑞雪。
绿芷兴冲冲地赶忙为乔津亭着装,“快,少主,看看去,好大地一场雪!”言语似娇莺,声声动人,感染着一身酣懒的乔津亭。
不一会,白蘋泠弦等人也来了,一霎时,娇红嫩绿,莺声燕语,好不热闹。
梳洗完毕,顾不得用早膳,乔津亭与流云六艳齐涌向御苑,。
好一片银装素裹的白雪世界!只见飘雪暗穿庭户,匀飞细舞,如素色天花撒播,往日的衰树残枝,变成了瑶琳琼枝。
众女嬉笑无忌,掷飞一个个雪团如球,相互追逐着一条条窈窕如袅云的倩影。
清澈的笑声在御苑响起,声声清脆,飞过厚重地宫墙,直插云霄。
乔津亭一时兴起,命侍女取过宝剑,一时间,剑光划开漠漠天幕,耀亮沉沉冬色。
雪地上,乔津亭一袭金丝缕描鸾凤玄色斗篷旋舞,露出内里绛色衣裙,闪亮了人眼。
六艳停下追逐地步伐,凝神细看乔津亭剑削飞雪,倏而往来,翻飞如轻燕。看到精彩处,轰然叫好。
突然,一阵反胃,一股酸流上涌,胸口窒闷无比,乔津亭缓下了剑势,柳眉轻蹙。
白蘋心细,发现乔津亭春山微蹙,疑虑不定,上前取过乔津亭手中的宝剑,一手搭上少主的脉搏。
不一会,白蘋喜上眉梢,“少主……”
乔津亭玉肌丹染,低声相询,“是不是……”
白蘋重重点头,“恭喜少主!”
真的是孩子!一个她和宇文川远的孩子!怪不得这些日子嗜睡、恶心,原来,在不知不觉中,一个孩子已然来临!若然宇文川远得知,该是何等地欢喜!
泠弦一声轻呼,“皇上来了!”
不远处,宇文川远大步流星,正朝乔津亭而来。
携了乔津亭的手,细看她丰肌玉骨,斗篷内纤腰玉削,袅柳应妒,偏又眉宇间一段飘逸英爽之气,浑不是人间闺阁模样,倒恍是当年流云初见之谪仙!这就是他的妻,他的皇后!
在宇文川远炽烈眸光的倾注下,乔津亭眼波流转,偏又羞意流溢。
“天冷,回去吧!”两只大手紧握着两只纤细的手,搓了几搓,觉得有了热暖,才停了下来。
“今日,朝中可有事?”乔津亭见宇文川远眉宇间隐隐有忧戚之色,轻轻问了一句。
听得细细一声叹息,乔津亭顿感握着她的大手一紧,果然!是萧家发难了么?
“边境来报,大凉国国君因病薨逝,穆尔蓝沁即位为国君,但不知为何,我竟似听见了战马嘶鸣,金戈声响!”宇文川远望着漠漠天际,层云低矮,心事重重。
乔津亭一愣,一时间,竟不知道是不是该将怀孕的事告知于宇文川远。
“沁芳殿”,沉香袅袅,扰乱芳心如乱絮。
萧琰倚着半开的窗台,看大雪如浮玉飞琼,一片白茫茫,冷沁人心。
慢慢地,让宫人紧闭了绮窗,这等凄冷,非是她这等多年独守空闺的人所能承受。
“贵妃娘娘!”一声轻唤将萧琰的思绪从纷乱渺茫中拉扯了回来,懒懒的,恹恹无神,“什么事?”
贴身侍女翠袖贴近萧琰的耳际,轻语数声。
萧琰脸色乍变,身子不由自主地抖动了起来,双目一闭,定了定神,颤声说:“你确定不会有错?”
“娘娘,多半不会有错的,这些日子,皇后娘娘时常无端作呕,”翠袖一面的笃定,“皇后娘娘擅宠专房……”
一罢手,截断翠袖刺痛人心的话语,跌坐在锦榻之上,唇色比之殿外纯白世界恐怕逊色不了多少。
幽深丽眸定定的,紧盯住升腾的炉火,只觉心痛似火烤炙,许久,问翠袖,“太子何在?”
翠袖未及答话,厚实的锦帘外传来宇文思耿的声音,“母亲,儿臣来了!”
侍女恭谨地打起绣着芙蓉的深蓝锦帘,宇文思耿大步跨进。
萧琰凝视日渐年长的宇文思耿,内心一阵酸涩。自她被册封为贵妃以来,宇文思耿坚持称呼她为“母亲”而非“母妃”,这孩子,是在为自己的母亲不平么?
“母亲,为何你脸色如此苍白?”宇文思耿浓眉一皱,阴郁自眸底倾泻而出,“翠袖,传太医!”
“不必了,思耿,眼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和你说说,你到母亲这来!”萧琰招了招手,让宇文思耿在自己的身旁坐下。
抚着宇文思耿的浓眉,这孩子,样貌倒是与自己一般的清秀,但这一双的浓眉,与他寡恩薄义的父皇是一般的模样。
雪地茫茫,宇文川远与乔津亭携手同行,一黑一黄的斗篷异常的耀眼。
“天气越发的冷了,今后少出来走动,免得受了风寒!”宇文川远不厌其烦,殷殷叮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