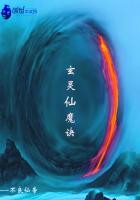次日清晨,天刚鱼肚白,料峭寒意还未褪去,枝头草尖尚挂着霜露。
陆梨一夜未眠,先是绣锦囊绣到半夜,好不容易躺在床上,后半夜不知怎的心神不宁的,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她揉着疲倦的眼眶,打算去院里透透气,却在踏出房门的一刻愣住了。
叶琛穿戴整齐、手中握着那柄长剑正朝林中走去,长长的乌发似墨一般飘在身后,白衣翩然,背影笔直。
陆梨猛然意识到什么,他要离开,一言不发地离开!
她忽地提起裙摆朝他即将消失的背影奔去,手里还握着熬夜绣出的锦囊。寒风之中,她顾不得被风吹乱的发丝和打在脸上的雾气,只是飞快地奔跑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追上他,不能让他就这么离开!
叶琛悄无声息地走在林间,心思缜密地回忆着来时的路,却在听到身后乱了节奏的喘息和密集的步伐声时错愕地转过身来。
他看见陆梨一脸慌张地朝他跑来,提着裙摆,发梢飞扬,额头细密的汗珠像是清晨梨树枝头闪着微光的露水。
身影像被定住了一般,立在原地,动弹不得。
“为、为什么……”陆梨终于停在了他面前,抚着心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好半天都没找到呼吸的节奏。
为什么不告而别?
为什么走得这么干脆?
她像是质问一般固执地盯着他,眼眸里有灼灼的光辉呼之欲出。
为什么?
叶琛神色复杂地看着她,连自己也说不出这是怎样一种冲动。无眠一夜,思绪纷飞,最终在天未亮时忽然决定悄无声息地离去。
他幻想了无数次告别的场景,却一次又一次在想到她会交给自己平安锦囊时断了画面。她会说什么呢?他不敢想象,甚至在抗拒这种念想。
他的日子已经很难熬了,知夏昏迷不醒,见风阁危在旦夕,昔日的亲信不知今日是否叛变,最信任最亲密的师弟要致他于死地……他已经没有办法承受更多的变故了,也不想再去理清心里那个缠成一团的龌龊念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安心解决好现下的一切困难。
就让那些古怪的心跳就此沉寂下去,火苗初现,他便浇熄。
此时陆梨无比清晰地直视着他,眼里的坦然令他无处遁形。他沉默半天,也只是垂眸不语。
清晨的风吹在面上,她此时才发觉冷。梨花一夜风雨,将开未开,脚下的泥土夹杂着腐败又悠远的气息,萦绕鼻端久久不散。
她就这样固执地看他半晌,才缓缓伸出手,摊开掌心。那里摆着一个小小的锦囊,青底白花,用细线一点一点勾勒出的轮廓,然后分成数股填色,可见制作的人多么用心。那花朵精致小巧,竟和枝头的梨花相差无几,只是这样看着,都有种花香扑鼻的感觉。
他的目光停留在锦囊右边的小字上,突然间失去了焦距。
梨花一枝望君归,
她望着他,一字一句地轻道:“这是……这是风姑姑送给我的,说是可以保平安,你带着它上路,万事小心。”
风诺送的?
他轻易识破了她的谎言,本可以说出来又或者轻笑一番的,可是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的眼睛还红红的,显是熬了夜;她的发丝凌乱湿润,贴在面颊上被汗染湿;她的裙摆沾了泥土,失去了素来的整洁;她的眼神固执坚定,像是枝头初绽的素净梨花。
他的手指动了动,久久才接过那个锦囊,“……多谢。”
她安心一笑,“一路平安。”
叶琛走后,陆梨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每日清晨监督婢女们熬药给知夏沐云,下午采药,夜晚翻医术,每隔三日施针一次。只是到后来针法的效果越来越差,逐渐变成两天一次,幸好沐浴这法子很管用,知夏的心跳竟然比先前多了几分活力,连呼吸都不那么微弱了。
她再一次察觉到知夏有力的心跳时,忽生一个念头——也许,也许她可以醒来的!
她兴冲冲地跑去找风诺,推门便问:“风姑姑,百叶草加墓头回若是用来使人清醒,你说知夏是不是可以暂时恢复神智?”
风诺先是一愣,而后脸色沉重起来。
“阿梨,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弃?”
她没料到风诺一开口就是这种话,先前的热情也被浇熄,恢复了素来清冷从容的声音,“姑姑为何一再要我放弃?医者父母心,这是姑姑教我的,如今我按照姑姑教我的来做,姑姑却责备我,恕阿梨难以从命。”
风诺微怒,拂袖重重拍在桌上,“我也是为了你好!阿梨,你太让我失望了!”
她倔强地看着风诺,低低地说:“姑姑,阿梨也对你很失望。”
她一步一步走出房间,留下风诺面色苍白地跌在床上。
师兄,你要我如何收拾这个摊子?
我怎么能……怎么能看着阿梨在救与不救的选择里受尽折磨呢?
不是她心狠,也不是她不愿帮陆梨,她是不能帮,不能说!她不能看着陆梨一辈子活在愧疚中,说她自私也好,狠毒也好,那姑娘若是就这么死了,她不过是一时难过,若是叫她知道了救治方法却眼睁睁地看着那姑娘死去,这才是一生的愧疚。
见风阁在江南,而叶琛此时就在江南的沉沉夜色里飞快地行走着,身披蓑衣,头戴草帽。微凉的雨丝拂在面上,他恍若未觉,只是悄无声息地沿着曲折小巷赶着路,最后停在了一家木门微开的人家前。
他犹豫了片刻,从蓑衣下伸手敲门,得到屋内人的回应后低低地说了声:“我是叶琛。”
“吱——”木门缓缓打开,一个乌衣老者飞快迎了出来,眸里闪着精光,太阳穴鼓鼓的,显是练功已久,内力深厚。他深深一揖,恭恭敬敬地说:“不知少主深夜来此,有失远迎,向东实在惶恐至极。”
叶琛伸手托起他,低声说:“向前辈不必多礼,非常时期,这些礼节可以略去。”
叫向东的老者这才直起身来,“少主,进屋谈。”
屋内摆设简朴,毫无格调可言,看得出向东生活朴素,未曾购置一砖一瓦的装饰物。
叶琛坐在木桌前的木椅上,神色凝重地听他讲着见风阁的现状,眉头皱了又皱。
郁晴风一向得人欢心,自小和同龄弟子打成一片,在见风阁资历最深的木溪师伯那里又最受宠爱。现下阁内无人主事,木溪就理所当然把一切交给他来打理,众人也并无异议。只是郁晴风一管事,就开始以笑面虎之姿调动阁内的人,表面上说是整顿门风,清理那些在其位不谋其职的尸位素餐之人,暗地里却将叶琛最死忠的心腹一一调离岗位,向东就是其中之一。
向东自少年起就跟随叶琛的父亲,可谓是他最坚实的后盾,本来在见风阁担任处理对外纷争的职责,而今却被派到这个小镇来说是暗查江湖上是否有对见风阁有异心的苗头。
真是可笑,这个借口也亏郁晴风那厮想得出来!见风阁的暗卫那么多,眼线遍布大江南北,如今却要他这个糟老头子跑来做什么暗访,这难道不是最明显的排挤叶琛的行为么?
除他以外,另外几个心腹也被各自调离岗位,和他差不多下场。看得出,郁晴风以知夏为挡箭牌,知道叶琛不会丢下她不管,因此有恃无恐地挑明了宣战旗号。可笑的是见风阁里的那群人还成日听着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无才无能,要等师兄回来主持大事,并且对此深信不疑,更认定他是个谦虚有才的领袖,真是荒谬!
叶琛听他说了这些,沉思许久,最终点点头,在他耳边低语半晌,然后告别离去。
“少主,更深露重,风雨交加,还是歇一宿再走吧!”向东焦急地挽留他。
他淡淡一笑,拿起蓑衣重新穿上,“来不及了。”
看他孤绝料峭的背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向东忍不住叹口气,现状堪忧,现状堪忧啊!
接下来几日,他又分别拜访了几位父亲昔日的旧属,向他们一一说明现在的情况,请求他们帮助,忙完这一切后,江南连绵春雨已有了消停的迹象。
他疲倦地走进临时租住的小院里,脱下草帽蓑衣,在接满雨水的盆子里掬水洗了把脸,然后躺在阴冷潮湿的木床上发呆。
屋顶有漏水的痕迹,水滴顺着瓦片从墙角吧嗒吧嗒落下来。窗纸破了不止一处,寒风从破的洞里刮进来,吹在面上犹如刀割。他很无奈,不是三月了吗?为何江南的初春这样冷?
脑子里突然浮现出神医谷的春天,春意融融,日光微醺,枝头的梨花都比这里开得早。那里有满山的药草,满谷的梨花,还有放纸鸢的欢笑,以及……那个如梨花般素净洁白的黛衣女子。
若是他也出生在那种地方,远离江湖纷争,没有勾心斗角,又会是怎样一番场景呢?有人关心,有人爱护,即便父母不在身边,也还有一个如父如母的风诺,和一个如亲姐妹般的宁欢。
其实,他是羡慕陆梨的。同是无父无母之人,她拥有的,比他多到哪里去了……
他就这样躺在床上闭眼沉思,好半天才睡过去。迷迷糊糊间好像看见了知夏的身影,她微笑着坐在他身旁,巧笑倩兮地说着:“叶琛你闭眼,我送你个东西。”
他顺从地闭眼,然后她将一个海螺凑到他耳边,“你听,大海的声音!”
他凝神一听,却没有听到什么大海的声音,反而……反而听到了陆梨的声音!
“合欢花,款冬,防己,地肤子……”
他听见陆梨用温婉沉静的声音念着一连串草药的名字,朦胧中想着这一定是幻觉,却在下一刻忽地惊醒过来,不对!他从未听过这些草药的名字!
他本就睡得极浅,这下更是清醒过来,疾步走到檐下,发现雨已经停了。然后就听见隔壁小院里真真切切传来他梦里听见的那个声音,那声音还在继续念着诸多陌生的草药名。
“忍冬,蒺藜,石龙刍……石龙刍不够啊,这可如何是好?”
他如遭雷击般怔在原地,回过神来之后迅速走到篱笆边,只见隔壁院里有两个少女围着一大簸箕草药,赫赫然是陆梨主仆!
他就这样惊异地看着她们,石化一般。
她们……怎会到此处来?
陆梨背对他,宁欢一偏头,就越过陆梨的身影看到了立在篱笆边只露出个脑袋的叶琛,也是一愣。
“小……小姐……”她磕磕巴巴地指了指陆梨身后。
陆梨立刻回过头去,然后也愣在了原地,眼里满是不可置信的光芒,“叶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