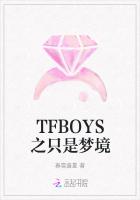一下雪我就想回家,回到寨子里去。如果是在寨子里,阿良阿生他们就会来找我去滑雪,我们还会去捉鸟、打兔子。可是在茶叶厂,我只能无聊地看着窗外的雪无聊地飘着。好几次我都跟妈妈说我们回家吧,妈妈总说雪太大不好走。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我还在上学。大雪里走路没什么危险,这儿是高山上,不会有深谷也不会有悬崖,都是浅浅的丘陵,再大的雪只不过是把小山谷填平而已。那样的话,我们就是真正的高原了,一望无际,像画片里的青藏高原一样。
我还没放假,我不能回到寨子里去。
我在教室里给大家讲我的班马,我的滑雪故事,我还说我是寨子里滑雪最好的。当然,他们都不信。我就说,不信?那咱们比比?但是我的同学们都没有班马,他们也不懂怎么做一个班马。即使我说得再好,把滑雪形容得再美好,他们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让我从某方面觉得自己和他们有很大的代沟。我的同学很多都是外地的,或者是城里的,只是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来到这儿。而我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在茶叶厂里,像我一样的人不多。或者,那些像我一样的,在茶叶厂停工后就随着父母走了。
这让我有点孤独。
学校的院子里积了一层雪,雪被风一吹就冻成了很硬的一片,走在上面不小心就会摔一跤。传达室的老爷爷用铁铲在院子里铲出了一条路,我们上学放学就只能走那条路了。雪让院子里安静了很多,没人愿意顶着风雪到院子里摔跤玩。很多时候我就托着下巴看着这逐渐白茫茫的世界,心里也很空很空。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收拾书包的时候马子洋跑来说,等下我们滑雪去吧?我就有点奇怪,问他,滑雪?滑什么雪?马子洋比划着说,就是你说的,拿着什么班马去滑啊。我就说,班马很不好弄的,我们拿什么滑嘛。马子洋笑着说,我想了一节课,想出了一个很好办法,我们可以拿凳子滑,你想啊,凳子也是很光滑的,我觉得它就跟班马一个样儿。这个马子洋,亏他想得出来,那我们就试试吧。我就说,那行啊,你找几个人,我去找场地,咱们试试?
看到马子洋的班马的时候我差点就笑倒在地上。他拿了一根板凳,把板凳的四个脚给去掉了,只留下一块板子,然后在板子上绑了一块沙发坐垫。他很骄傲地举给我看,高兴地说,怎么样?这个还行吧?我只好说,还行还行。我只是纳闷,等下坐在上面滑雪的时候他会不会掉下来?真正的班马可不只是弄一个坐垫那么简单。马子洋就怂恿我也去弄一个,最后我只好也照着他这个班马的样子弄了一个,最后,我们几乎所有男生都有了一个绑着坐垫的小板凳。
我找到了一个山谷当我们的滑雪场。滑雪的场地选择也是很重要的,最好的场地是狭长的倾斜的山谷,要先把班马拖到山谷的最上面,然后再从上面滑下来,最好是山谷前面还有一块平地起缓冲作用。以前在寨子里的时候我们有时会找没有缓冲平地的山谷,山谷前面就是结冰的水稻田,如果刹车不好就会冲到田里去。这当然也是很刺激的,所以滑雪不只是班马好速度快的问题,还要学会掌控速度和方向。我觉得马子洋他们都不会滑,所以就选了一个并不陡的山谷,前面也没有水稻田或者什么挑战性的东西。
我们吭哧吭哧地抱着凳子爬到了山谷的深处。马子洋问我,现在可以滑下去了吗?我说,不可以,要先找到路。所以找到路就是要先清理一条滑雪道出来,不然雪积得太厚了,很可能连人和班马都陷进雪里,站都站不起来。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找路,这个活儿只能是我来做。我就小心翼翼地坐着自己的班马慢慢往下滑,两条腿伸直,控制好速度,为后面的人开一条路出来。
开路的活儿很累的。别看雪看上去软绵绵的,但是被风一吹就变得很硬,我滑得很艰难,才滑一半就累得气喘吁吁,比刚才拖着板凳上山谷更累。上面有人在喊,晶晶你到哪儿了?我回过头去,却什么也没看见,这个山谷是一个弯的山谷,上面的人看不见下面的人。我就使劲喊,快好了!上面没回音了,我就继续往前滑。
山谷里的风很大,呼呼地吹着。我穿着皮帽子和厚棉衣,皮靴子,还戴着毛线手套,可还是被吹得满脸通红,鼻子像掉了一样,完全没知觉了。这个山谷似乎变得很长,我滑了半天还没到底,风越来越大,然后又开始飘雪了。我回头朝起点看去,只有白茫茫的一片,山顶的大雾笼罩下来,树上的冰凌倒挂着在风里摇摆。我就大喊,你们下来了没有?远处传来遥远的回答,我们下来啦!我们的回声在山谷里跟着风雪一起回荡,然后我就看到一群人坐在板凳上滑了下来。
他们滑得跌跌撞撞的,远没有我们在寨子里滑雪时候的样子好看。有几个人甚至翻到了雪窝里,爬起来的时候一头一身的雪,像个雪人。我就说,不是这样滑的!我滑给你们看!我就拖着自己的板凳,在雪地里艰难跋涉到山谷上的起点,顺手从旁边的树叶上扯了一块冰在嘴里嚼着,大喊一声“我来了”就沿着自己开的雪道滑了下去。
不得不说,板凳远远没有班马滑得顺畅。首先坐在上面就不舒服,而且速度很慢。习惯了滑雪时候飞一般的感觉,面对这个情景我有几分沮丧。这哪儿是滑雪,简直就是蹭下去的,遇到稍微高一点的地势还要用脚在地上蹭。但是马子洋他们还在周围叫好。我就想,那是你们没见过真正的滑雪,要是见到了你们还不得吓死?我们都是骑在马上的风雪战士,在雪地里飞奔的。而现在,顶多就是骑了一头老牛。
我们玩得不亦乐乎,天空里的雪也越飘越密。风有点大了,卷起地上的雪,混合中空中的雪花,天地一片翻腾。我们嘴里呼着热气,眉毛都结了一层霜,每个人的脸都是红扑扑的。天空越来越暗,不知道是雪变大了还是天快黑了。当我们都觉得应该走了的时候,突然发现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天空暗得如同已经降临的夜幕,我们惊恐地发现,暴风雪要来了。
马子洋喊着,我们快点回家吧!要下大雪了!大家都说,快点走吧。当中有人已经有哭腔了。我想起了什么,赶紧说,点一下名!看人都到齐了没有!马子洋说,对!点名!我喊谁的名字谁就答到,跟在学校里一样!大家就说好。马子洋一个一个点了起来,但是喊到小赖子的时候却没人应声,喊了几次都没应。我心想,完了,我们把小赖子弄丢了。
我们只好朝山谷里走去,去找小赖子,边走边喊他的名字。风雪越来越大,我感觉我们的喊声都被风雪给吞没了。明明喊出了口的声音,却又被风给吹了回来。风雪混杂着我们的喊声在山谷里回荡,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在积雪里艰难走着。马子洋本来就很胖,再加上穿了一身的厚棉衣,远远看过去就跟一个球在雪地里滚动一样。走了一会儿,这个球一样的马子洋喘着粗气说,行了,我们看来是找不着了,回去叫大人来吧,天都快黑了。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确实已经变得跟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当然,我没看清天空是怎么样的,因为雪花越飘越大,抬头只看到一片密密麻麻的雪花在眼前飞舞。
山谷里的风呼呼响着,我们一群小孩站在没过小腿的雪里喊小赖子的名字。我反对马子洋的意见,我认为我们一走,小赖子说不定就会被冻死了。在我的坚持下,大家只好在山谷里大声喊着小赖子。其实我真正的理由是,小赖子只可能在这个山谷里,他不可能跑到其它地方去的,除非他是会爬山的猴子。
可是等我们到了山谷顶上却什么也没看到,连个人影都没有。这下我们是真泄气了。
风雪呼啸着在山谷里翻滚,我们沮丧地一个拉着一个在山谷里顶着风雪慢慢往下走。远远看过去,我们肯定很像一群在喜马拉雅山探险的人。我记得看过一本漫画书,《丁丁历险记》,里面就有很多人外国人在雪山里手拉着手一起走。其实在雪地里手拉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防止被风吹散。我们已经少了一个人,再把其他人弄丢就说不过去了。
等我们走到山谷入口的时候,远远地就望见一个瘦小的身影靠在一棵树下瑟瑟发抖。有人就喊,是小赖子吗?那个身影用带着哭腔的颤抖声音回答我们,你们到哪里去了……我都找不着你们……原来真的是小赖子,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我就跑过去一拳打在他身上,说,你跑哪儿去了?我们找了半天喊了半天你怎么跟个木头一样啊?小赖子就哭着说,刚才我是最后滑下来的,到了下面一看,你们都上去了,我就在这儿等你们,谁知道雪下大了,我就找不到你们了。
马子洋说,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回家吧,等下真的大家都回不去了。
我说,赶紧走吧,雪越来越大了。
山谷里的风就在我们身后呼啸,我裹紧身上的棉衣,把那个滑雪的板凳扔在雪地里,猫着腰像个老头一样迎着风雪朝山谷外走去。我的身后跟着我们的滑雪大军,每个人都猫着腰,低着头,在雪地里摸索着。我们都在想,赶紧回家,赶紧回家,不然就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