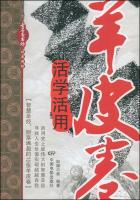“娘,娘,你不要死,孩儿不要你死!”
冯负双手用力地捂着遗飘飘不停往外冒血的伤口,看着她属影黯淡,若隐若现,胎印也接近透明,泪如雨下,大声喊叫着。
遗飘飘望着冯负稚嫩的小脸,勉强笑道:“负……负儿,你……别哭……”看向结束战斗走过来的苏酥,眼神里满是恳求,虚弱地道:“校……校……,求……求你……”
苏酥握住她手,重重点头道:“易浮,你放心,一日为师,终身为母,我会替你照顾好他。”
遗飘飘轻微地点头,露出一抹微笑,艰难地抬起手,向冯负摆了摆,道:“你……你……走……”
冯负哭道:“娘,我不走,孩儿要陪您一辈子!”
苏酥明白了遗飘飘的意思,出言道:“冯负,你先退开些,你娘有话要和我单独说。”
冯负看了眼母亲,遗飘飘微微眨动眼睛,表示苏酥说的没错。冯负不敢忤逆,只好往后退了几步。
这时遗飘飘嘴里呕出大量血水,已经不能开口说话,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嘴唇嗡动,苏酥忙附耳上去。
听到她说的话,苏酥眼眸狠狠闪烁了几下,不自觉握紧了遗飘飘的手。
不远处的冯负看到母亲属影消散,抬起的手无力地落下,呆滞地跪倒在地,一步步爬向母亲的遗体,抱起她的头,将自己的脸紧紧贴在她冰冷的额头。
黄昏悄然而至,夜幕即将降临。
雪花不解人间离恨,仍漫天地下着。
银装素裹的白河村,一处小院里,所有的狼藉早被大雪所掩埋,滚烫的血水,不知何时化作了寒冰,将一对母子紧紧地冻结在一起。
他们身旁,静静地矗立着一个女人,为两人撑着一把油纸伞,而自己的发上身上,雪花堆积,光滑的脸蛋,冻得通红。
时光静止般,三人就这样一动不动,像一幅凄美的画卷。
良久,女人轻叹了口气,拍了拍男孩的肩膀,轻声道:“跪一天了,让你娘入土为安吧!”
男孩像只受惊的鸟儿,丢了魂般恐慌地四处望望,喃喃道:“娘,您不要负儿了吗?”哽咽沙哑的声音之后,没得到任何回响,想到母亲就这样永远地离自己而去,泪水“扑簌扑簌”地往下滚落。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您,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呀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流浪的人……”
冯负一边哭一边哼唱起地球上的伤情歌曲,苏酥听了,鼻子一酸,禁不住也淌下眼泪。
不知过了多久,冯负道:“苏酥老师,请您搭把手。”
他在雪地里跪了一整天,膝盖早已麻木,变得毫无知觉。
苏酥伸出玉手,冯负抓住,此刻他的心里再产生不出任何其他的异念,苏酥微微用力,冯负抱着遗飘飘站起,。
苏酥伸手欲接过遗飘飘的尸体,冯负坚定地道:“我可以的。”
苏酥看着他突如其来的平静,不知怎么,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男孩不仅仅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
试着踏出一步,“腾”,再度跪倒。
苏酥正待要扶,冯负沉喝一声,硬生生地竟强撑着站了起来,他紧咬牙关,随即又踏出一步,就这样一步步走到一里外的小山丘,用手刨了个大坑,将遗飘飘的尸体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在母亲额头上轻吻了一下,用土掩盖好。
做完这一切,天已大亮,冯负用木板刻了块碑:“慈母遗飘飘之墓”,竖放在母亲坟头,认真地磕了十几个响头。
魂不守舍地回到家,胡乱收拾过东西,放了把火。
这个住了十二年的家,没有遗飘飘在,他再也不想回来。
苏酥不知该如何劝慰,一直静静地跟在冯负的身后,看他走在前面,纷扬大雪里,行尸走肉般,孤单寂寥的削瘦身形,心里十分难受。
一直走回属校,其时已是正午,学生们下了课,陆陆续续地往食堂而去,看到满身血泪的冯负,目露惊异,又看到不远处的苏酥,有的装作没看见远远躲开,有的则连忙走上前去问好,待他俩走过,立刻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苏酥跟着冯负走到宿舍楼下,冯负转过头,微笑道:“多谢老师,我回去睡觉了。”
苏酥看着眼前刚刚失去母亲的孩子,小脸憔悴苍白,仿佛老了许多岁般,一阵心疼,蹲下身抓着他的肩膀道:“节哀顺变,你还有老师……”
冯负重重点了点头,转身回了宿舍,苏酥叹了口气,自去办公室处理两天来积压的公务。
冯负躺在床上,眼前浮现十二年来遗飘飘对他的宠爱与关怀,早已干涩的双眼,又不自禁地滚下热泪,良久,紧紧抓着床单,牙缝间挤出两个字:“朱弼!”
傍晚时分,一名室友推开了门,道:“冯负,刚刚有个人让我把这张卡片给你!”
冯负接过一看,上面写着“有种的,一个人来小树林!”字体遒劲,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冷冷地道:“老子正要找你呢!”攥紧了拳头,嗤嗤声响,卡片先是褶皱起来,随即在水力的浸润下,变软,最后化作一缕轻烟。
冯负只身到了树林,果然朱弼在里面,这次他并没有大张旗鼓,只带了四五个人压场助威,这几个人,人人手腕处都有八只莹然的水镯,显然都是踏入了泉境的。
“我弟弟的事,咱今儿就好好地清算清算!”
朱弼冷冷地看着冯负,却发现他同样目光冰冷地注视着自己,眼神透着噬人的凶光,仿佛死弟弟的人不是他朱粥,而是冯负。
黄鼬属影现出,水镯光芒盛放,朱弼大喝一声:“碎骨破风锤!”蹂身而上,整个身体带着破风的呼啸向冯负撞去。
冯负血瞳黑翼蝉的属影在背后悄然闪烁,两目变得通红,待朱弼的肘风袭到,心里低喝:“动!”
想象中肋骨碎裂的声音没有听到,朱弼仿若击在了棉花上,径直从冯负的身体穿了过去,跌在地上,滚出老远,惊诧地望过去,只见冯负两尺外的身边,又出现了一个冯负,瞳孔微缩,暗道:“这……是什么?分身术吗?”
冯负不理会他,从袖里拔出匕首,扑将上去,朱弼又是一肘扫出,冯负不避不挡,将匕首直直插向朱弼的胸口,朱弼大惊,忙一个侧滑,最终冯负背上生挨了一肘,吐了口血,而匕首,则深深地插在朱弼的左肩。
朱弼一声惨叫,冯负没有任何的停顿,立刻拔出匕首,再次往他胸口攮去。
朱弼有些慌了,他没想到不过十二岁的冯负下手竟是如此之狠,看样子,是非要自己的命不可,叫了声:“上啊!”使出本命属技-穿山丛,箭一般往外逃窜。
那几个人从愣神里醒过来,忙施展出自己的属技,几道水力匹练劈在冯负的身上,冯负登时摔出十几米远,撞折一株刚植不久的小树。
那几个少年连忙奔上,抓住冯负的胳膊,匕首扔脱,将他摁在地上。朱弼看了眼肩头的伤口,狞笑一声,既然都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那什么天阶生的,也不用顾忌了。
眼中杀意暴涌,狠狠一脚往冯负的头颅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