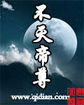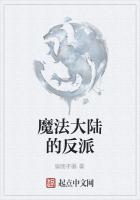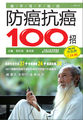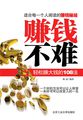丁邦彦,魏国清河郡人。公元988年,丁邦彦参加立天府乡试,顺利中得举人,排第十九名。但此后10年,丁邦彦三次会试失败,在失败之后更是在人世间饱尝冷暖。公元998年也就是两年前,时年三十九岁的丁邦彦再次参加会试科考,并取得了殿试资格。
时任北魏皇帝吴阖也准备移居西苑后一心修玄,以求长生,朝内大小事务交于太子吴越处理,公元998年吴越继位,太上皇吴阖虽然不问朝政,但对于当时魏国的治军、吏治、臣子、隐患、国库、民意仍然还是非常在意的,他不想自己积累的些许国资在魏王吴越成长所需要的经历的必然错误中损耗过大。所以,他要为吴越选择一位能够经世致用的人才,吴阖出人意料地告诉魏王在殿试时必须要问这个问题:“若欲闻人得用,财日理,以至治美刑平,华尊夷遁,久安之计,何道可臻?”魏王孝顺又自知较他的父王经验缺乏,这样的要求吴越应声答应了,而这个策问几乎囊括了内外政务,直指吏治关键,这道题目对那些注重文辞、没有政治经验考生来说着实是一件难题,他不是高谈阔论的讲演而是针砭时弊列举治国之策。
殿试结束之后,考官们经过商议,拟定出了第一名,吴越拿到名单之后并请吴阖过目。吴阖看过后,连连摇头,表示不满意并询问吴越:“我儿,你以为这数篇殿试文章谁是第一的最佳人选?”
吴越记得丁邦彦的《策论》,他当时看到后便眼前一亮,于是说道:“丁邦彦有一篇策论儿臣以为可以为第一名。”吴阖看看自己的儿子说道:“何以为然?”
“首先其的优美的字体字字楷正,足说明此人是细致之人,其次其起笔之言便为“帝王之致治,是必君臣交儆,而后可以底德业之成;必人臣自靖,而后可以尽代理之责”不同于其他的殿试文章,此为立意高远。最后在这篇作文中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去三浮,汰三盈,审三计”的具体措施,“三浮”是指官浮于冗员,禄浮于冗食,用浮于冗费;“三盈”是指赏盈于太滥,俗盈于太侈,利盈于太趋。“三计”是指有不终岁之计,下也;有数岁之计,中也;有万世之计,上也。所以说,丁邦彦在《策论》中对澄清吏治、改革弊端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有条理的分析论证,切中了时下的一些弊端,故儿臣认为能为第一。
“好,吾儿当有治国之眼能能自辨好坏,但为父要告诉你光有分辨是远远不够的,拥有力排众议的勇气和聪慧的君王之心尤为重要,为父相信你”吴阖说完便朝着自己西苑去研究养生去了。
近两年吴越对丁邦彦的在旧族和军功上的改革建议采用并加以改良魏国的国力也逐渐变强,但因此旧族对丁邦彦多有微词一直想打压,吴越力排众议果断将其改革视为国策,并制定法律至少要坚持百年。以前的贵族们在祖辈遗留的德荫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丁邦彦一上来便制定一切以功劳为原则,每个人都争着抢着去争功劳,故魏国这几年对北方少数民族和西方部分小国家的战争接连告捷,综合力量在东部大陆上排名第二,在国际上也更加具有话语权。
也许有个别国家对于最近几百年的三国是看不懂了,为什么之前的争斗不断,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的状况会突然停止,造成今天大陆东部三国之间相互依存支持又相互制衡的局面,那就不从先前几百年三国战争不断造成损失说起了,无数人口失去和各项财产也被摧毁,坚国等西方国家和西南部小国以及蓬国趁火打劫现今整片国土都有大小地方被各种协议和约定模糊,弄得如今是收回但又不是对手不收回就受气得尴尬局面,三国领土加起来在这些争斗中比先前越来越小,蜀国与菲越国在西部南漳郡有争议同时还要提防西北部的匈族,周国与在海宝岛坚国驻留军队与船舰存在历史问题,魏国与蓬国在巢州郡以及北部少数游牧民族斗争不断,所以三国的祖辈发现这些悄然变化起就举行了三国会盟,对之前三国中有争议的国土和岛屿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对于先前分属与其他国家或者民族有争议的领土采取不干涉他国政策,此举意在提升三国国力,不消耗彼此,能够最大限度把祖辈留下的每一寸土地和主权牢牢控制在自家人手里,甚至能收回哪些被他国和异族占领的土地,而至于将来三国是战还是和或者是统一,谁也不知道,至少现在战争是打不起来,三国会盟达成的各项文书和协议统一汇入《三国总要》并编入各国法律,如有个将军或者郡守违反则按罪论处,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让我们将视角对准蜀国,宰相诸葛相如组织将军编写《经兵令则》给各种兵种定级划分,举例弓箭手职称标准,令则上规定能挽一石弓的是普通士兵兵阶为三等兵,能挽一石(dan)五斗弓的是二级士兵兵阶为二等兵,能挽二石弓的是一等士兵兵阶为一等兵,而能挽三石弓的是特等士兵兵阶为特等兵。兵服也相应做了改革,在兵服左胸处有不同兵阶的标志,可能读者会好奇三石弓的弓力在实战中到底有多大,当时统一的计量单位一石约为120斤,一石为五斗,在蜀国,有一位臂力最佳的神箭甘化,一箭射出,在对匈族战争中把二百步远、二百尺高城楼上的一个敌方将领击毙,而他只有200斤的力量,只能排在一等兵,而经周朝禁军相传廖彦东有3石的力量,足足三百六十斤,为已知三国内拉弓力量之最,他的禁军有着这样的标准:选补班直,弓射一石五斗,弩蹠三石五斗,只有达到这样的标准才能入选为禁军,开了禁军选拔之标准,同时也形成其他二国禁卫军的标准。这只是对弓箭手做了具体的划分。同时还有工兵、重器械等兵种也具体做了划分,这是三国内最为专业的划分,共同对将军的要求也有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严格划分和等级鲜明的部队不断为出类拔萃的将领,论战将蜀国是一个出将才的宝地。
三国摒弃了之间的争议,各自发展,各国人才更是不断涌现,似乎一切都太多顺利,但古人依旧说的好:“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仔细看,等待三国的路途依旧迷茫,他们都在积蓄着力量,但力量究竟朝着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力量它就像是没有方向的流水,但到了哪里就就有模样,到了小溪就是形成了溪水,到了大海就有大海的轮廓,到了酒杯就成了酒杯的模样……
力量取决于掌控它的人把它引向何方,正义与邪恶也就有了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