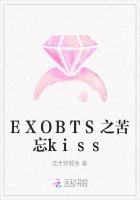清晨,她在清脆的鸟鸣声中醒来,撕开眼皮,头要炸了一般,生活一切依旧。
无意识的虚无要比有意识的现实慈悲得多。被撕裂的生活,被撕裂的记忆,就像于少甫在搬离前摔碎的一片片酒瓶碎茬一样,飞溅开,躲在各个犄角旮旯里,阴险地注视着她。稍微一不小心,就划开她的皮肤。虽不至疼到难以忍受,却让她无法安宁,细碎地折磨着她的神经,让她体会另一种意义的痛不欲生。
此刻,刘苏的心里充满着怨憎。一想到那个莫须有、荒唐的谎言,她头上的短发似乎都变成了蜿蜒扭曲的蛇,像尼弥西斯一样,满脑袋散发着一股股幽暗的怨气。
她不明白,自己深爱过的男人怎会如此不堪!夫妻十年,同床共枕,结果自己在他嘴里却连个出卖肉体的女人都不如。假若一个男人与一位小姐发生了肉体关系,多少还要付点经济,而自己十年同床共枕的男人却用这事儿来成为堂皇的理由,好成全自己的卑劣!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而自己与他的恩与情在哪里?
不是说,种什么得什么,为何自己拼尽全力,怀着希望和爱种下的却是这般的苦果?!
她在无数个为什么中激进愤恨起来,她拨通了那个没有姓名标记却烂熟于心的号码,这是于少甫搬离后她第二次拨打。
第一次是于少甫乘她不在家时搬完自己最后的东西后,将门锁好,用扔进院里的方式把钥匙还给了她。他留了一张纸条放在茶几上做说明。
晚归的刘苏看完字条后,上小院里找药匙,却久找不到,她给他打了他离家后的第一个电话:“我没找到钥匙!”
“我明明扔进院子里了!你再找找看。”他很不耐烦的声音。
”你从哪个方位扔的?“说实在的,刘苏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药匙会在院子里,换了自己估计是想不出这种方式的。
”从榕树这个位置扔进出的,你好好找找。找到没?实在找不着,我回来给你找行不?“他在电话哪头提高了声音,像是她故意找不到似的。
“谢谢!不用麻烦你了。”她没有再找,她相信他做得出来,钥匙一定就躺在院子的某个角落里。第二天,她在三叶梅的花盆边缝处找到了钥匙。
这次的电话拨通了,接的还很快。
“喂!”他的声音仍然充满磁性,还是那么悦耳。刘苏突然想到,好像从争吵开始只要她打电话,他从来都接的。她听到了悦耳声音后粗重的喘息声。
“忙着呢?”刘苏的手在发抖,声音却出奇平静。
“你在哪?不忙,在搬点东西!”
“我打电话来,是想跟你道歉的!”刘苏没有回答自己在哪里。这个问题还有任何意义吗?
“道歉?道什么歉?”于少甫的声音里是不解还有暗藏的嘲笑。
“应该道歉的呀!原来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么多年每天做完所有的家务,然后等你一回来我就躺在床上装植物人!碰都不能碰!真够难为你的,受了这么多罪,憋屈了这么多年!我还不该给你道歉吗?”刘苏想都没想,这些话就非常有条理地排好队从嘴里鱼贯而出。
“谁跟你说的?”于少甫的声音里透着实实在在的惊讶。
“既然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知道了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至少我也曾在你QQ上看过类似此话题的聊天记录。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既然敢说,还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于少甫的心理素质比她想像的要好得多,他没有被她问得哑口无言,反而以极快的速度开开始了反攻,他的声音从惊讶的状态恢复到这几个月刘苏所熟悉的痞气,“既然您都听说了,就是我说的。您就信呗!还问我干嘛?”
刘苏不争气地全身颤抖起来。“那我祝你幸福,下半辈子幸福,下半身更幸福!”她拼着最后一点力气还击他,然后飞快地挂断了电话。不能再说什么了,再说也只会自取其辱,流露自己的伤悲而已。
刘苏徒然无力地倒在床上,像一只抽空了内容没有支撑的面袋。她嚎啕起来,有泪有声。有时她也很惊奇,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眼泪?像一口不会枯竭的井。又还是像歌里唱的,眼泪是心尖上的一面湖水?
一只从院墙上借道的猫,惊奇地停住,瞪着猫族的大眼,从窗玻璃外看屋里这个发出悲声的奇怪雌性生物。忽然,它受惊了一般地飞快窜走。
她输了,输得透透的,她从来不是他的对手。这样急不择言的损他,为什么哭的会是自己?没有畅快淋漓,反而压石在心。自己的伤痛他早已不关心,愤怒又能说明什么?也许他还会安慰,看!你不也伤害了我!找个借口和理由从来都不是难事,可怜自己笨到连回击也会痛。
脑子里有太多的问题,像一本打乱了页码又没有答案的十万个为什么,杂乱拥挤的要炸了一般。
沉浸在痛苦里的她,忘记了煤气炉上还烧着水,是她早晨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
她觉得冷,想要用被子把自己包裹起来。大脑里开始观怪陆离,一会儿是过去,一会儿是现在,她像一只梭子,在期间过去和现在里穿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不知多久,她在浑噩中醒来,全身疼痛,乏力。特别是头,像是被人用千斤大锤砸过似的,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臭鸡蛋一样的可疑气味,她终于想起了煤气灶上的水。
刘苏几乎是挣扎着起来,跌撞着奋力拉开卧室紧闭的窗子。大量新鲜的空气涌了进来,带着救赎的味道钻进她被煤气侵占了的苦难的肺。
她趴在窗台上喘息了一阵子后,才拖着疲累的身体到厨房关掉煤气。才发现,壶里的水没有一点温度。原来,深陷于困扰中的她,点火的时候根本没发现燃气并没有打燃,她差点亲手葬了自己的命。
在逐一打开其他窗户时,发现只有书房的窗开着一条近20厘米宽的口。三个多小时,也许就是这道20厘米的距离让她回到了支离破碎的现实,挽救了她的命。
这时,电话响起。是妈妈打来的,她很担心女儿,却无能为力。再怎么劝说,女儿都不肯回到自己身边。女儿太倔了,就像当初执意要去丽水一样,放掉工作,放掉在家当公主的生活。也就是因为目睹女儿对婚姻的全情付出,做父母的生怕她一时脑子短路,想不开,做出什么傻事来。所以,在见不到她的日子,每天都要通个电话。幸好,刘苏也很懂事,几乎都是她主动给家里打电话的。今天迟迟不见女儿来电,妈妈就着急起来。
刘苏异常镇定地骗母亲,说自己在店里,一切安好。母亲的心这下才稳妥地回到该待的位置。
刚挂掉妈妈的电话,李青的电话也来了。她说见刘苏一直没来店里,问问她好不好。
刘苏笑着说自己今天有点事不能去,店里就辛苦李青了。
静下来的刘苏开始庆幸自己没有在这场意外里死掉。假如她死了,在别人口舌中,不过是世间又多了一个含恨而死的弃妇。就像前些日子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的女子,用生命换来的不过是几天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论,再就被遗忘。自己觉得再冤枉,老天不会为了自己的委屈下一场三月雪,因为这里是春城。反而,她更是会成为于少甫所说的那个寄生虫一样的女人,没有他的照料连活都活不下去,只得选择轻生。
如果真意外了,无限伤痛的只会是自己的父母,他们的晚年生活里要是没了自己,该会是何等的凄冷?而那个能编造谎言的男人,将会得到解脱。丧偶听起来应该要比离异更让人同情和理解。
想到这些假设,她连连吸气,她不想活着时委屈,再不清不楚地告别世界。既然上天归神管,下地属鬼辖,自己为什么不好好地活着?至少不能再这样的颓废,荒唐给地自己制造意外。
想过这些后,她居然觉得饿,饿的饥肠辘辘。不记得有多久,她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刘苏打电话订了德克士外卖。汉堡,鸡排,冰淇淋,统统全部吃完。
再过半个小时后,她蹲在马桶旁吐得一塌糊涂。这一次,她没有半滴悲伤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