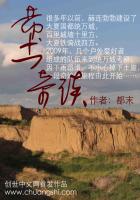辛雪安和肖里郎从村长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真相大白了!”辛雪安兴高采烈地说,“酒仙还没有起床吗?叫他快起来抓罪犯去!”
钱玉珠和美美婷正在互相帮着梳头。美美婷笑着问:“你们昨天晚上就谈了整整一晚上吗?”
“没有,谈到一点多,村长就叫我们在他家睡了。”
钱玉珠问:“你们能肯定谁是凶手了吗?”
“是的,我们现在有证据了。”
“证明他杀了红英?”
“是的。昨天晚上村长叫了你们村里的一个人来,那人说红英失踪的第二天,他看见凶手从隧道里出来,从悬梯上下来。”
美美婷说:“说了半天,凶手到底是谁呀?难道不是村长吗?”
大家大笑。笑完后辛雪安说:“凶手是道士呢。酒仙呢?叫他快起来!”
“酒仙上厕所去了,”钱玉珠说,“由我们去抓罪犯,这行吗?我们不是公安呀。”
酒仙早已听见了这里说话,这时已经出来了。
辛雪安说:“这有什么不可以?我们抓了罪犯,押送公安局还立功呢。破了这么个大案子,我至少可以进县公安局的刑侦科了。”
酒仙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来辛雪安是为着这个目的才来参加破案的。他和酒仙自己的激于义愤的目的很不相同,又是半途加入查案没有出多少力的,现在却大有把功劳完全抢过去的意思。酒仙想,要抓人你自己去抓吧,我可不想陪你做无用功了。他又想到道士从隧道里出来只能说明他也许见过红英的尸体,不能就证明他杀了人,况且他进隧道是红英失踪的第二天的事情。但是他不想说出来,只是想,辛雪安这个警察专业的毕业生,分析问题还不如我周密呢。
“好!”美美婷一边换鞋一边说,“我们现在就去吗?”
“你们两位女士就不用去了吧,这是挺危险的,出力的事情,你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要去!你管得着吗?”美美婷对肖里郎吼叫,唬得肖里郎噤若寒蝉。
“先吃饭吧,”钱玉珠说。
饭后,酒仙表示头痛,没法去抓人了。钱玉珠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也没有说什么。钱父是天还没有亮就出门看水去了的,辛雪安就叫上钱玉珠的哥哥一起去。
翠草绿禾经过了一夜的凉爽,已经恢复得生机盎然,在无风的晨光里争浓斗艳。迟归的青蛙鸣声稀落,轻盈的鸟儿常常从禾苗间飞出来,站在青枝绿叶间撩人地卖弄它们世界的情歌。细心听去,一只鸟儿唱起来,远处必然有另一只鸟儿用相同或者相谐的曲调应和。看来在芸芸众生中每一只鸟儿都不会失去了它们的情侣的,它们自有互相连接的纽带。
鸟儿的叫声节奏感很强,人在走路时自然而然地和着鸣声最清脆的那一只鸟儿的节拍下脚。
庄稼地和林地过渡的地方是一大片茅草,草高高的,密密的。这里离人家已经很远了。
美美婷走在最前面。她忽然指着路边说:“快看快看,你们快来看,这儿是怎么了?是不是有好多人在这里睡觉过?”
这地方稍平。紧邻路右边的方圆一丈之类,凌乱的草匍匐在地。有几丛草被拔断了,到处散落着。
辛雪安拿起一些断草来看,草很新鲜,一点都没有枯萎。
“昨天日落之后到现在以前这一段时间,这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打架啦,或者小孩子玩耍啦什么的。”辛雪安说。
他用脚把茅草往上扶,可是草都已经折了,扶不立了。他发现草间有一个黄色的东西,便拿起来看,原来是一个简易丁烷气体打火机。
“不是小孩子,是大人,”他说,“不管它,我们班我们的事情。”
不久就走进了树林。这一片全是稀疏的野栗子树。树间芳草肥美,蜂缠蝶绕。草被人踏出一条线来。
美美婷顺着踏成的线望过去,大吃一惊说:“那边有个人!”
那边确实有个人,是悬在空中的,双脚伸直,离地面有三尺高。
美美婷哆嗦着直往后腿。辛雪安越到前面去,领着众人跑了过去。
一个人脖子上拴了一根绳子,吊在横斜的粗树枝上。他赤脚长衫,正是比目山上的那个道士。
道士身下的草凌乱不堪,两只竹耳草鞋吊在地上。
“他,他为什么要上吊?他,他知道我们要来抓他吗?”
没有人理会美美婷的话。
钱玉珠的哥哥抱住道士的双腿左摇右摇,怎么也放他不下来。他只好爬上树去,叫辛雪安抱好道士向上用力,让绳子松了,他才解开绳子。
道士“噗”地一声倒下地去,把辛雪安也带倒了。
辛雪安爬起来,众人围上去。辛雪安解开道士的长衫去摸他的胸口,胸口早已冰凉。
“他已经死了。”
“那么我们还抓他不抓呢?”美美婷颤栗着问。
辛雪安恼火地瞪了美美婷一眼。肖里郎赶忙说:“他一定是畏罪自杀的,你认为呢?”
“不是自杀,是他杀。”
“别人把他吊死的?”
“不,别人把他杀死以后,又把尸体吊在树上,故意给人造成自杀的假象。但是他手法太拙劣了,被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为什么?”美美婷说。她想问:“你看见了吗?”但是怕辛雪安再次瞪她,终于没有说出来。
“凡是吊死的人,必定是瞪着眼睛,大张着口,长伸着舌。这个人不是,说明他在被吊起来以前就已经死了。你们看他的太阳穴有一团青的,必定是有人一下子击中了那里,就把他打死了。对了,手上还有划伤,衣服也破了,说明死前曾经和人搏斗过。”
没有人说话。良久,辛雪安沮丧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可能上了陈长远的当了。”
美美婷因为惊恐,说话还有些不关风,“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陈长远骗我们道士是凶手,并且买通了一个人为他作证,然后杀了道士,弄得个死无对证。”
辛雪安闷闷不乐。他俯下身子解开道士的衣服到处查看,除了又发现一些擦伤外,什么也没有找到。道士的口袋里空空如已。
“我明白了!”美美婷双手一指,说,“刚才在下面我们看见草被弄乱了,陈长远一定是在那儿杀了人,然后把尸体搬到这儿来吊上去的。”
辛雪安没有说话。他早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了。
钱玉珠说:“哥哥,你和道士来往过,他抽烟不抽烟?”
“他不抽烟的。”
“昨天晚上陈长远点烟的时候用的是一个绿色的打火机,我记得很清楚,”辛雪安说,“但是即使这个打火机并不是村长的,也不能排除他杀了人。道士虽然不抽烟,他做饭之类的一定要用打火机的,他一个人,出门把小东西随身携带也不奇怪。所以不排除是他的打火机。还有,凶手随便弄一个打火机来丢在这儿,让我们去追查,扰乱我们的视线,也有可能的。”
“道士生火用的是煤油打火机,”钱玉珠的哥哥说,“我们村里大多数人都用这种打火机的。”
美美婷忽然想到一件事情,打断正在张口说话的辛雪安说:“昨天晚上你们不是在他家里睡觉吗?他在家不在家你们知道吧?”
辛雪安和肖里郎对视一眼,两人都没有说话。
美美婷追问:“他睡觉的房间离你们的房间近吗?”
“他跟我们睡一间房间,”肖里郎说,“我和辛雪安一张床,他一个人一张床。他不会那么大胆吧?半夜悄悄出门去杀人,不怕被我们发现他不在吗?”
钱玉珠说:“他会使迷药呢,说不定让你们吃了迷药,你们一觉就睡到天亮了。”
“不对,我半夜醒过来一次,看见他还睡在床上呢。”肖里郎说,又补充说,“我们睡觉没有拉灯的。”
“还有,”辛雪安说,“道士住在山上,按照常理他夜里不会还在这个地方。如果是村长有计划的杀人的话,他得考虑时间:上山下山要八小时呢。我们一点钟睡觉,六点半起床,中间只有五个半小时时间,他要上山杀人是办不到的。就算他事先知道夜里道士会在这儿,他到这儿来回要四个小时,杀人并且吊上树怎么也得半小时吧,可是肖里郎中途醒来还看见他在床上呢。除非外界影响,人正常睡觉往往都要两个小时以后才能醒来,所以肖里郎应该是在三点以后醒来的。对了,你醒来之后听见鸡叫了吗?”
“没有。”
“也就是说你是在四点之前醒来的。这前后睡觉的时间都不超过四个小时,这点时间里村长是不可能赶来杀了人然后赶回去的。”
“看来凶手是清白的了,不不!我是说看来陈长远是清白的了。那么是谁杀了道士呢?”美美婷说。
“我们上山去看看,”肖里郎说。
“是的。凶手杀人一定是有目的的,如果是跟幽灵的案子有关的话,他杀了人多半也会上山去,因为他得考虑道士有可能有对于自己不利的证据留在山上呢。现在事情变得复杂了,道士被杀了必须报案。”
“你不是警察吗?还向谁报案?:美美婷说。
辛雪安不回答。他现在实习已经结束了,正式工作还没有找到,并不是警察身份。“玉珠和美美婷回去给村长说明情况,叫他去找派出所,我们三个上山去,”他说。
“不行!我也要上山去!”美美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