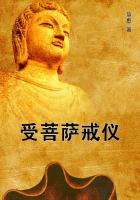秋风习习。
CX监狱九监区。
六十四个新剃的光头,八八见方,纵到横排斜成线,整齐而精神,在将腿去的朝霞中反着光。
六十四件崭新的囚服,蓝白条纹,折痕未消,长的遮手,短的露脐,穿在这群无论年纪还是体形,都参差不齐的人身上,仍显得清爽而利落。
监区长郑廉,大马金刀地站在操场中间,正在给新犯们训话:“欢迎大家来到九监区!不!不能说欢迎!监狱不欢迎任何一个人来!你们每个人,都是因为触犯了刑律,不请自来的!既然来了,就应该搞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好!你来说!”他指向了第一排中间的一个眼镜。
“报告警官,服刑人员夏雨请求发言,报告完毕,请指示!”
“不错!举止规范。好!现在回答我的问题!”
“报告警官,这里是监狱,我是罪犯,我到这里来服刑改造。回答完毕,请指示!”
“好!回答得简洁明快,看来三个月的入监教育没有白受。既然你们该学的都学了,该知道的也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一句话,一切都按《行为规范》上的来!听到没有?”
六十四人齐声回答:“听到了!”
“不够响亮!大声点!听到没有?”
六十四人齐声大叫:“听到了!”
“汪——汪——汪!”怎么突然冒出了第六十五个声音?
人们这才发现,一只其貌不杨的土狗,昂首挺胸地蹲坐于第一排的队尾,神情专注地望着监区长,俨然就是与会的一员。
“二排!你搞什么乱!又不是问你,你答应啥?!”监区长急声喝斥。
“汪——汪!”那狗却以为又在叫它,再次认真地回答,还挺了挺身子,铆足了十二分精神。
不知是谁忍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就象点燃了炸弹的导火索一样,引爆了其他人的喜剧神经,大家“嘻嘻哈哈”地笑成了一片。原本十分严肃的气氛,一下字变得轻松了起来。
监区长的眼中露出几分尴尬。他不知道这个时候该说点什么。
倒是站在一旁的教导员反应很快,见怪不惊地笑着,走向前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样很好嘛!我们就是要在轻松的氛围中改造,在希望中改造!你们来之前,我粗略地看过大家的档案,除个别短刑犯外,大多数人都是需要减刑的。九监区虽然是老字号,如今却是重新组建,你们都是开国元勋哦!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一切都从头开始,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希望。减刑分数线,改造看表现。该怎么做,不需要我来教你们吧?在这儿,我代表郑监,以及九监区的全体干警,给大家表个态:该我们做的,我们一定会做好;该我们争取的,我们一定会争取到。于公,尽一个人民警察的职责;于私,对得起你们每一名服刑人员和你们的家人。但是,丑话我也要说到前头,如果你们哪个调皮捣蛋,不遵守监规队纪,犯到我手头了,到时候就有他的好看!”
一见很多人的笑容都僵在了脸上,气氛再次严肃了起来,于是他又将话锋一转:“早先,有个别老犯,给我编了个顺口溜:卿杰,卿杰,只管清洁。是啊!当初我在生活卫生科当干事,现在却是监区教导员了。在其位,谋其政。九监区的干部,犯人我都得管了。欢迎大家来打小报告!按行规,我会保密的!”
几句话,又将大家逗乐了,他满意地笑了笑:“看郑监还有什么要指示的。来,大家鼓掌!”
掌声迅速响起,十分热烈,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明眼人不难看出:“承上”是肯定和赞许,“启下”是期望与鼓励。
清了清嗓子,郑监又发了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啰嗦。我想说的,刚才卿教都替我说了。他说得很好,你们大家都要照他说的那样去做。记功,减刑,才是你们真正的希望和出路!我就说这么多!杨指导、周主任、乔队,你们有没有要说的?没有就散会!乔队,你安排一下,先把包裹放进贮藏室,再把监舍的卫生打扫了,然后把床搬回来餔好,晚上再开个室长会。周主任,你指派一下临时的室长,再安排几个值班人员。杨指导,辛苦你老人家,还是守一下值班室。我和卿教还有很多事情要和狱部协调。
炒豆子似的交待完一切,郑监拉着卿教,回了办公室。那只叫“二排”的土狗,摇头摆尾地跟在他们身后,走出了人们的视线。
周主任拿出花名册,念着每个监舍人员的名单。被点到名字的人,答“到”后出列,到操场另一头,在众多的编织袋、蛇皮袋中寻找着自己的行李。
乔队在一边大吼:“铺盖、垫絮不要动它!一会儿铺床时再来搬。各人拿好东西,按监舍次序排好!一监舍的跟我来!”他把第一拨人带进了监管大楼的贮藏室。
还未被点到名的人当中,飞机有些沉不住气了。(飞机,本名:乐飞,十九岁,盗窃罪,判三年,入狱前无业。)他拉了拉前面那个人的衣服,小声说到:“坤师,不知道我们几个会不会被分开?但愿能在同一个监舍。”
坤师脸上露出了狡黠的微笑。(坤师,本名;龙玉坤,三十八岁,非法持有毒品罪,判二年,入狱前经营小型茶坊。)他知道飞机看不到他脸上的笑容,于是背过右手,做了一个“V”的手式:“你放心!教授早做好了安排。”
飞机一脸疑惑的回头看身后那个人。
教授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教授,本名:吴昊,四十三岁,贪污罪,判十年,入狱前某机关财务处长。)
飞机正准备向教授发问,发现旁边有人在拉他的衣角。
憨弟正皱着眉头,嘟着嘴给他示警。(憨弟,本名:曾强,十八岁,故意伤害罪,判五年,入狱前某大厂保安。)
飞机这才发现周主任向他走了过来。
“小鬼,你懂不懂规矩?在队列里七拱八翘的干什么?”周主任黑着脸问道。
“报告警官,有蚊子咬我,我忍不住才动的。”
“秋天都到了,哪儿来的蚊子?”
“报告警官,总有漏网的,坏蛋是打不完的嘛。不信,你看!”飞机伸出脖子,指着颈后一处“红肿”。
周主任摇了摇头:“算了。待会儿到我那儿去檫点药。这秋蚊子,还真的有点凶!”
飞机伸了伸舌头做了一个鬼脸:“谢谢警官,我擦点口水就行了,就不麻烦你了。”
“也好。”说罢,周主任继续点名去了。
憋了半天的憨弟,终于笑了出来,心里对飞机崇拜得五体投地:居然把胎记说成蚊子咬的,飞机哥简直就是天才。
名点完了,一切如坤师所料。从入监队一监舍来的五个人,就有四个人分在了同一个监舍。
大家拿行李的时候,飞机疑惑地问坤师:“我们真的就分在了一起,你们是怎么弄的?”
“早上在入监队选人的时候,是诗人帮着抄的花名册。教授让他把我们几个的名字写在一起,尽量靠后一点。”坤师得意地说到。
“我明白了,干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打乱了重排,所以我们就一起分到了七监舍。但是诗人呢?他自己咋个被分到了一监舍了呢?”飞机对这一点始终没想明白。
坤师失望地摇了摇头:“你这个笨蛋!诗人的表弟在狱部给监狱长开车,他肯定要受特殊照顾的嘛!你又不是不知道?”
“哦——”飞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去吃安胎(指干轻松的活路)了!”
说曹操,曹操到,诗人已经放完了包裹,满脸流着大汗地向这边走来。(诗人,本名:夏雨,三十一岁,挪用公款罪,判七年,入监前某刊物编辑。)
满面愁容的诗人,走到教授旁低声地询问:“他们叫我值班,你觉得如何?”
“好啊!你当了红毛(事务犯),我们也跟着沾光!”教授打趣道。
“快别洗我脑壳了。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他们?”诗人这时候看起来有点着急了。
“他们是冲着你表弟的面子上,第一次你就回绝,以后恐怕就不好相处了。何况这个位子,是别人争都争不来的,你不要轻易就放弃了。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我都是第一次进来,两眼一抹黑。不过不用怕,有坤师在,他是五进宫的老鬼了,有什么事都可以问问他。加上这几个难兄难弟给你扎起,你也该雄起了噻!走一步,看一步;在哪个坡,唱哪个歌。这点能力,我相信你还是有的!”教授给诗人打着气。
“值班简单得很,只要把人,数清楚就对了。你肯定没得问题!”坤师这时也附和着。
“你不会因为这个,吓出了一身汗吧?”飞机趁机恶作剧到。
“肯定是没有人帮你搬东西,把你累到了,出的汗!飞机你就不要乱说了!”憨弟永远都最耿直,“要搬东西,你随时喊我!随叫随到!”说完露出一副憨厚像,惹得众人忍不住都笑了。
“飞机乱说话,罚你一会儿去帮诗人铺床!教授的床,就由我亲自出马来铺!坤师和飞机这对志年的老乡,是见不得也离不得的冤家。所以说起话来总是一个钉子一个铆。
“是啊!飞机,只有麻烦你去帮他一下了.我和他都是,饱得饿不得,怕冷不经热,闲得累不得的笨家伙啊!”教授无限感慨地说。
“收到!这是一个少先队员应该做的!”飞机继续搞怪地行了个军礼。
这边,诗人敏感而脆弱的神经,被这几个老少难友的热忱所触动,眼眶已有些湿润。
“七监舍——”乔队又一声大吼。
“到!”几个人同时回答。
“我们放东西去了。你也去把话回了吧!”教授拍了诗人一下,背上了一个大号旅行包。
憨弟抢先背了个大包,两支手各提了两个大编织袋。
飞机左手提了个大蛇皮袋,右手提了两个小包。
坤师脚不方便,右手提着一个小编织袋,左手还同教授一起提着一个大编织袋。
看着四个人竟拿了十一个包裹,教授又笑着回头对诗人说:“拥有得越多,负担就越重。我们的路都还长,应该轻装前进才行!”
教授随便说的一句话,就点醒了梦中人。诗人突然明白了什么,眼睛里一亮。
又阴又潮的贮藏室里,一股股的异味,让人受不了。坤师给飞机使了个眼色。飞机一边拉住憨弟,一边对其他人说:“我们这组东西多,要整理一下,你们先放吧,放完了我们在来放。”
等其他的人在地上放完了第一层,坤师才指挥飞机和憨弟将包裹重放在第二层,并将教授的几个包及旅行袋放在了最上面的第三层。
一行人回到操场上,等最后一拨人去放包裹。正在这时,飞机看到了又一个提着五个行李的人,再次笑开了:“你们看,那不是千王吗?他装了三个月的跛子病。昨天还要四个人抬他,今天就能提五个大包,还跑得跟兔子一样快。一不小心就穿帮子!哈哈!”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
“病从嘴入,祸从口出。飞机啊,很多事只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千万不要挂在嘴里哦!”虽然自己也在笑,但是教授还是忍不住要提醒这个可爱的年轻人。
翻了翻白眼,伸了伸舌头,飞机用一个鬼脸作了回应。
周主任拿来了扫帚、拖布,发给了各个监舍,要求大家在吃中饭前把监舍及门前的走廊打扫出来。
教授作为临时室长,带着手下的七个人来到七监舍。这里和入监队完全一样。外间是七米乘四米的睡房,两米乘四米的里间被隔成了两半,一半是厕所,一半是洗漱间。睡房顶上装着两盏日光灯和一台可以二百七十度转头的风扇。厕所的两个蹲位中间,是一个有上下水的陶瓷洗脸盆。洗漱间瓷砖砌的洗漱台,有一米二高,八十公分宽;正对门的窗户下面,就是洗漱池了。
唯一不同于入监队的就是,这里长辈脏得来可以:厚厚的泥灰,已看不见地砖的颜色;墙面污渍点点;墙角蛛网密布;洗漱池和便盆积满让人恶心的黄垢。
“啧啧”的咂嘴,教授难以想象,这就是他们要居住的地方。
坤师笑着安慰他:“不用担心。要不了一会儿,到处就会干净得照出人影子来!”
“对!事在人为。就象你经常说的:和尚是人做的,劳改犯也是人当的!”教授听他这么一说,也来了劲。
“大家都过来。”坤师越俎代庖,开始发号施令,“我帮教授给大家分分工。憨弟,你个高,先拿干净扫帚把蛛网和扬尘打扫了,然后把墙上的黑点点擦掉。飞机和火星人,你们负责地面,先用水冲,再用拖布拖,,最后用帕子擦干净,必须照得出人影才行。老绵羊,你就把洗漱台、窗台、洗脸盆,反正瓷砖砌的地方,给我抹干净。弹绷子,你就把窗子擦了,等一会儿床抬回来了,你还要爬上去把灯管和风扇打整了。短冬瓜,你还是干老本行,把金鱼缸{便盆}刷干净,我去给你找牙刷和洗衣粉。我负责门和门道。教授,可能兵器(工具)不够,得想想办法!”
“我马上去找诗人,看能不能再找一两个拖布。”教授说完就出去了。
憨弟拿起扫帚,二话不说就开干了起来。
飞机冲着火星人吼道:“愣着干啥?还不拿桶接水去!”
其他人瞄着阵势不对劲,也逐步进入了自己的阵地。
教授很快眉开眼笑地就弄回来一把崭新的扫帚和两把旧拖布。
坤师捐出了自己的旧牙刷和洗衣粉。
大家热火朝天地开始干了起来。教授一会儿帮着冲厕所,一会儿又去抹抹窗台。反倒是坤师成了监工,在那儿指手画脚,就连该他负责的门和走廊,都是憨弟帮他搞定的。
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
七监舍就象被施过魔法一样,变成了另外一番景象:窗明几净,光可鉴人。
看着大家伙的劳动成果,教授又发起了感慨:“劳动真的改造人啊!象我这种懒人,在家里,扫帚倒了都不会扶一下。今天却累出了一身的毛毛汗,结果还很有成就感。真的是该进来锻炼锻炼啰!”
“教授。如果你这种人都该进来的话,我这种人就不该出去了!”坤师自嘲道。
两人对视了几秒钟,而后哑然失笑。
集合、整队、报数、唱歌。
虽然一切都按部就班,却总觉得有些忙乱,就连临时安排的四个分饭的人都明显的缺乏经验,分到后面就是汤多菜少了,于是被不少人咬牙切齿地咒骂成了“杂种。”
杂种一词,在劳改队使用频率之高,用途广泛,已经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无论内涵与外延,乃至词性,都得以无限的扩展,甚至变成了语气词。
三监舍的冲棒,从小半碗莲白中找到了一片肥肉,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暗自庆幸:“居然这么大一片。杂种!”
教授从入监队带上来的一瓶“饭扫光”,此刻堪称极品佳肴,虽然四个人每一筷子都得小心翼翼,生怕会遭遇异样的目光,但还是很快地吃了个瓶见底。
之所以说“带上来”,是因为入监队所在的监管大厦的五楼,此时正与九监区的操场相平行。
原来由于全国监狱系统战略布局的调整,从边远山区转移到城市近郊,从农耕模式过渡为工矿模式,先前远在雨城兰溪山中的CX监狱,如今部分搬迁到省会芙蓉城外围的大苞山上。高砌砍,低平川。一座大苞山竟被削成了三级大台阶。最下面一级最大,由三个相连的部分组成:十二到十七监区的确女监;七、八监区组成的“准外劳”;医院、大小厨房、超市、小间(禁闭室)、砖厂、纺纱车间、服装车间、制鞋车间以及一幢“T”形监管大厦,里面住着四、六、十一、十八监区(入监队);第二级次之,只有一幢“T”形监管大厦,里面住着一、三、五、九监区,还有一个刚刚动工的大车间;第三级空着已经平好的地,是留给兰溪山上二大队的。
随便说一句,五监区监区和十一监区监区众多的外劳点,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芙蓉城四周的区县。更为稀奇的是,狱部的行政综合楼却位于数公里外的城区。
如果把整个CX监狱比作一个糟糕厨师做出的杂乱拼盘,还不够准确,而要说成一个变态杀手四处抛洒的碎尸,才显得更为贴切。
无论拼盘也罢,碎尸也好,哪怕是守着厕所,这里面的人照样“吃嘛嘛看”,一顿素烩莲白,大米饭的午餐,前后不到十分钟,就已风卷残云了。
大家吃完了午饭,有次序地回到了个各自的监舍,作短暂的休息。因为干警也是人,也是要吃饭的。
飞机看到憨弟正帮着教授洗着碗,便嘻皮笑脸地说:“这儿还有两个,你就顺便了嘛。”说罢,将自己和坤师的碗,放在了窗台上。
憨弟上当又不止一两次了,于是无言而又无赖地扁了扁嘴。
十几年的机关生活,让教授养成了午眠的习惯。他席地蜷缩在角落里,头靠在墙上,已在假寐。
坤师脱下了自己的囚服外套,盖在了教授的身上。
教授闭着眼睛,以一个微笑,表达了对坤师的谢意。
飞机的手搭在弹绷子肩上,两人靠在监舍门口,望向楼上监区收工回来的队伍,努力寻找着自己认识的人。
而刚把碗洗完的憨弟,却已躺在地上,大声的扯起了呼噜。
简单的人,总有着简单的梦。憨弟又梦见他带着春燕去钓鱼,还是在东风渠的岸边,还是躺在青青的草地上,蓝蓝的天,还是和暖的阳光照在身上,春燕依旧在一旁捣着乱。
先是挠他痒痒,憨弟尽量憋住不笑;然后是向水里扔石头,吓跑了所有的鱼,憨弟假装生气,不理她;最后是扯了根狗尾巴草,又探耳又探鼻孔,弄得憨弟不停地打喷涕。
和梦里一样,现实中的飞机也是,先挠他脥肢窝,再在他耳边打响指,最后用布头戳他的耳道和鼻孔。
让飞机又是羡慕又是气愤的是,这头猪怎么弄都弄不醒。
飞机正准备加大动作,突然屁股上挨了一脚。
原来是躺在不远处的坤师干的。他正冲着飞机怒目相向,把手指竖在嘴唇上,发出“嘘”声,示意飞机保持安静,不要影响到他人的休息。
飞机做了个招牌式的伸舌鬼脸,然后甩出中指,以回敬刚才屁股那一脚。
坤师一脸苦笑,知道飞机欺负自己,怕影响别人的午休而不好发作,只好用夸张的唇语,咒骂了两句。
飞机以牙还牙,以夷制夷,也用唇语与坤师对骂,一边骂着,一边还得意地扬着眉毛。
这时坤师才反应过来,心里大呼上当:这个臭虫本来就有小儿多动症。正愁没人陪他玩,我居然自动送上门。越理他,他的疯劲就越大,还是睡我的觉为妙。随即翻身背对飞机,开始了闭目养神。
飞机一下就失去了所有互动的观众,顿时索然无味。一阵倦意袭来,打了个哈欠,他又俯身睡去。
刚刚迷迷糊糊,似梦非梦,就被憨弟摇醒:“飞机、飞机快起来集合了!”
操场上,乔队在作下午的安排:“等一会儿,我们就去医院旁的备勤楼搬床。一个监舍六张,十四个监舍,一共八十四张。虽然你们现在只住了八个监舍,每个监舍只住了八个人,但是很快就要从入监队和其他监区,调来很多人,我们要作好准备。这么多床,一趟可能搬不完,我们就多跑两趟。老弱病残可以留下,由周主任来安排打扫教室、办公室、开水房这些公共区域。大家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可能是才睡了觉起来,大家回答得有些懒洋洋的。
坤师看着教授。教授却看着坤师的腿小声说:“我宁愿去搬床。”
“那就一起去搬床!”坤师指着自己的残腿自信地回复。
飞机笑嘻嘻地凑上前:“万事都有我和憨弟,一切全搞定!漏怕提!”
“不是漏怕提!是漏,怕不能提!”教授这么一纠正,把大家全逗乐了。
一行五十来人,向山坡下走去。不知什么时候,那条叫“二排”的土狗,又出现在了队伍中,并忽前忽后的在队伍中穿梭。
憨弟当保安时,厂里有只退役的军犬,家里也曾养过狗,便对狗有种天生的亲近感。每当二排跑到他跟前,他都会轻声的呼唤:“二排!二排!”并用指挥军犬的通用手势,五指并拢,从胸前向外平挥,要求它小跑前进。
无奈二排只是只没受过任何训练的本地土狗,除了用陌生的眼神,打量了一番这个叫它名字的大个子外,对军势手语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与憨弟恰恰相反的是飞机。他小时候偷别人的桃子,被邻居家的狗咬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飞机对狗总是敬而远之。每次二排逼近,他总是往教授和坤师两人的中间卡。有一次,险些把坤师挤倒。
说来也怪,飞机越是害怕,二排越是凶他。就象是在炫耀自己的胜利一样,那狗还不时地冲飞机吼上两声。
坤师起先还嘲笑飞机的胆小,见他是发自内心的害怕,便安慰了起来:“一只破土狗,怕它干什么?!恶狗如恶人,你弱它就横。你越显得怕它,它就越是起劲。找机会我和你一起,教训它一次,他就会一辈子都怕你了!”
飞机不敢相信地回了一句:“真的啊?!”
说话间,已经来到了备勤楼下。
乔队打开一间房门,对外面的人说:“一上一下,两个床架,两个挡头。八十四张,先理清楚,放在门口,你们在搬走!”
大莽、二莽、钢钎、冲棒、憨弟奎娃六个大块头进去下货,其余的人在门外,帮他们分类摆放。
趁着其他人在忙的当口,坤师上前给乔队发了一支烟,并点燃了或。
“你脚不方便,跟着跑出来干嘛?”乔队有些奇怪。
“在入监队关了三个月,都关瓜了,出来走动一下,透透气。何况我们这些人,在哪改造都积极主动,做活路从不偷奸耍滑、拉稀摆帶。既然跟着乔队出来了,肯定就会尽力,我能搬多重就搬多重!”坤师表着态。
“咿——,一看就是个老鬼。不要光会说,不会练哦!”乔队一来就打预防针。
坤师自嘲地笑了笑:“看你说得。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的表现,你是看得到的噻。其他的不敢保证,做活路上,是不得给你乔队丢脸的!”
“那就好。我就喜欢爽快的人。”
“对了。乔队。我们监区的主业是什么?”
“现在还没有正式定下来。据说狱部联系了一个做假发的业务。女监已经做了一年多了。另外好象还会帮八监区编编藤椅、竹篮之类的东西。反正都是手工活路,累不死人的。”
“是啊,肯定比兰溪山上采茶,要轻松得多。”坤师心中有了底,便开始东一句,西一句的和乔队闲聊。
抽完了第三支烟,满身是灰,满头是汗的冲棒跑过来:“报告乔队,八十四张床,数清楚了!”
乔队回身对大家说:“力气大的,就多搬一点,争取少跑两趟。”
于是大家两人一组,自由组合。
憨弟和莽娃搬了六张床架;飞机和弹绷子抬了三张闯架;坤师和教授只扛得动两张挡头。大家各使各力,各尽所能,三长两短地加起来,这一趟也就运走了三十张床。
由于爬坡上坎,一个来回居然用了四十多分钟。第二趟明显不如第一趟有劲,只搬走了二十多张。第三趟虽然勉勉强强搬完了所有的床,少数人已经累得力所不支了。
虽然都是抬前面,上坡不会太吃力,到最后一趟时,只抬着一张挡头的教授,腿在打着颤,头在冒着汗,脱去了外套,只剩下一件内衣,也被汗水湿透。
看着憨弟之流健步如飞,教授又是羡慕,又是惭愧,又是心酸,回头对坤师说:“老了,不行了。再歇一口气。”说罢放下了手里的东西,喘着粗气。
离监区不到五百米,大多数人已经到了。看着教授两手支腰,弓着身子,坤师知道他已经到了极限。“不用着急,休息一会再说。”一边安慰着教授,坤师一边向人群挥着手。
不一会儿,憨弟和飞机赶了过来。“你搬床,我扶教授。”飞机简明地分了工。
飞机这一搀扶不要紧,教授两眼一黑,险些晕了过去。教授在心底给自己打着气:吴昊啊,千万要挺住!不要在年轻人面前丢脸哦!这点累就把你打倒了,你还有七八年,又怎样才能活出去呢?!挺住了!”
一见教授脸色惨白,飞机关切的问候:“你没事吧?”
“没事。只是有点贫血,回去喝口水,歇一下就好了。”教授挤出了一个灿烂的苦笑。
这个微笑,在飞机的眼里是那么勉强,在教授的心里是这么顽强。这就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主观的实际和客观的臆断。
终于,累得贼死的一群人,瘫在操场上,横七竖八,象糊了牌的二五八万,而等着他们的,还有一大堆事情还没有做完。
坤师跟着乔队,溜进了办公室倒来一杯热水,又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小包葡萄糖,放进水里,端给了教授。
“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入监队那么凶险,站两三个小时的军姿,连续跑四五个小时,你都熬过来了,也没见你这么恼火噻。多半是营养跟不上。”坤师寻思着找原因。
“是啊,是啊,这三个月,又是学习关,又是过生活关,饭都没吃伸展过,还每天这么大的运动量,咋不把人拖垮嘛!”飞机也在一旁抱怨。
“劳改队,过三关,学习关、生活关、劳动关,是必经之路。还好,我们已经闯过二关。现在下了队,除了劳动,一切都要轻松一些。放心,只要有我坤师在,就吃得到荤菜。”
“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荤菜看不见,晕菜倒是天天见。吃牛不打草稿!”飞机打着坤师的顶张。
“几天不见,刮目相看。跟着诗人耍了两天,就满嘴成语,出口成章了。小伙子有前途!到时候肉弄回来,不要跟着叔叔泊泊两个抢,就是对的!”
“你幺爸我,又不是没有吃过肉!就是没有吃过猪肉,也看惯了猪跑,有啥子好稀罕!会跟你抢?!”
看着这一大一小在斗嘴,教授的心情好了很多,一杯葡萄糖水,也让身体恢复了动力。振作了一下精神,教授发了话:“大家歇够了没有?歇够了,就把床搬进监舍装好、铺好,晚上才好睡觉。”
“要得!”七监舍的人答应了一声,开始了行动。
六张床很快就装好,并且擦拭干净了。教授安排憨弟和飞机睡在上铺,其他人睡下铺。
飞机正准备提出异议,却发现坤师正恨着自己,只好悻悻地说了一句:“吃得亏,打得拢堆。”便跑去给诗人帮忙去了。
憨弟从操场上抱回了四个人的被褥,协助着坤师铺床。
先是上铺,后是下铺;先铺垫絮,后折被盖,坤师熟练而快捷,如同受过军事训练。
“大家累了一整天,辛苦了。来,抽支烟,休息一下。”教授拿出一包香烟,每人递上一支。
“不要把我忘了!”刚走出门的飞机,听到要发烟,一个踹步又飞进了七监舍。
教授自己拿出一支,把剩余的大半包扔给了飞机:“飞机哥,你朋友多,这些拿去为人处事。”
“谢了!”飞机接了教授甩过来的烟,一下又飞得不见人影了。
“不要把他给惯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安排购物,很多人都断烟了。”坤师有些担心。
“没关系的。我是属耗子的,存得有冬粮。”教授笑着,鼻子里冒出了袅袅的青烟。
晚饭过后,人们不再象呆在入监队时那样,龟缩在监舍内记背《行为规范》,而是三三两两的,在走廊里闲聊或散步,好一派悠闲景象。
虽然山坡下那座监管大厦,挡住了部分风景,然而站在走廊的尽头,从楼房的旁边,仍能窥望一角,丘陵下盆地中广阔的平原:鲮次栉比的高楼,小如针盆、火柴;穿梭往来的汽车,微似甲虫、蚂蚁;道路如同蛛网,把一切粘黏于其中,杂乱而有序。外面的世界,象一幅微缩景观,展开在眼前,想象着自己曾经也是其中蠢动的一员,不禁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此时的天空中,一轮红彤彤的夕阳,缓缓下坠。那油亮诱人的颜色,跟泡得返沙的盐蛋黄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就连旁边被晚霞映红的云朵,一跎一跎的,也象是沾了红油的白面馒头,虽然刚吃过晚饭,照样让人禁不住直吞口水。
“夕阳无限好,人生望晚晴。”教授触景生情,无限感慨。
“好!好个‘夕阳无限好,人生望晚晴’!教授,你不写诗,简直是资源浪费啊!”诗人夹着值班记录本,走了过来。
“过奖,过奖!惭愧,惭愧!如果早有这种心境,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了。”个中滋味,百感交集,教授摇头而苦笑。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拥有时不在意,失去后才珍惜。我们又不是神仙,没办法预测明天。总结昨天,把握好今天,就不愁没有晚晴,就不怕没有圆满!”诗人说得有些激奋。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说得好啊,老弟。你今天又给我上了一课,让我受益匪浅啊!”教授发自内心的称赞。
诗人有些脸红,推推一旁的坤师:“别光愣在这儿,你也说两句噻!”
坤师故意装傻:“你们这些大知识份子,文人骚客摆龙门阵,哪里轮得上我们这些蛋白质、二百五插嘴哦!来来来,我以烟代酒,敬二位!”
教授接过香烟,笑嗔道:“你这个家伙,是盘海(螃蟹)有肉,在肚子头。揣着明白装糊涂,揣着海鲜装吃素!”
“对对对。自称二百五,装猪吃老虎!”诗人也趁火打劫。
“二位老大,饶了我!我不开腔则已,一开枪就把自己打掰了!”坤师彻底投降。
三个人“嘻嘻哈哈”笑成了一片。
高墙之外,大苞村七队的高音喇叭,又放起了音乐。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越过电网,隐隐约约邈邈冒冒地飘了进来。
坤师正色道:“人们都说,大劳改就象爬山,刑期过半就是走下坡路。我们呢?从看守所到入监队,现在总算下了队。虽然还在上坡路,但终究也是半山坡了,山顶就在前面,希望就在前面,快了。大家一起努力哦!”
“是啊。我们就站在希望的半山坡上,今天太阳落下,明天又会升起,说不定会比今天,更红更亮。”
教授拍着两人的肩膀。三人一起望向地平线,那即将隐去的,最后一丝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