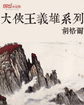张维坐着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学校,一路上,他不敢相信今天看到的是事实,可是他又无法否认。夜里,他又睡不着了。他想,他应该找找她,让她不要再这样下去了。难道是她没钱花了?不可能,她父亲不会不给自己的宝贝女儿花的钱的。她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想不通。
第二天,张维找到了杨玲,问她:“巫丽家是不是最近不行了?”“谁说的?”“我猜的,她父亲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儿,没花的钱了?”“没有啊,她爸前几天还来看过她,给她买了个大哥大呢。那玩意儿你见过吗?”“我跟你说正经的。那你知道她在酒吧里干的事吗?”“知道。”“她不是不缺钱花吗?为什么要做那些事呢?”
“刚开始是有人请她去主持节目,其他的事她一概不做,后来她好像有点收不住自己了,反正,我也不太清楚,是听别人说的。你怎么又关心起她来?”
“我也听别人说她的闲话,才随便问的。你早知道了,为什么不劝劝她?”
“她?她能听我们劝?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脾气,谁劝也没用。”
“她爸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了,那种事儿能让家里人知道吗?”
张维的心里很沉重。本来他想今天再去找找巫丽的,可是他现在不想去了。他知道巫丽是自甘堕落,便想起巫丽从前对他说的那句话:“我就去接客。”他一想起巫丽跟那些男人乱搞,他就对巫丽越发地厌恶了。他想,一定是情欲在作怪。她什么都不愁,物欲对她没什么诱惑力,但情欲对她却有诱惑力。
晚上,他又睡不着,他看见巫丽和一个一个的男人轮流做爱,说着下流的话,勾引着男人。等他睁开眼睛,什么都不见了。他又闭上眼睛,努力地想睡着。他又看见吴亚子和穆洁一起笑着向他走来,到跟前时突然变成了讥笑,口里骂着:“想和我结婚,也不看看你口袋里有没有东西。”然后他就看见两个女人转过身去,和两个男人拥抱着走了,那两个男人也留下一串嘲笑声。他不想听了,就又睁开眼。又是什么都没有了。现在他不敢睡。他坐了起来,打开灯,又拿起那张诉状看了起来,直看得他热血沸腾,怒气冲冲。
快到五点钟时,他终于疲惫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时,他醒来了。手边放着那张诉状,他读起来。这阵子读却没有了昨夜的那种感觉,便把那状子放下,洗脸,刷牙,然后他继续去图书馆写论文。可是,一坐到那里,他就看见满天下的人都在为一个字而奔忙,就是“欲”字,说得清楚一些,一是物欲,二是情欲。他越想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便回到宿舍,又拿起那张诉状看起来,发现自己的文章写得真好。他不知道把这篇文章怎么办好。说是张诉状,却不会有受理的地方;说只是篇文章吧,却明明是张诉状,里面的八大罪状写得清清楚楚。
他无心再做他事,一心想着自己的这篇文章该如何处理。想着想着,他就想,人们不是说他疯了吗,他索性再做一件疯事。他来到了附近的法院,找到了法院办公室,问里面的人,这张诉状应该交到哪里。一个中年人看了看,说:“这不是诉状,是一篇文章。”张维说:“谁说不是诉状,明明是一张诉状。”张维对那个人说他的文章不是诉状很生气。中年人看了看张维,又看了看底下的诉讼人名字,就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张维说:“北方大学。”那个人仔细地把张维看了看说:“你一个大学生,怎么连最起码的一些知识都不知道,你要告谁啊?这里面写清楚了吗?”张维说:“我告欲望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中年人说:“欲望是谁啊?”张维就说:“欲望就是欲望,是每个人都有的欲望。”中年人很生气,说:“我给你再说一遍,这不是诉状,只是篇文章而已。”
张维去找任世雄,他觉得任世雄在这方面肯定有好主意。果然,任世雄听说后,拍案叫绝,一拍张维的臂膀说:
“啊呀,他妈的,张维啊,你真是一个天才啊。你居然能弄出这样一件奇事来,真是闻所未闻,古今绝无。你给我一说,我就怦然心动。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在法院审理此案,但要让新闻界知道,把这件事报道出去,然后专门找一家报社和杂志社刊登审理内容,这样,公堂就不在法院里了,而到社会上,就真正成了一件议论社会公理道德的大案。”
张维一听,正中心怀。任世雄说:“这件案子由你来作,但最后由我处理出版事宜。”张维虽然对任世雄很有意见,认为任世雄给他的稿酬实在太低,但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就回去认真地准备。
第二天中午,任世雄来找张维,说一切事宜都办妥了,有好多家报社到时还要现场采访。下午时,两人就去找法院领导。
结果,他们都不同意。说是在胡闹,就这么完了。
张维和任世雄从法院出来,一路骂着回到了学校。任世雄说:“干脆我先把你这篇文章想办法发了,也一样有效果。”张维说:“就怕没地方发。”任世雄说:“试试吧。”试的结果也是没地方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