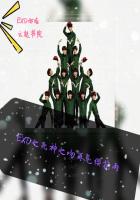秋意浓,月光如泻,宫道幽深。
“颜儿,你叫我说你什么好?生哥哥……狠是出了名了,你骗了他,害得他——”苻芸晃了晃颜儿的臂弯,捉急道,“他饶得过你?你去见他,哥哥恐怕都不会肯,更莫说……”
苦苦一笑,颜儿仰头望一眼明月,却是不语。只听得宫道后头一阵脚步声急,身边的两个女子“哦”了一声,手便被钳住,胳膊被拽着直往前拉,颜儿抬眸,不由一愕,棱角分明的侧脸不见平日的温润,却是冷峻莫名。没来由地心慌,转瞬便是不忿,颜儿死命要掰开他的手,奈何那人却钳得更紧了,脚底更似生了风,一路疾走,拖得颜儿差点踉跄跌倒。
“放手!”忿忿一喝,颜儿不住甩手,却被拉拽着一路碎跑。
充耳不闻,苻坚既不扭头,亦不回眸,倒是紧拽一把,步子迈得愈发紧了……
荷花池,菡萏凋零,映着月光,漾着波光,愈显枯寂。
苻坚总算住步,松开手,却是定定地望着黑黝黝的池水,低沉一语分明夹着怒意:“你这番置气竟是做给谁看?”
一怵,眼前之人陌生得可怖,颜儿直直地望着,星眸倒映葱绿树冠,似染了绿芒的猫眼石。一路急走,亏得自己暗藏一丝希冀,竟妄想他追来是为……破镜重圆……始料不及,忆及云龙门谯楼,心底暗涌一丝惧怕,颜儿禁不住细细退了一步,嘴上却不饶人地低喃:“置气?我不是件衣裳吗?死物还会置气不成?你——”
“若是做给孤看,趁早醒醒你的春秋大梦!”容不得半点反驳,苻坚冷冷地扭回头,明眸映着月光泛起一抹从不曾见的冷厉,逼近一步,“若非看在融弟和双儿份上,孤此番断不会来!”
当头一棒,颜儿怵得僵在原地,除了星眸里熠熠闪动的几点泪光,整个人呆住了。
冷厉褪去,唯剩冷漠,苻坚不耐地瞥了一眼,冷冷道:“厉王有多狠,你比孤清楚,若你——”
顿了顿,眼神越过娥眉黛玉,苻坚仰望一眼圆月,声冷过冰凌:“执意要去送死,孤绝不拦你!”
死?轰然……心……崩了,不敢相信,颜儿睁大了眸,眼前之人可还是他吗?温润如玉的他、情深似海的他,去了哪里?可月光雾了眼,眼帘白茫茫一片,唯见那两刃眉峰直逼心口,那两瓣薄唇张张合合……当刻,颜儿甚至想剜下自己的双眼,究竟是自己的眼盲了,还是心……盲了?怒,怒得无法复遏……颜儿周身轻搐,只想堵住那张嘴,甩手便打了过去……可手悬半空,腕子却是钻心的痛,再甩一手,又是钻心的痛,双手竟交叉着被他牢牢钳住了。
“又想打孤?你是真不怕死吗?”
淡淡一语,没了狠戾,没了怒气,甚至没了阴沉,可听在颜儿耳中,却分外刺耳,比怒吼狂哧更戮心。颜儿死命挣扎,骨头散架般颤栗,眼帘弥蒙不堪,什么都看不见了……然,腕上的铁钳分毫未松,心头的诅咒愈念愈紧……
见她歇斯底里哭作泪人,眼波漾过一丝浅淡涟漪,苻坚敛眸,唇角一抿,却是直逼一步,更是紧了紧掌心,幽幽道:“你是个聪明人,你该懂,你而今是多么愚不可及。孤说最后一次,孤对你——”
顿了顿,苻坚别眸那池幽漆秋水,似从牙缝挤出一缕沉闷之音:“无半点情意。孤不是厉王,像你……”又是一顿,明黄胸口一伏,苻坚微扬声线,快语道:“这等红颜祸水,莫说你如今是孤的弟媳,即便不是,孤也不容你玷污孤一世英名。”
“呃……”重重地一声喘息……双肩簌簌发颤,颜儿咬紧牙,头一回尝到恨意蚀骨的滋味,埋头便是狠狠一口。
“嗯……”手背猛地一疼,苻坚下意识地抽手,可,回眸一瞬,眸光凝滞,手亦僵住,牙尖的疼远不及滴落手背的炽热来得灼心。
舌尖涩涩一丝血腥,唤回一丝清明,亦唤回钻心的痛楚,颜儿雷击般松了口。自己这是疯了吗?自己而今是什么样子?痛楚未褪,耻辱来袭,若不是被他钳住,颜儿只想一头栽进荷花池里。惊觉腕上的铁钳松动了,颜儿猛一抽手,低眸瞥见白玉镯子,怒得烧心,不假犹豫,哆嗦嗦地捋下镯子,扬手便扔向了荷花池……
一道寒光划破宁静夜幕,撕开心头一道细口……
噗咚……凄清一声,闷闷地砸落心头……
二人齐齐望向秋水,相对已是无言,空气凝固了,四下寂灭了……
泪眸一颤,颜儿微勾下巴,玉靥沾着寒露,孤傲一笑,漾起一缕碎心的残忍之美:“白玉为聘?呵……”再开口,笑已褪尽:“即便陛下他日一统江河,成了千古一帝,于我……亦不过是个可鄙的负心汉而已。我嫁谁,轮不到陛下保媒,你……不配。”说罢,转身离去。
攀着石桥,双腿不支地打颤,颜儿抚着膝盖,竭力挺直了脊背,唯是丹田一涌而上的热流,顷刻腾上了嗓子眼,唇角一热……颜儿不由弓腰,滴答……滴答……月白的裙角洒落点点乌青……手揪着膝盖一紧,颜儿强撑着站直,尚未迈步,抬眸间,夜幕已唰地落了下来……
夜宴之上,当众退了苻融的婚事,王太妃暂居的玉堂殿如何还容得下颜儿?昏迷的颜儿,被送至了苻芸的寝殿。御医只道是余毒未清、气血攻心,并不大碍。翌日清晨,人确也醒了,却愈叫苻芸担忧。
苻芸抚着腮帮子,愁闷地对着苻雅撒娇:“都三天了,不言不语的,吃得也极少。这可叫我怎么向峰哥哥交代?姐姐,你给我想想法子。”
苻雅轻轻地撂下绣绷子,叹道:“心病还须心药医,你我……哪有法子?”
“哥哥真是坏透了!我都懒得理他。”苻芸挺直了身子,撅着嘴忿忿,忽的,狐疑地望了眼姐姐,道,“姐姐这回怎么……”
“怎么舍得在宫里陪哀家这么多日?她哪里是陪哀家哟。”苟太后皱着眉,幽幽地踱进了屋,拂了拂手示意两姐妹免礼,径直落了座,又冲着长女嗔道,“你啊……还是这性子,什么话都憋着,哀家不问,你难不成要赖在宫里呆到明年?”
“母后……”苻雅脸色尴尬,比起挨着母亲坐下的妹妹,拘谨得似个宫婢,细声道,“我……始平县的案子,还请母后替女儿做主。王猛……欺人太甚,郭怀安着实冤枉啊。”
“陛下亲审的案子,怎会有冤?”苟太后抬眸睨了女儿一眼,捻起绣绷子,漫然道,“治国是男人们的事。你绣绣花样子就得了,添什么乱?嫌陛下如今还不够烦吗?”
“母后,陛下以仁义闻名天下,王猛却反其道而行。我……夫家的案子是小,我是怕陛下遭佞臣蛊惑——”
“行了!”苟太后拍案,不耐地起了身,“此事到此为止。你拾掇拾掇今日便回府吧。”
望着母亲离去的背影,苻雅别过脸,拭了拭泪。
“姐姐……”苻芸悻悻,挎着苻雅的手,宽慰道,“近来宫里事多,又秋燥,母后难免……”
“行了,我知。”苻雅抚抚妹妹的手,泪眸凄清,“在母后心里,我本该是……个儿子,却不该是……”
“姐姐……”
“算了,这么多年,都惯了。”苻雅深吸一气,道,“可,你姐夫死得早,我若守不住他的家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你可知,只因王猛一句‘以礼治安定之国,用法治混乱之邦’,陛下不仅不罚他,还夸他有管仲之才。这冤屈,我如何能咽得下?罢了,陛下和母后都不理,我唯有靠自己。”
“姐姐,你……可别做傻事啊。”苻芸屏住气,着了急。
苻雅挤出一丝笑意,捏捏妹妹,道:“放心,我不会乱来。他是瓦罐,我是瓷器,不会跟他硬碰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