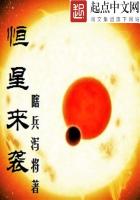房里只剩郦书雁和钱婆子两个。郦书雁看着她,笑道:“钱妈妈,你这些天过得可还好么?”
钱妈妈心态大变,再也不敢在郦书雁面前耍威风。她重重磕了个头,厚着脸皮道:“老奴这些天一直想着小姐,每天都念着经,向老天祈祷小姐平安呢。”
“你少来这一套。”郦书雁冷声道,“钱氏,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钱妈妈见郦书雁不打算原恕自己,一颗心就冷了一半。郦书雁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低声说了几句话。钱妈妈霍然睁大双眼,另外半颗心也冷了下去,瘫坐在地上。
“你……你……”她颤抖着抬起一只手,指着郦书雁,语不成句。
郦书雁淡淡笑道:“眼下,我有一件事要你去做。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钱妈妈想到自己在郦书雁手上的把柄,心如死灰。她哀叹一声:“也罢,我这一把老骨头,死了也就死了。大小姐,你是个厉害的角色。请您无论如何,放过我的家人。”
郦书雁毫不遮掩,直接说道:“这倒简单,但还是要看你的表现。”
独孤夫人的请柬上,指明让她午时赴宴。所以,郦书雁用过早膳,还余下不少时间准备。刚巧郦书雁这两个月裁了几件料子不错的衣裳,便换在了身上。
她换完衣裳,紫藤竟然看得呆了。她喃喃道:“小姐,你……前几个月……真是大不同了。”
郦书雁抬手摸了摸脸,调侃道:“变美了,还是变丑了?”
紫藤毫不犹豫道:“当然是变美了!”
事实上,她是知道自己的变化的。之前的她,最大的问题不是容貌,而是仪态。所谓居移气、养移体,她这些日子气度变化不小,外人看来,就像容貌变了一样。
一时准备停当,郦书雁坐上马车,却看见郦碧萱已经等在里头。
郦书雁柳眉微扬,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郦碧萱被她的态度气得死去活来。可她心里知道,自己今天全靠郦书雁才能混进金明池,只好赔笑道:“姐姐说哪里的话。上次去花会,便是我们两个;这次也是我们两个同去才对。”
郦书雁淡淡地看了她一眼。郦碧萱只觉得她的目光深邃无比,仿佛能一眼看进自己的内心。她心里一阵难受,转过了头。
令她大为惊奇的是,郦书雁并未为难她,而是直接上了车。紫藤跟在她身后,也并未说出什么。
郦碧萱心下一宽,掀起车帘,对车夫趾高气扬道:“走吧,还磨蹭什么?”
“妹妹。”郦书雁端坐在车厢的另一边,嘴角轻扬,笑意却不达眼底,“今天,你可要谨慎行事才是。”
独孤夫人的请柬本来就是写给她们的。郦书雁合上眼睛假寐,心里暗暗发笑。瞧郦碧萱这副样子,只怕是想错了什么。
不过,她带郦碧萱去赴会,本身也是另有所图。郦书雁微微睁眼,看了看郦碧萱又是欣喜、又是害怕的模样,又闭上了眼睛。
——毕竟,如果不让郦碧萱和豆卢徽云接触,她又怎么能捉住她们的把柄?
这一次,仍然是由几个美貌的宫女守在门口,分别带着她们往定好的地方走去。暮春的金明池比起冬天,多了几分婀娜,却也少了些特殊的意趣。
宫女引着她们到了湖畔的一片梨树之中,便自行回去了。豆卢徽云来得早些,一见她们,便换上了一副惊喜的表情。她热情地迎上来,拉住郦碧萱的手:“萱儿、郦大小姐,你们来得好早。”
“不如豆卢小姐早。”郦书雁淡淡答道。
豆卢徽云碰了个钉子,讪讪地不知说什么好。郦碧萱也不敢再说郦书雁什么,三人一时无话。
郦书雁瞟了郦碧萱一眼,识趣地坐到了离她们足有两三丈远的地方,悠然自得地看着眼前的梨花。
紫藤还是头一次来到这种场合,身边全是陌生的小姐、公子,她越想越紧张,连大气也不敢出。郦书雁看了一会梨花,回头看她一眼,轻笑道:“紫藤,今天可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你今天千万要小心些。”
紫藤知道,郦书雁很少说言过其实的话。她心下一凛,点了点头,道:“奴婢记得。”
独孤夫人邀的,果然还是上一次的那些人。郦书雁稍加观察,只觉得满眼都是熟面孔。过不多时,慕容清也来了。他远远地看了郦书雁一眼,往前走了几步,坐到了离她不远不近的位置上。
独孤夫人在请柬上说了午时,最终,她在午时二刻才姗姗来迟。不过,这一次她却不是自己来的,身边还坐了一个穿黑衣裳的青年人。
那青年的发色不是处处可见的黑色,而是稍稍泛红的檀色,在日光之下像是镀了金,格外引人注目。他神情冷峻,一坐下,便自顾自地倒了一杯酒。因此虽然生得一副好皮相,却也没人搭讪。
看见独孤夫人到了,宾客们便都慢慢安静下来。独孤夫人笑道:“上回我俗务缠身,走得太早,累得各位没能好好欣赏这金明池的美景,实在是罪过。”
她这样说,别人哪敢答应,纷纷起身辞谢。独孤夫人待他们安静下来,又指着身边的青年道:“这是舍弟,是单名一个信字。”
这人竟是独孤信?
郦书雁心中一动。前世她在虽然身在深闺,却也听说过独孤信的名头。
这位独孤信是个传奇一般的人物。他虽然身在江湖,却有着旁人远远不及的令名。世人甚至说出了一句话,“独孤不出,如天下何”。
郦书雁经历的事多了,也就知道这种美名大多是造势而已。譬如魏晋时的谢安,也是一样。即使惊才绝艳如谢安,出山之后,也有人讥讽他“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她想起这个刻薄的典故,不由会心一笑,心道:独孤信做的最正确的抉择,莫过于终身不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