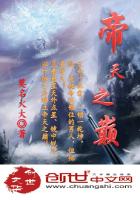夜深了,天很黑。
窗柩外风雨交加,雷声大作。
“……嗯,下个星期三就走。”权宴背对着书房的门,站在长桌前,跟话筒里的人确认:“只有一个人……”
“咚咚咚”
听到敲门声,权宴微微侧头看向声源处,看到来人,匆忙挂掉电话,“我之后再联系你。”
贺至脸色凝重的走过来,“家那边出事了。”
权宴抚着肚子扶着腰站定,“怎么了?”
贺至走到她跟前,将她打横抱起放在一旁的太师椅上。
他蹲在她的脚边,低着头,紧皱着好看的眉峰,帮她按摩浮肿的小腿肚。
“不太好。”贺至抿抿唇,“听说我们隔壁楼的老太太之前跳楼了。”
权宴心下一沉,鸡皮疙瘩蔓延了一身。“你是说——”其实小区里的恶臭真的是动物尸体腐烂的味道,而且不仅仅是单纯的“动物”。
“什么时候的事情?!”
“一两个月了。老太太的儿子公派出国,听说回来之后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习性……”权宴觉得贺至的表情有些古怪,她隐隐觉得自己好像知道了什么,但是这种潜在记忆藏得太深了,她想不起来。
权宴迫切的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
“她儿子怎么了?”
“……爱上了一个美国男人。老太太接受不了,把儿子赶出家门之后,一时想不开跳楼自杀了。”
贺至的话就像一盆混着冰块的凉水,哗啦哗啦一股脑儿全都倒在了权宴的脑门上。
“媳妇儿,你怎么了?”
漆黑一片的天空下,落在大地之上的雨滴各自汇聚成一条条蜿蜒曲折的小水流,汇入江河,奔腾进大海。
书房里,权宴空洞的眼神里找不到贺至所在的焦点,她脑袋里的画面一闪而过,快得让她抓不住任何过往片段可以参考。
贺至着急忙慌地叫权宴回神,他很怕,刚刚的她,好像就在那一刻就要离他远去一样,他甚至觉得自己就要失去她!
这怎么可以!
不可以!
“权宴,你怎么了?!回神啊,跟我说句话!”
权宴轻轻抓住呱噪的贺校长的大手,木然的回他:“打电话叫防疫局去收尸。”天气越来越炎热,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消毒,恐怕会在阳城蔓延起传染病和瘟疫。
“叫了,你不用担心。防疫局的人去得很快,你义父他们对这件事情很重视。”贺至并不担心旁的事,他的眼里现在只有权宴。就算天塌下来,也甭想把他对权宴的关注转移。
“你刚才怎么了,发什么呆?”
“……没事。”
贺至明显不信。
“我还以为你这个医学博士跟普通人不一样,就算听到这些事情也不会有多大反应。”
权宴狠狠的白了他一眼,“中脑水管破裂了?老娘肚子里还有你闺女呢!就算我不怕,你也不怕你闺女出点儿什么闪失?!”
贺至赶紧“呸呸呸”打嘴,对着权宴的肚子点头哈腰的认错,“我错了我的错,以后我肯定注意!哎哟我的宝贝亲闺女诶,你爹我错了哈,以后再也不吓唬你了,爸爸保证!”
隔天,天气仍旧没有放晴,权宴最近在家里休产假,有医户因为中医堂在建的事情冒雨来找权宴商议。
“老徐,你坐那。”小王氏倒了一碗热姜茶给他。
“那就谢谢东家了。”老徐没客气,还滴着雨水的华发一缕缕的紧贴在脑袋上,再不喝一碗姜茶驱寒,恐怕要得风寒感冒。
权宴裹着外氅坐在书房的太师椅,济生堂的老徐被让到客座。
“老徐,这么着急来大宅,工地那边出什么事情了?”
“东家,眼见着这雨势越来越大了,也不知道要下到几时。工人们怕雨大,看不清楚,出差错,正闹罢工呢。我想着这中医堂急于一时也做不成,不如就给大家伙儿放工几天歇歇吧?”
权宴右手习惯性的敲击实木的桌面,眼皮子垂着遮住了眼睛,让人猜不透她在想什么。
老徐坐立不安的勉强喝完了一碗姜茶,这才听到她发话:“工程建到什么程度了?”
“梁椽都立完了,现在正往上铺干稻草和瓦片。”老徐连忙接上话,生怕怠慢了东家。
“两个月能建完全部工程?”
老徐擦了一把冷汗,“阳城也就最近这个时节降雨频繁,过了这个节气,大家手脚麻利一些,”他说:“一定能赶上小东家出生!”
权宴不在意的笑了笑,原来他们都以为她赶工期是为了迎接她女儿的出生?
没多解释,权宴放了话:“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
“诶,好嘞东家!”
送走老徐,权辛也蹦哒着跟权宴进书房。
她坐在太师椅上看院办文件,小胖子依偎在她身边,摸着她高高隆起的肚子,小声的跟还没出生的妹妹讲话。
也不知道权辛是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么个习惯,每天跟妹妹聊天几乎已经成了他的日常功课。王子豪跟贺家兄弟找他出去玩也要等他跟妹妹讲完话才行。
“姑姑。”权辛小心的摸着小baby胎动的点,像是被这个小生命奇怪的举动吸引住。
“嗯?”
“妹妹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抱抱她啊?”
权宴想了一下,“大概要等你长大。”
等你长大,回来找到她。
权辛虽然有点小失落,但这并不妨碍他期待着。“你以前也说过我要长大后才能去看妈咪,可是我现在也快要见到我妈咪了。还有还有啊,等我回来我会给妹妹带世界上最好吃的草莓夹心巧克力的……”
权宴慈爱的摸摸他的脑袋,耐心的听他讲述他对未来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