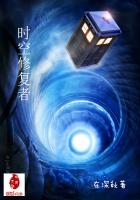“王后,世子过来辞行了!”
琉璃停了手中正写字的笔,说道:“请世子进来!”
聂阿姆轻叹了口气说道:“世子年纪尚幼,只身前往大魏,实在有些难为了他!”
然而心里却是想道,沮渠牧健为了让大魏皇帝安心,亲妹嫁了过去,世子也都舍了出去,然而却依旧存着异心,暗里派人去了宋地面见宋帝。北凉一朝,为兴国旺邦,真是舍得出来。
心里叹着,沮渠封坛随着云裳进来,与琉璃见礼:“我今日就要随大魏叔孙将军前往大魏,特来与母后辞别。一别不知时日,望母后保重!”
琉璃上前将沮渠封坛扶了起来,说道:“大魏是我自幼生长之地,你此番前去,不必担心。你平日读书勤勉,若有学问上的疑问,只管前去向我的父亲询问。我已修书一封,你且带去,以你的资质和勤勉,但凡潜心学习,必有所成。”
说完,从桌上拿起自己刚写完的信,吹了两吹,说道:“刚刚写完,笔墨尚湿。”粗略折了两折,从桌上又拿起信封,说道,“知道你要看时辰启程,来不及等墨干掉。你且先分开收着,等墨干后再装信封。”
沮渠封坛将信封装到怀里,信纸拿在手里,对琉璃又施礼:“我素闻外祖盛名,今有母后的书信,外祖必会对我格外宽待。多谢母后为我考虑周全。母后的叮嘱,我必放在心间,时时自醒,不教心有旁骛。”
琉璃便笑着说道:“你能听到心里去,我甚是欣慰。叔孙将军曾在我阿爹门下修习,一路必会照顾你。他为人纯正,你可与他多多相交。”
沮渠封坛恭敬答道:“谢母后提点。”
擎着琉璃写的信,告辞了出宫。
聂阿姆等沮渠封坛走了,说道:“世子面上看着,对王后没有半点嫌隙,一口一个母后,一口一个外祖。小小年纪,竟然如此屈伸自如,叫人看不出真假。”
琉璃心里想道,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她又何曾看到沮渠牧健的真假?她听聂阿姆的话,努力让自己不去猜疑沮渠牧健的种种,然而那个人面上做得越是随和亲切,她越是心里没有底。纵使因为她大魏公主的身份,沮渠牧健面上对她客气有加,他总还是一个正常人,总该有他的喜怒哀乐吧?一个男人,你永远只看到他对你的温柔,从来不在你面前流露一丝的恼怒与难过,忧愁与为难,正常么?
琉璃正想着,云裳进来禀道:“王后,大王子夫人来了!”
自从丝路被王太后发落到酒泉,宫中上上下下明显对琉璃敬畏了许多。大王子夫人也不觉收敛了起来,不敢太过肆意了。
琉璃看了看聂阿姆,笑了笑,想到这位大王子夫人真是会捡时候。专捡着能落进下石的时候来,还真是没有长够记性。
“请大王子夫人进来!”
说完了,回身往书案前一坐,对聂阿姆笑道:“阿姆也坐。”
聂阿姆说道:“宫里自有宫里的规矩,王后这是故意让人嚼舌么?”
琉璃便笑道:“大王子夫人上门,不过是妯娌之间串门聊天,阿姆还要像客人一般正经伺候不成?我看阿姆昨晚还在灯下为我缝衣服。趁着天光大亮,阿姆正该这个时候做活,以后晚上莫再要累眼睛了。”
聂阿姆看着琉璃动了调皮,笑了笑,说道:“依你!”
拿了针线,往琉璃对面一坐就着昨晚的针线缝起来。
大王子夫人一进来,一个写字,一个做针线,一刹那几乎怀疑自己错了眼睛。
聂阿姆看到大王子夫人进来,拿着针线,站起身来,先行了一礼:“夫人且坐。我们王后自来北凉,琐事繁忙,许久不曾写字,趁着今日得闲,赶紧捡起来,免得时间长了手生。”
云裳过来,给大王子夫人置了坐垫。大王子夫人上一次跪了半天,腿脚都麻了,再不肯跪那个垫子,一扭身,坐了书案下面的一个胡凳。
说道:“王后倒是有闲的心思。我原想着,今日是大魏叔孙大人启程回朝的日子,王后想来多有不舍,唯恐王后心里难过,因此过来陪着王后说说话。”
琉璃这时抬起头来,笑了笑,说道:“我不舍叔孙将军是真。然而倒也没有夫人说的那样难过。我既嫁了凉王,这王宫便是我的家。我安好地坐在自己的家里,好吃好喝,再生难过,哪来的道理?况且叔孙将军为送我过来,离国去家已久,终于能得以回去,我为他高兴还来不及!”
抿嘴笑了笑,说道,“不过仍然谢夫人好意。如此贴心地过来陪我说话。我自来王宫,母后对我甚为关照,不让我受一点委屈。如今又有夫人如此体贴,以后在这宫里,我只会过得越来越开心。”
大王子夫人气得心中发狠,脸上假笑了笑,说道:“你能想得如此开,总是好事。在这宫里,只有心大些,万事少计较些,才能过得舒心。说起来,你比我命好,一嫁过来,就是王后,且四下安定。想当初,父王初为河西王,北凉四面皆是强敌,伤了不知多少人。我的夫君,便是迎战柔然的时候被杀的。眼下北凉能好好地不起战争还好,否则……”
叹了口气,低声说道,“王后不知有没有听说,凉王派人暗里去了宋地面见宋帝,求好求和。凉王此举,实在有些不智,我真是担心呢,王后真该劝劝他……”
琉璃见大王子夫人如此大胆,竟然将沮渠牧健暗里派人去宋地的事情说给她听。沮渠牧健本来便是瞒着她做的这件事,她若出面去劝,沮渠牧健会怎么想她?她是大魏和亲来的公主,这个时候,远离政事避开嫌疑才是正理,这位大王子夫人真当她是傻子吗?
淡淡笑了笑,说道:“夫人说的事情,我倒并未听说。不知道夫人是从哪里听的消息。且我想着,凉王费尽心力,只为北凉安定,不再有战乱。必不会不经思虑,冒然做出决定。”
“所以你这是不信我了?凉王派去宋地的事情虽是暗里进行,却也并不是做得天衣无缝……”
琉璃不等大王子夫人说完,截道:“夫人如何知道,我并不想问。我不是不信夫人,夫人既然听说的途径,想必也该明白,凉王一心为北凉安定,决不会做置北凉于内乱外斗的境地。真若有派人去宋地的事情,也必是有所考量。我虽于国事朝事并不通,但我相信凉王不是意气用事之人,否则父王焉会将北凉交到凉王手里?”
大王子夫人冲口说道:“你哪里知道,父王更属意的世子人选本来是四弟……”话风出口,忽然便收。急急转了口,说道,“凉王有没有考量我不知道,但我听说宋地对我们北凉向来没有存着好心。北凉和大魏,本来已互相和亲公主,结了盟友,何必再招惹宋地?凉王这一举措,很是让汉平王生气,最近为此事,和凉王闹得十分僵。咱们北凉的大半兵权在汉平王手里,凉王实在太意气用事了。”
琉璃心里吃了一惊,斗然想到上一次汉平王妃在自己面前的嚣张。汉平王不会就着这个缘由,结党拉派,对沮渠牧健不利吧?汉平王妃能在她面前,不将她这个北凉王后放在眼里,那汉平王反沮渠牧健的意图是不是已经十分明显了?
“哎哟!”
做着针线的聂阿姆此时忽然痛呼一声。
琉璃骤然回神,看过去。只见聂阿姆捏着手指,手指上已有血珠冒出来。急忙凑过去,拿了桌上的手绢便捂了过去。
聂阿姆一边接了手绢按着,一边自责说道:“上了年纪,眼神到底是不济了。不过是走了针扎了一下手指,倒惊了王后。”
琉璃说道:“阿姆以后万不要晚上在灯下做针线了。叫我说,这针线上的活,阿姆只管丢给青萍和红笺。她两个针线都是不错的。”
聂阿姆将手指往嘴里含了,吸了吸,说道:“王后从前的衣服都是我缝的。原是做习惯了的,一时放不下。到了这岁数,这眼神刺绣是不成了,由着青萍和红笺做去,贴身的衣物,总还是我来做的好。王后从小身子就娇气,贴身的一衣物不能有半点不舒适的地方。这宫里,还有哪个比我更了解王后的?”
这两人说着,倒把大王子夫人给晾到了一边。
大王子耳朵里听着,心里却泛起了酸来。她自从夫君被杀后,再也不是什么世子夫人,前凉王和王太后虽然因着过世的大王子,处处容让着她,然而说到真心相待,是远远没有的。且她身边也并没有聂阿姆对琉璃这样,贴心又宠溺的人待她,不过是一些对她面上敬畏,心里不以为然的宫女。
心里一时酸起来,便待不下去了,起身说道:“我的话王后且想想。北凉若真因凉王一时行差起了乱子,我便是前车之鉴!”
说完了,便起身走了。
聂阿姆对琉璃说道:“这大王子夫人,也太大胆了些。她说这话,不是在咒凉王么?只是王后别把她的话往心里去,如今王后送封家书都要不能装信封里让人带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琉璃轻声说道:“不管她什么心思,我们只别理她便是了。阿姆说的对,这个时候,我们更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过我们自家的日子才是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