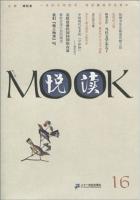苦难是一张微笑的脸
包利民
他七岁那年,卧病在床三年的母亲便去世了。父亲每日拼死拼活地去山上扛石头,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而他的弟弟刚四岁,天天哭着要妈妈,他便带着弟弟去山上玩儿,让弟弟于游戏中忘记妈妈。回到家里,他还要做饭,等晚上父亲回来,用温水给他洗被石头磨烂的肩膀。
十二岁的时候,他毅然地放弃了读书,和父亲一起去山上扛石头,他小小的身躯在石头的重压下艰难地移动着,可他从不喊累,为了这个家,为了弟弟。弟弟此时已上小学了,成绩是乡里最好的,每天放学,他像哥哥当年那样把饭做好。
十七岁的时候,由于他和父亲的辛苦劳作,家里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弟弟也去乡里读初中了。可是还没等他喘口气笑一笑,一场灾难便又降临了。父亲在扛石头下山时一脚踩空摔了下来,而那块上百斤的石头砸在了他的身上,还没送到医院便闭上了眼睛。刚刚露出了一点阳光的天空瞬间又是阴云密布,弟弟要辍学,他说什么也不让,对弟弟说:“你好好读书吧,要不咱世世代代都要扛石头!”弟弟含泪回了学校。
十九岁的时候,他被石头砸废了一只脚,从此再不能扛石头了。他便到了乡里,推着一个小板车捡破烂收破烂,靠这挣来的钱供弟弟上学。弟弟不负众望,那年秋天考上了县一中。他便随弟弟搬到了县城,由于腿脚不利索,加上城里收破烂的人多,一开始他根本挣不了几个钱,连房租都挣不回来。想出去找份工作,由于残疾根本没有人用他。后来他看见修鞋掌鞋的收入不错,便买了一套工具自己摸索着干起来。由于努力,他的技术越来越好,加上他身有残疾,人们也同情他,都到他的鞋摊上修鞋。而他也朴实,有时小来小去的活儿便不要钱了。所以生意很好,除去房租和日常花销,供弟弟上学也有结余。
二十四岁那年,弟弟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高兴得没有出鞋摊,破例和弟弟喝了酒,笑出了眼泪。他觉得生活终于露出了笑脸,自己的所有努力都得到了回报。可是就在去学校报到的前一天,弟弟出了车祸,从此只能生活在轮椅上了。
他一开始万念俱灰,觉得生活对自己太残酷、太不公平了。可后来一见弟弟颓废的样子,他便重又鼓起了勇气,他对弟弟说:“别怕弟弟,我推你去上学!”于是兄弟二人又搬进了省城,他每天推着弟弟去学校,然后就在校门口摆修鞋摊。每隔两个小时去校内推弟弟上一次厕所,晚上再把弟弟推回在校外租住的小屋里。
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刚听说时我还不相信,认为就算生活再残酷,也不会把所有的苦难加在一个人身上。直到有一天我在省城师大门前见到了这兄弟俩,当时他正一拐一拐地一只手推着弟弟的轮椅,一手拉着身后的修鞋小车往回走。而在他们的脸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愁苦神情,有的只是灿烂的笑容。
我问他:“经历这么多的事,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他说:“我原来也犯愁过,可是过后一想,就算我愁死也没有用,弟弟那时还小,所以我只能去面对这些了!”说完他笑了,那张穿越漫漫风尘的笑脸使我的心变得暖暖的。
人生总会有苦难,可又有谁能在苦难中露出笑脸?当我们穿越苦难回过头来看走过的路,才会觉得只有根植于挫折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才会品咂出一种用痛苦酿就的幸福。那从岁月深处漾出来的微笑,会扫尽你心底的阴霾,会像一盏明灯,照亮你前方所有遥远的路途。用一张微笑的脸去面对苦难,那么所有的苦难终会在岁月中绽放出最美的人生!
痛苦可以使你远离地狱
去绝踪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老约翰夫妇刚刚睡下不久,便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老约翰披衣来到院子里,敲门声还在持续,他打开院门,门外站着一个年轻人。
老约翰吓了一跳,面前的这个年轻人脸色苍白,极长的头发零乱地披散在脑后,身体颤抖着,眼中射出阴冷的光。老约翰强自镇定了一下,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同时他用眼睛的余光寻找着可以防身的东西。那年轻人嘴唇哆嗦着说:“你可以给我一些盐吗?”老约翰颇感意外,以为自己听错了,问:“什么?”年轻人说:“盐,我需要一些盐!”这时,老约翰的夫人也走了出来,看见这个年轻人也是吃了一惊,老约翰对她说:“亲爱的,这个年轻人需要一些盐,你去给他拿来!”
当那年轻人拿了盐蹒跚着远去后,老约翰夫妇回到房中却是睡意全无,于是讨论起这个年轻人来。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他们还没有遇见过深夜来讨盐的,而且那个年轻人看起来又是如此让人恐惧。他为什么只要一些盐呢?两人猜测了半天也没有个结果,最后老约翰笑着说:“也许他正在家里烤肉,碰巧没有盐了!”
大约半年后一天下午,老约翰夫妇正在院子里侍弄花草,这时,从门外径直走进一个人来。约翰夫人抬头一看,立刻认出了正是去年来讨盐的那个年轻人,不过此时他比过去穿得更糟糕,目光依旧阴冷。老约翰立刻起身打招呼:“你好孩子,欢迎再次光临我家!”那人愣了一下,问:“我来过这里吗?”老约翰微笑着说:“当然,去年你在一个夜里来要些盐!”年轻人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老约翰说:“我的孩子,我看你现在的样子好像是有些麻烦,来,坐下来吧!”约翰夫人很快地端来牛奶和面包。
年轻人狼吞虎咽地吃喝完毕,说:“我叫凯瑟。无业,无家,得不到政府的救助,靠乞讨为生!”老约翰问:“为什么不去找一份工作呢?”凯瑟垂下头,说:“知道去年我为什么来你家要盐吗?”老约翰夫妇摇摇头,凯瑟挽起了衣袖,老约翰夫妇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他的双臂上,纵横交错地布满了伤疤!凯瑟缓缓地说:“因为那时我已经吸毒两年了。我是个孤儿,在贫民窟中长大,结识了一些不良青年,由此染上了毒瘾。后来由于没钱买毒品,便自己想办法戒掉。毒瘾发作时生不如死,我就用刀在胳膊上割个伤口,在疼痛中我可以好受些。后来,用刀割已经不能减轻毒瘾发作时的难受,于是我便往伤口上撒盐。可是,我连家都没有,到哪儿去弄盐呢?所以只好向别人讨要!”
老约翰想了想,问:“你现在的毒瘾戒掉了吗?”凯瑟点点头说:“已经彻底戒掉了,就算把毒品摆在眼前,我也不会有欲望了!”老约翰说:“那很好呀!你该感到快乐才对!”凯瑟黯然地说:“哪里有快乐?人们都知道我曾是一个瘾君子,没有人愿意雇用我,再加上那些白眼冷遇,反而觉得更痛苦了!”
约翰夫人给凯瑟递过来一条湿毛巾,擦过脸后,他的脸上透出血色来。老约翰说:“孩子,痛苦不一定就是件坏事。你看,你用刀子割伤自己的痛苦,使你远离了毒品的深渊。同样,精神上的痛苦也能使你远离地狱,只要你不在痛苦中麻木,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堂!”凯瑟闻言垂头良久,老约翰拍了拍他的肩说:“我儿子曾是一名警官,在办案中殉职。我们夫妇俩也曾痛苦过,可是这痛苦却使我们骄傲,从而更要好好地活着珍惜这骄傲。孩子,我有一些朋友,或许他们愿意雇用你!”凯瑟离开的时候已是满眼的泪水,出门后他把怀中的一把利刃远远地抛了出去,他来这个院子,原本是打算抢劫的。几年后,通过努力,凯瑟已经是本地一家大公司的高级职员了。他常常来到这个院子,和老约翰夫妇共度美好的时光,他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他们,因为是他们使他有了新的生命。他曾对老约翰夫妇说:“是你们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堂,我永远爱你们!”
求乞者
鲁迅
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
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叠在墙缺口,墙里面没有什么。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四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
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灰土,灰土……
……
灰土……
好的故事
鲁迅
灯火渐渐地缩小了,在预告石油的已经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熏得灯罩很昏暗。鞭爆的繁响在四近,烟草的烟雾在身边:是昏沉的夜。
我闭了眼睛,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学记》的手搁在膝髁上。
我在朦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
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织成一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
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罢。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如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剌奔迸的红锦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在一瞬间,他们又将退缩了。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伸长,就要织进塔,村女,狗,茅屋,云里去。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见,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视他们……
我正要凝视他们时,骤然一惊,睁开眼,云锦也已皱蹙,凌乱,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无意识地赶忙捏住几乎坠地的《初学记》,眼前还剩着几点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还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抛了书,欠身伸手去取笔,——何尝有一丝碎影,只见昏暗的灯光,我不在小船里了。
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
中国的人命
陶行知
我在太平洋会议的许多废话中听到了一句警语。劳耳说:“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垃圾堆里的破布烂棉花有老太婆们去追求,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没有人过问。花十来个铜板坐上人力车要人家拚命跑,跑得吐血倒地,望也怕望,便换了一部车儿走了。太太生孩子,得雇一个奶妈。自己的孩子白而胖,奶妈的孩子瘦且死。童养媳偷了一块糖吃要被婆婆逼得上吊。做徒弟好比是做奴隶,连夜壶也要给师傅倒,倒得不干净,一烟袋打得脑袋开花。煤矿里是五个人当中要残废一个。日本人来了,一杀是几百。大水一冲是几万。一年之中死的人要装满二十多个南京城。(说得正确些,是每年死的人数等于首都人口之二十多倍。)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每个字出世是有三个人进棺材。
“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
您却不可作片面的观察。一个孩子出天花,他的妈妈抱他在怀里七天七夜,毕竟因为卓绝的坚忍与慈爱她是救了他的小命。在这无废物而有废命的社会里,这伟大的母爱是同时存在着。如果有一线的希望,她是愿意为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奋斗,甚而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愿的。
这伟大的慈爱与冷酷的无情如何可以并立共存?这矛盾的社会有什么解释?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
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朱自清
生命本来不应该有价格的;而竟有了价格!人贩子,老鸨,以至近来的绑票土匪,都就他们的所有物,标上参差的价格,出卖于人;我想将来许还有公开的人市场呢!在种种“人货”里,价格最高的,自然是土匪们的票了,少则成千,多则成万;大约是有历史以来,“人货”的最高的行情了。其次是老鸨们所有的妓女,由数百元到数千元,是常常听到的。最贱的要算是人贩子的货色!他们所有的,只是些男女小孩,只是些“生货”,所以便卖不起价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