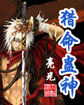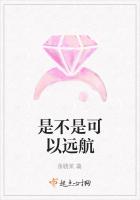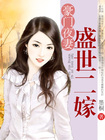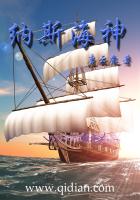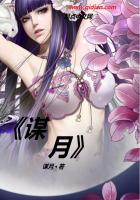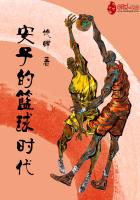三峡触动神经
一位从北京来的资深记者,伫立在重庆移民局的门口,凝望着白底黑字的“重庆市移民局”匾牌。几分钟后,他才缓缓挪动脚步上楼,开始他极不平常的采访。
移民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郎诚接待了记者。
郎诚在三峡库区移民大县的奉节县当过县委副书记,还在万县市政策研究室供过职。他40多岁,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年龄。
******三峡建设委员会这几天正组织一期水位移民验收,他忙得焦头烂额,晕头转向,累得身心交疲,从他略带紫色的面容看,不是缺血就是缺氧,说话也有气无力。
这位记者说:“以往,我到移民机构采访,看到‘移民’这两个字的英语单词,心里就产生一种躁动、渴望、兴奋,但在‘重庆市移民局’这块匾牌面前,一点没有兴奋的感觉;只要一想起三峡百万移民,心情就沉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一会儿,电话铃响了起来,《中国青年报》记者小徐、小吕到移民局采访,怕采访扑空,先打个电话。
北京来的资深记者刚走,小徐和小吕又进入了办公室。两位记者被郎诚和他所介绍的移民情况吸引住了,也为移民工作者全身心投入三峡百万移民做出的牺牲所感动。二人执意要请客,要慰劳慰劳三峡移民干部,于是,晚餐就成了这般景象:北京来的记者到重庆采访,反而请重庆人吃“重庆火锅”,弄得郎诚一边吃一边表示歉意。
对中外新闻媒体来说,三峡百万移民是新闻的焦点问题,百万移民充满悲欢离合的大搬迁过程,他们的过去、现在、将来的生存状态,将会有层出不穷的新闻出现。有人贪污移民资金是新闻,移民工程质量问题是新闻,三峡库区发生滑坡事件是新闻,甚至一个移民伤风打喷嚏也可能成为新闻,都值得舆论界去聚焦、去跟踪、去关注和披露。
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的人认为,三峡炒这么热干吗?不就是(******)修一座水库么?这些年来,全国有很多地方受洪涝洗劫,遭水灾的那些人,修房子、搬房子都很积极。水涨起来,人搬走就行了,以前,咱们国家也修过大水库,也有过移民,三峡移民咋就这么难呢?
重庆市移民局发展扶持处王满发牢骚说,一次,他护送移民外迁,车在途中“抛锚”,与过路车发生了一点小擦挂。车也没伤,人也没伤,没想到才一会儿,七八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像从地缝里冒出来似的,围着车子又是拍照,又是采访,本来芝麻大点屁事,非要弄出“移民车队发生车祸”的天大新闻来。
1999年7月16日,一家报社头版头条刊出了一篇《三峡移民贩子见利忘义,库区百名移民叫苦不迭》的报道。相隔一两日,另几家报纸也用大黑标题、醒目篇幅刊登了内容相同的文章。几家媒体的同时聚焦,在三峡库区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上众多目光盯住了事情发端地——湖南省当阳市和重庆市巫山县。
这篇文章(后来还有系列报道),主要是描述巫山县29户移民自愿迁到湖北当阳的一系列不幸遭遇……
主动外迁的移民利益受到了伤害,这还了得?
巫山县的“县太爷”王超,以前担任过《万县日报》的总编辑。以前搞舆论监督是监督别人,现在作为地方官被别人监督,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才明白。写此报道的人可能疏忽了一点,一不小心遇见一位资深同行。王超一看此报道,第一感觉就发现“有诈”,当即指令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调查。
结论是:移民贩子不是贩子,移民资金没有流失,移民身份合理合法,这批自主外迁的移民安居乐业。
可这种“想当然……或许有……”的报道,却如同在三峡的激流中投下一块巨石,激起了一阵阵涟漪,久久难以平静。
三峡移民牵涉面广,阶段性的政策性很强,如果在宣传口径、宣传分寸上把握欠妥,就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种豆不一定能收获豆,种瓜不一定收获瓜,这也是唯物主义的精髓。
库区一个县在抓先进性教育中,部分干部发挥先进作用,主动把街头位置较好的、容易聚集人气的门面,让给移民经营。当地日报把这个“让移民得实惠”的例子刊登了出来。这本是一篇不大起眼的消息,但却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街上好地段的门面毕竟不多,并不能照顾到每一个移民,没有得到好门面的移民就气吁吁地找上门来,理直气壮地问:“同样是移民,为什么他们得到实惠,我没有得到实惠?”
不少人要求政府“说个聊斋”(意即说清楚)出来,不然就不依不饶……
湖北省一位移民局长曾介绍过他的“深刻体会”。他说,他看到一篇写三峡“库区行”的文章,觉得写得不错,就邀请那位写“库区行”的资深记者到另一大型水库去写一写移民的生活现状。
有新闻写,这位记者欣然前往。
走水库、访农家、看田畴,记者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采访,写了水库移民如何科学种水稻,如何网箱养鱼,如何勤劳致富和如何使自己的小日子日渐红火的创业过程……
这篇以人物、以事实为依据的长篇通讯发表后,赢得了各方好评。
好的通讯,就像“苹果饱含着果汁”。
不想才过了几天,一大群外迁他乡的移民拿着报纸找到了移民部门,他们要求再搬迁回水库来住。
“不是说人多地少么?”
“不是说不外迁就没法过日子么?”
“他们不外迁,是祖坟埋得好些吗?”
“让我们搬走,他们在库区搞发展、发财,是哪儿的天理?”
“叫我们迁走,移民局完全是‘半夜吃桃子专拣的捏’!”
移民们又嚷又吵,不依不饶,横说竖说要求搬回水库。
移民干部们傻了眼,没想到一篇报道竟弄出这么多事来。局长啼笑皆非,一脸无可奈何。他苦笑着说:“移民区的宣传报道,看来是豆腐落在灰里面,吹也吹不得,拍也拍不得啊!”
这位局长的感触是颇有代表性的,三峡库区几乎每一个区、县政府都吃过宣传上的苦头。
一家报纸在外迁移民的补助费中写上了5000元,这本是国家政策给外迁移民的补助,问题在于这家报纸刊发的是一条过时新闻,记者写的是一年前的消息,又加之写得含糊其辞。这下麻烦就惹大了,外迁的移民以为政府又给外迁移民增加了5000元。迁到外省的部分移民拿着报纸回到家乡讨说法:是不是当地政府扣了5000元?是不是人走了这钱就不发了?
好说歹说,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2001年1月7日下午,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到万州区周家坝慰问演出,这次组织到移民区演出可以说是大腕云集,阵容空前强大,倪萍、王刚、李谷一、郁钧剑等等悉数到场。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刘伟在合说的相声《三峡说三》中一不小心“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国家对每个移民人均投资3万元。”移民认为国家对每个移民的安置费补偿金就有3万元,这一下在移民区炸开了锅。
真是无巧不成书,云阳县的移民恰恰又在年初回家领到了生产安置费的“价差部分”,移民就以为每人还有1万多元的安置费要陆续发放下来。移民补偿资金的价差是以1993年5月的价格计算的,国家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每一年的价格都不一样。过了八九年后,1万元的补偿金就变成了1.5万元左右。
不少移民看了演出很是兴奋,但随之而来的是有些气恼。
此时节正是动员外迁移民的关键时期,“克扣”移民款,良心何在?于心何忍?移民表示不迁了,纷纷找当地政府说理:
“你们以为瞒得过吗?你们不说实话,李金斗就说了‘实话’,移民人人都有3万元,怎么发到我手里只有一万多元?”
“移民资金总共400亿元,100多万移民,从大数上看也是平均每人3万元啊!”
“是不是被当地政府贪污了?”
重庆移民局****处长李善联很善于积累群众语言,也非常喜欢刘伟、李金斗说的相声。当时他在现场看了演出,一听到“3万元”这个词心里就一阵发紧。他听说这台节目正月初五要向全国转播,就和政策法规处的郎诚处长商量,立即给央视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这台节目后来转播时删去了“3万元”这一句。
这场“李金斗风波”闹了些日子,移民们也都些是通情达理之人,听政府人员作了些解释,也就慢慢平静了下来。
万州一位移民很是幽默地说:“李金斗是说相声的,他说了不算数,说对了也不算数,说错了也不算数!”
新闻理论中有一句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其实,在记者的眼中,不管是“狗咬人”,还是“人咬狗”,都可以变成新闻。国内的不少记者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面前,不得不采取“迂回”的方式进行采访报道。而个别西方记者到库区采访的视角完全不同,他们能把一些零碎的、残缺不全的素材写得很生动,也很逼真,从单纯的新闻业务看,也足以叫人叹为观止了。
在库区多年新闻大战中,当然也不乏“想当然”和捕风捉影者。大江截流的前夕,国内外记者蜂拥而至。几个西方记者来到重庆采访,外事办公室和市移民局接待了他们。
一位记者问:“听说三峡有10万人住帐篷,是真的吗?”
市移民局的一位官员回答说:“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大江还没有截流,水还没淹起来,移民们全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先生听说有人住帐篷,我肯定地回答你:是有,不过,那是到三峡的旅游者,是一批自愿住帐篷的、自找‘罪’受的旅游者。”
一名记者问:“据说重庆库区1997年的外迁移民已有几千人上了路,三峡有很多离乡背井的民工出走,请问这是否已成为事实?”
市移民局的这位官员回答说:“库区不是几千人的问题,而是有几十万、上百万人外出打工。家住三峡库区,外出务工致富,这是移民自己的事,我们无法也无权干涉。不过,有些事请记者先生心细一点,我们鼓励、提倡外迁,很多省、区也欢迎移民去安家落户,但不要把外迁的移民和外出务工者给弄混淆了。”
泰国水利、水电代表团从武汉溯江而上,参观了三峡大坝和移民区,到了重庆之后,市政府在人民宾馆宴请。
副市长向客人介绍了三峡移民的情况,并鼓励泰国朋友到移民区投资,享受优惠政策。
席间,一个脸色黑黝黝的泰国人突然发问说:“我们修水库,移民不愿搬迁,我们只好叫人搬石头去砸房子,以撵走移民。你们三峡工程这么大,那么多的移民,怎么办?总不可能也搬石头去砸吧?”
陪同的移民干部回答说:“三峡地处巫山大山脉,有的是石头,但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搬石头去砸我们的移民。用一句中国的俗话说,搬起石头只能砸自己的脚。”
泰国朋友笑了笑坦诚地说:“看来,我们修水库搬石头去砸移民,等于是砸了自己的脚。”
席间众皆大笑起来。
女记者“花容失色”
一位女记者到三峡采访旅游的情况,听说库区已经有好几万“占地移民”,以为发现了重大新闻。她打了一个电话故作神秘地问我:“是不是江水把移民的土地淹了,移民纷纷去‘乱占土地’?”
“你就是这样理解‘占地移民’的吗?”我问。
“是的,我想‘占地’二字肯定与‘抢占’、‘占领’有关嘛。听一个乡镇干部说:占地移民的事已把他整得焦头烂额。”
“呵呵,你从字面上产生奇妙联想,真是有创意嘛。”
“我想到库区调查一下占地移民的情况,不公开报道就写‘内参’,你熟悉移民的情况,要帮我一把哟。”
“你就不想想,如果移民都去抢占土地,三峡库区不早就乱成了了一锅稀粥了吗?”
我接着告诉她说,比如丰都县城全部被淹完,就要新修一座县城,在修新县城的地方又要占一大片土地,就产生了移民。原来居住、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也要进行搬迁安置,这就是“占地移民”。
“原来是这样啊,这个新闻线索让我白白激动了一天。”她感到有些失望。
三峡百万移民这道超级难题,在考库区各级政府的同时,由此而产生的一大堆专业术语,也考倒了不少新闻界的朋友。比如:生产安置、生活安置、对接工作、价差补助、机械增长、实物指标、双淹户、单淹户、线上线下、风浪线、红线、坠覆体、占地移民等等,就有上百个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
不把这些很专业的术语搞懂,怎么能写出有血有肉的稿子?即或是记者搞懂了,编辑不懂,编出来稿子又是另外一回事。
曾经,一位记者采访移民工作会议,写出一篇移民大搬迁的报道,原稿中说库区某地坚持“移民为先,移民为重”的指导思想,“生产安置移民人,生活安置移民人”,编辑拿到稿子细读之后,嫌记者写得过于啰嗦,不假思索地把“生产安置”的人数和“生活安置”的人数一加起来,并把这个数字赫赫然做到了副标题上。
这篇稿子第二天见报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读者认为是地方官员说假话:“吹牛皮不犯法,也不上税。”
政府官员认为报纸在说胡话:“总改不了假大空的德性。”
移民认为政府官员和记者串通一气“扯谎”:糊弄上级,愚弄百姓。读者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报社和政府办公室,愤怒地指责这种“睁大眼睛说瞎话的不道德行为”。
移民干部看了则认为这位记者素质太差,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可怜的记者,真是“跳进长江洗不清,一腔苦水向谁诉”。
生产安置是指农村移民的生产资料的配置,说直白一点就是“土地安置”;生活安置主要是指移民搬迁住房的安置。移民中有只淹地的,又有淹地又淹房的。“生产安置”和“生活安置”只有一字之差,这两者一相加,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曾经,一位女记者到重庆市移民局采访农村移民的安置问题,我拿出渝移发[1999]252号文件给她看。文件第四条“计划生育安置人口和房屋搬迁总人口与移民户实际安置时搬迁口相衔接”中规定:“在安置搬迁移民户的生产安置人口和房屋搬迁人口应根据该户实际合法人口进行计算,而不能按《实施计划》中1996年底人数计算,也不能按1996年底人数加千分之十二的增长率计算。”
这位女记者被这份通篇都是专业术语,比“绕口令”还难读清楚的文件吓得“花容失色”。她吃力地研读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虽吃力地向她解释了一个小时但也是白搭。因为,从她惊愕、惶惑不解的表情来看,我知道她的努力和我的努力全是徒劳。
她说,读这份文件真是“痛苦得无以复加”,基本的东西搞不懂,怎么能写出稿子?最后她“被迫”放弃了这次采访和写稿的打算。
到移民区采访,像这位记者一样“退避三舍”的人还不少。“写稿子都有难度,百万移民真不知有多难啊!”
精心策划的采访阴谋
赵春远,如果光听他的名字,加上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不看衣着长相,很难想到他是外国人。
他的真实职业是某国的一名记者。
2000年的金秋时节,赵春远只身来到长江三峡。他此行公开的身份是一个普通的旅游者,持有个人旅游护照。
三峡截流之前,由于中外旅行社在世界范围内“联袂”上演了一幕“告别三峡游”的喜剧,前来“告别”三峡的中外游客如过江之鲫,三峡沿线各旅游景点的宾馆、床位纷纷告急。旅行社早就把船票瓜分了,重庆的“黄牛党”也趁机“爆炒”旅游票价格。
像赵春远这样“孤独”的旅游者,一般是不容易搞到船票的。但这并难不倒一个职业记者。他找到一家旅行社表示,自己多出一点手续费,以自费旅游者的身份加入了一个以中国游客为主的旅游团。
当轮船进入三峡之后,游客们都被雄奇壮丽的峡江景色所吸引,而唯独赵春远不太感兴趣。他一路上打听三峡工程和三峡移民的事。他一再说是造物主给了中国的三峡,并称赞三峡工程很了不起。这些话也赢得了同行的中国游客的好感。
但在库区腹地的一个著名的旅游点,他突然向带旅游团的导游提出,家中有急事,要提前结束三峡的旅程,并说他下船之后乘车赶往重庆,再转乘飞机回国。
他下了船,见并没有人在意,就向附近的一个移民村走去。不费吹灰之力,他就找到了离江边最近的一个农家院落。这家户主姓杨,是又淹土地又淹房子的移民。
“你们是三峡移民吗?”赵春远问。
“是啊,你是……”50多岁的老杨疑惑地看着他。
“我是国的游客,到三峡来旅游。”
“啊,是老外呀,请坐请坐。”友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杨以三峡人特有的热情,端出凳子放在坝子中间。
“你们的房子要淹吗?”赵春远坐下之前递过一包香烟。
“房子是要淹的,谢谢你的烟。”老杨喜滋滋地接过香烟说。
“土地也要淹吗?”
“是的。你问这些干吗?是记者呀?”
“我不是记者,是自费旅游者。我对你们三峡移民搬家感到好奇。我们也经常搬家,提个包就走,从不带家具,你们搬家要带家具吗?”
自以为是“中国通”的赵春远知道“欲速则不达”这句话,开始“循循善诱”,一切正按着他设计的圈套进行着。
“你们老外真懒啊,搬家不带家具怎行?”老杨说。
“这么好的地方,你们愿意搬走吗?想得通吗?”
“不搬不行的,水要淹来了,想不通也得搬啊,还不是为了修三峡电站。”老杨是个直性子人,也是实话实说。
“老大爷,我要是能看到你们搬家就好了。”
“搬家有啥稀奇,有啥看头?你们外国人真是没事可干啊。”
老杨被这个年轻的老外说得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这样吧,老大爷,你找几个人搬家给我看一看,我每一个人给100块钱,好不好?”
老杨以为又碰见了财神爷。
一年前三峡旅游高峰时节,导游小姐带来过三个高鼻子老外,硬要到他家的地里挖红苕,剥莴笋菜,老外不相信绿叶藤地下会长出大个大个的红苕。三个老外轮流挥锄,挖出一个红苕就大声叫好,然后抱着粘满泥巴的红苕照相、合影。导游小姐说,老外在船上吃饭时,对薄薄的莴笋片很感兴趣,觉得亮晶晶的,质感很好,感到不可思议。
所以非要找个地方看一看,莴笋这种蔬菜是怎么长出来的,也算增加一点“见识”。
老杨从地里拔出莴笋,淘掉泥,剥了皮,当场就削出了亮晶晶的莴笋片。几个老外伸手就抓来吃,他们吃着什么佐料也不沾的莴笋片,乐得叽叽哇哇地叫个不停。导游小姐告诉他说,这些老外对中国的高楼大厦、洋房街道一点不“感冒”,但对挖红苕、刨花生、亲手摘下树上的橙子橘子等“农家乐活动”却兴趣盎然。
三个老外临走时,给了他200元钱作为补偿。后来,老杨逢人便吹嘘说,老外的见识看来也不行,连红苕、莴笋都没见过。打那以后,老杨就盼望再来几个老外来搞“农家乐”。
眼前这个老外更奇怪了,居然想看搬家。这段时间库区到处都有移民搬家,有啥稀奇?这次是不是又碰见财神爷了?一个人给100块钱?找四五个人假装搬一会儿家,不就是四五百块钱进账了吗?这可相当于养两头肥猪的利润啊,老杨心里盘算着。
“真是一人100块钱?”老杨还是有点不相信地问。
“是的,你找五六个人搬家也行,只是假装搬一会儿家,我拍几张照片做个纪念就给钱。好不好?”
“好的好的,就我们家4个人搬吧。”老杨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等好事不想更多的人来分一羹。
老杨把老伴、儿子、儿媳叫了过来,把锅碗瓢盆收了一大堆,用背篼装了起来。然后把被盖捆好,又把柜子里的东西腾空,反正是假装搬家,轻一些就好搬一些,老杨一边收拾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怎样省力。
“搬好远的路才算数?”老杨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不远不远,搬个一两百米远就行了,不过要爬一段坡。我先给200元,搬完后再给200元。”
老杨把200元揣进兜里,就组织一家人开始“搬家”。背的背,抬的抬,扛的扛,赵春远跟着“搬家队伍”走,不停地拍着照片。
突然,赵春远大声喊叫着停下来。原因是老杨一家人搬家竟然没流汗水,一路上还嘻嘻哈哈的,照片拍出来“太不真实”了。他像电影导演给演员说戏一样,要求老杨“搬家”时一路上要汗流浃背,额头上要有汗水珠儿,眼睛要有泪水,表情要沉重,就像真的离别家园一样悲伤……不然,就少给200元钱。
这下可把老杨给难住了,本来就是搞着玩的,怎么流得出眼泪?
要是真到了永远离开家乡的日子,不用他说,全家人都会难过得流泪。
但想到还有200元没拿到手,只好和家人沉下脸来搬着“沉重”的家具向村外走去……
正在这时候,乡里的移民办主任和社长过来了,他们是来动员移民迁往外省安家。远远看见的情景让人觉得好生奇怪,移民的房子都没建好,老杨一家怎么会搬家?何况,老杨还对补偿有意见?
老杨说,他是在为一个老外搞“旅游表演节目”,收几个劳务费。
赵春远的真实身份暴露,他精心策划的新闻也就此流产。按照外交辞令的说法,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两个美国记者在三峡
不少外国人对中国三峡百万大移民感到很惊愕、很困惑,也难以理解。其实,戴西方的眼镜看东方,或戴东方的眼镜看西方,用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去衡量人家的是非曲直,总难免有失偏颇。这些年来,东、西方文化一直在碰撞中融合,在碰撞中燃烧。具体的反映有合理的,当然也会有不合理的。
三峡工程开工以来,新闻大战一直是硝烟弥漫,从未停息下来。
客观地说,西方记者大多数都愿意脚踏实地地采访,客观公正地报道,他们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常常为中国同行所称道。喜欢偏听偏信、隔岸臆断的西方记者毕竟是少数。
1996年4月3日至5月20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记者齐克、萨查到三峡库区进行了为期40天深入细致的采访。
齐克在踏上东方这个神秘的古国之前,与萨查一起搜集了一大堆西方报道三峡工程的文章、图片资料和书籍。在三峡采访时,为核实是否有大量的移民住帐篷,他在万州花了两天时间采访,并向当地老百姓打听,结果没有发现移民住帐篷。
水都没涨哩,怎么会有人住帐篷呢?
“西方关于三峡工程的负面报道大多是不真实的。”齐克和萨查在对三峡库区重庆至宜昌16个县、市、镇采访40天后,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萨查是摄影记者,一到三峡就兴奋得“OK,OK”地叫个不停,完全陶醉在如诗如画的三峡长廊中。每到一地,他端起相机就噼噼啪啪照个不停,三峡的人文景观、自然风光、枢纽工程、移民生活都使他眼界大开,收获不小。
在三峡峡谷屈原镇的西陵村,他跟踪拍摄了移民郑新年举家搬迁的全过程。从郑新年一家整理家具,搬家具上船,并随船到湖北董市安家的经过,全部摄入了他的镜头。这位记者说,他没有想到移民搬迁的场面如此感人,也没有想到移民搬迁竟然进行得如此顺利。这与他在西方报刊上看到的大不一样。他希望那些采访走马观花、隔岸臆断、报道不负责任的记者,多多深入了解些真实情况。他的感触是:这么多的移民搬迁,恐怕只有中国才能做到。
齐克说,三峡工程并不像西方有些传媒说的那样存在着严重问题,这个工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工程,不存在问题、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记者同行们应对这些问题深入地了解并作客观报道。一般记者在三峡呆上两三天,还没弄清三峡工程、三峡移民是怎么回事就走了,这怎么能写出客观公正的报道呢?
齐克同时抱怨说,产生这些问题,中国方面也有一定的责任,既然能投以巨额资金兴建三峡,就可以拿出一点钱来做好对外宣传工作,三峡工程的形象对该工程的顺利进行十分重要。
“人与人不同,花有百样红”,记者也一样是人,如果用一只眼睛看三峡,当然有失偏颇,也有失公允。用两只眼睛看,多看、细看,才真实、客观、公正。
芬兰一画报社驻京记者林达到过重庆万州区,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支局局长山田道明也到过万州区,这二人分别在万州城区调查了近百名居民,居民中95%支持上三峡工程,并希望通过移民搬迁加快城市建设。
现在,移民在搬迁中也吃到了苦头,尝到了甜头。他们对三峡的态度也有了180度的大转弯,这是叫人始料不及的。
要破解百万移民这道难题,唤起成千上万人的热忱,形成“人人关心库区环境,个个关注移民生存”的氛围,只有在强大的舆论支撑和引导下,库区各级政府和移民才会充满激情地开拓前行。
新闻媒体在库区的采访报道,有时也有难言之隐。主要是移民区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搞得不好就失之偏颇,出发点是“想帮忙”,结果却是“帮倒忙,越帮越忙”。
曾有媒体人士向我抱怨,库区看起来新闻素材充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一写出来就变了味,不是“复杂的政策尺度”把握不准,就是“一踩九头跷”,惹是生非不少。错误和挫折生出的许多教训,也使新闻界“比较地聪明起来了”,移民区的事写不好就不写,不写报纸就不登,不登顶多挨点“小批评”,总不会犯错误噻。
也许,要谈三峡和三峡移民问题,只有过了若干年后,让历史检验后才有资格评说。现在,包括我在内的一群人,总是怀着一腔热情想把三峡的事说个清楚,一脚还没踏入库区,就已陷入了“先入为主”的泥淖。也许世间的每一个人,都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和感觉,但“跟着感觉走”有时是一种“危险的举动”。
人最容易忘记的就是:感觉往往会成功地欺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