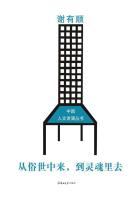那时,我们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很少照相,照相是很奢侈很精神的一件事,而那时我们是在深山架桥铺路,不能照相也并不影响我们的少年情怀,我们有梦,有很甜美很绚丽的梦,而那帮老工人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经常就是这样比较难听地称呼他们的。
他们也就是四五十岁,但因了深色的劳动服与粗糙的山风,已显得很苍老,甚至是糟糕透顶。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宿命是他们一年四季所有的表情,当然他们是残缺的,甚至是一种没有活人气息的缺失,看起来只是一种莫名。那时,我们并不懂这些,我们十分的厌恶他们,认为他们无非是为了挣钱,抛家离子,全都像抽了脊骨的动物,软沓沓地集体龟缩在从来都不怎么挺拔的帐篷里,灰暗,糜烂与粗陋。那时,老工人烦透了我们这些嘻嘻哈哈的男娃女娃,我们不明白,关于爱情,他们为何有那么多的刻毒与冷漠!一到冬天,他们就准确地绻缩成一团黑色物状,路和桥囊裹在茫茫雪天,他们囊裹在茫茫雪天,除了这样勤奋地做工,就是围着火炉热烈地思念家乡与女人。当然还有夏天,还有其他总会有风景的所有季节,他们就这样数着冷与热、酸与苦,数着一点点失掉的日子,和随着日子或许是增加或许是减少的情感。他们可能也思忖过要不要随便找一个女人,来安抚那太焦灼太寂寥的身体,不过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一般还要受到我们最肆无忌惮的鄙视。
受到鄙视的还有那太节俭了一点的饭菜。外号叫盐巴的老汉,就是因米饭拌盐而著称,他们的工资都通过那个瘦小的邮差,一张张寄回到家里,那个飘渺的不怎么真实的家和家里不怎么真实的女人,那么眼前,他们真是什么都没有了,但为此我们也很少同情与尊重他们,我们不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思维。
守护一份坚贞的爱情是要有极大勇气的。
那时的山风是淳朴的。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在这件事情上显然有些疑虑与犹豫。
忽然就有了那个小城,它不是太繁华,却有一定的喧闹,不是太时尚,却与我们惯常住的山沟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飘着落叶的深秋,几辆卡车把我们连同老工人,运到了小城,要为小城修建一座立交桥,工程还算庞大,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黄昏像模像样地踩铺地砖的街道散步,这可是我们的体面与荣耀,散步时,男娃女娃一起,叮呤的笑声传的很远,当然,我们年轻,我们可以把爱高高地悬挂在额头。这时,我们真厌恶这些软体老工人,他们并不理会什么散步,太繁重的体力劳动取消了这份悠闲。小城边的那个舞厅成了老工人心中永远的疼,他们没有谁有勇气进去,但对迷离的灯光、欢快的音乐充满向往,对进进出出扭着小蛮腰的女人充满向往,小蛮腰从他们身边袅袅经过时的馨香,使他们非常的烦躁。
真是太不怀好意太给我们丢人了。幸亏,小城女人没有理会这一团团黑色莫名的老工人。
工程进入攻坚,钢筋水泥铺排了很远,那个被称为工地的地方日夜兼程,夜晚,它灯火通明,几乎望不见深邃的夜空。我们常在午夜为工地送一顿夜饭。食堂与工地还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让我们稍稍以一个旁观者看去,我们是不以为然的,不管他们如何在庞大的吊车上碾转,如何在高的脚手架上挥汗,在低的桥墩下如负重的蜗牛,是比不上我们内心梦想的高尚,我们爱情的美好,谁让他们是一团背井离乡的黑色愁绪,他们只能过一无所有的日子,宿命是他们一年四季的表情。
我们一般是推着一大锅汤汤水水的薄面片,最多加上几笼包子,睡意惺忪地走向工地。夜色总会涌上来一股莫名情绪,现在,我们才明白,那是有关男人与女人的情绪。为此,我们会更加地讨厌老工人,把包子漫不经心,要么是重重地摔在有秩序地伸过来的碗里。这些要么是黄铁碗围着一圈锈迹斑斑的黑边,要么是白铁碗,突兀地有几个大小不等的黑疤,像他们眼巴巴睁着的眼睛,要么是一个硕大的敞着的盆,浑身布满横七竖八的精细的印痕,这些都是一张张又脏又破的脸,整天伸过来伸过去的。但他们并不多在意,盛了饭端了碗就走,默默的,只留过来一个弯曲的后背,可是我们早已啪地一下关闭了卖饭窗口的小木门。
除了更深地熟悉了小城冷寂的夜色,他们当然什么也没有得到。听说小城有一片很著名是湿地风光,他们却说有什么好看的,我们深觉这话的意思是只想看小城的女人。为此,又得到我们更深一层的鄙视。尽管他们已很卖劲地把立交桥建好,剪彩那天,工地打扮的花枝招展,他们局促地搓着手,完全一副腼腆新郎倌的做派。
后来,卡车又晃晃荡荡地载着我们回到了山坳,老工人除去挣了一点奖金之外,感情上自然是一无所获,这次离开,差不多是彻底粉碎了他们所有的肥皂泡,而我们年轻人的爱情显然在疯长。
都是因了那一份工钱,他们的日子才会有秩序地前行,但是又因了女人,他们的日子又显得踉跄,显得蓬头垢面,涌动着某种情绪,就这样,一直,一直到了再也抡不起那个镐头,就回到了那个近乎于图腾一样的家了。他的这漫漫岁月,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像是在还黑夜里吹过一阵看不见的风。
但是,家里的女人有的已经病死,只留下冷若冰霜的孩子,有的没有等到他回来就另嫁了人,也有的忠实地守在了家里,可是,由于这长长厚厚的岁月,他们的爱情已变的支离破碎,不辨当初,只有莫名的怪异,像一支怎么也调试不出和谐音调的破损竖琴。
从此以后,那个山坳,那个小城,还有我们这些任性的叛逆的男娃女娃成了他们记忆中反复上演的场景,并永远介于这样的拉扯、碰撞与破碎之中。
如今,我们这些男娃女娃差不多也到了老工人的年龄,身边也围着一群嘻嘻哈哈的年轻人,我们暂且还不能相信,历史难道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