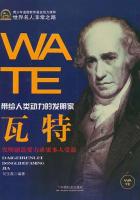“我的儿子不可以想着为我的死报仇。他应该从中得到教益。和平统治应该成为他努力的目标。如无必要,不得模仿我而重启战端,否则便是愚蠢。重复我的道路就意味着否定我之前的一切……同一个世纪,不要将同样的事做上两次。过去我出于不得已斥诸武力,以期征服欧洲,而今,却必须说服它……我的新思想已经在法国和欧洲生根。这些新思想不可能再倒退回去。但愿我的儿子能够将我播下的种子培育成熟……
“英国人为了粉饰迫害我的罪过有可能帮助我的儿子返回法国。但为了与英国和睦相处,无论如何都必须照顾到它的商业利益。这种必要性会有两种结果,对英作战或与英国一起共同参与世界贸易。目前只有后者可行。在法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外交要比内政重要。我留给我的儿子足够的力量与别人的好感,他只需要利用一种武器来继续我的事业,那就是宽容且互谅的外交。
“……希望我的儿子永远不用借助外国势力登上皇位。他不能为了统治而统治,而应该争取后世的颂扬。希望他尽可能多接近我的家族。我的母亲具有古典美德……若治理有方,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容易统治的民族。他们的理解力无与伦比,敏捷且透彻。他们能马上分辨出,谁是为他们工作的,而谁又不是。但一定要顺着他们的脾性说话。否则,他们不安分的思想会变得异常活跃,会引起骚乱,诱发暴动……
“他要蔑视一切政党,只接近民众。除了叛国者,他必须尽弃前嫌。他应唯才是举,唯功是赏。
“在法国,贵族的影响最为微小。依赖于他们无异于沙上建塔。在法国,唯有依靠民众才能有伟大成就。
“……我从来都是依靠民众。我建立了第一个照顾各个阶层利益的政府……民族利益的分裂会导致内战。天然不可分的东西便绝不能分,否则便将毁灭它。我并不重视宪法……但基本原则应是普选。
“我所提拔的贵族对我的儿子没有任何用处。
“……我的独裁是不得已。证据就是,我想要的权力并不多,但人们总是提供给我更多的权力……对我的儿子来说情形会有所改变。他的权力将引发争论,他事先就应当估计到人们要求自由的愿望……君主不应为了统治而统治,而是要启蒙民智、传播道德和实现富足。所有虚假的东西不仅起不到帮助的作用,反而有可能让事情更糟。
“……两种同样强有力的热情鼓舞着法国人民,它们看来似乎相互矛盾,但确系同源,即爱自由和爱荣誉。政府只有实现最大限度的公正才能满足这两种需求。为政之道并不在于遵循某个好的理论,而是因地制宜进行建设。必须要认识到,服从于必要性,然后利用这种必要性。
“在政府的手中,出版自由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政府可以借此将健康的观点和正确的原则传播到帝国最偏远的角落。忽视出版自由,无异于临渊酣睡……在生死攸关之时,要么疏导,要么压制。
“是我让新思想与新事物在欧洲各处胜利进军,我的儿子应继承这一事业:将欧洲统一为不可分的联邦。
“欧洲的巨变无可避免。要制止这一转变,无异于螳臂当车。唯有积极参与,方能成就众人共同的心愿和希望。
“我儿子的地位将是困难的症结。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诉诸武力来解决某些问题,希望我的儿子能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后才解决它们。要是我1812年击败俄国,将可一劳永逸地解决未来100年的和平问题,同时我也可以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将民族矛盾的“百年绳结”一剑斩开。现在,人们必须自己去解决了。今后对于重要问题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北方,而是地中海沿岸。那里有足够的东西,能够满足所有强国的野心。在那里,只需付出几小块贫瘠的土地就可以换到文明国家的幸福。君主们应该明白,欧洲不应当是国际仇恨的策源地。
“消除偏见,扩大利益,拓展贸易,没有哪个国家能垄断贸易。
“如果我儿子的心中没有燃起神圣的火焰,没有任何向善之心,那么你们告诉他的一切,他所学到的一切都将起不到任何作用。只要他有向善之心,就足以成就伟业。我希望,他能够配得上他的使命。
“如果他们不让你们去维也纳……”
这时他的力量突然消失了:遗嘱至此戛然而止,仿佛是通灵者的呓语。这个垂死之人用来教育他那可怜的儿子的训示,在100年后依然可以教育欧洲。无论我们打算怎么解决今天的国家问题,其实这个天才都已经给出了答案。
19
梦境 官方死亡 死亡辩白 最后困窘 空白的日期
最后命令 长逝
思想一泻千里之后,创造的源泉枯竭了。美妙的梦境浮现在眼前。命运似乎要让他安乐地死去。完成遗嘱后的第二天,他躺在那里,无痛无忧,希望的云彩环绕着他:
“如果我死了,你们都能返回欧洲,你们可以重新见到你们的妻子,而我将会在天堂与勇士们重逢。他们会向我走来。达武、迪罗克、内伊、缪拉、马塞纳、贝尔蒂埃,我们一起谈论共同开创的事业。我给他们讲述我后来的际遇。看到我,他们一定会重燃昔日的热情,回想往日的荣誉。然后我们会同西庇阿、汉尼拔、恺撒、腓特烈谈论我们的战争。这是无比惬意之事!世上的人若看到这么多杰出的将帅会聚于此,一定吓得够呛!”
这就是一个垂死之人的奇思妙想。关于他生活的对话数以千计,可那些都不能如此真切地反映出他灵魂的天真。唯有此刻,这个灵魂在半梦半醒之间孩子似的描绘出一个英雄的世界,他的将领们与古罗马的将领们待在一处。他仿佛生活在天堂似的田园中,这里到处都以谈论大炮为乐。谈话之际,那个英国医生走进了房间,拿破仑最终还是同意接受这个医生的治疗。
就在此刻,他内心悠扬的笛声突然中断,激昂的鼓声则再次响起。政治家回到了现实。一贯的作风又回来了,他换了一副腔调,中间没有任何过渡,立即就发表了一个形式完备的对于自己死亡的官方讲话:
“靠近些,贝特朗,你把我的话逐字逐句地翻译给这位先生听。我是受辱而死,这个结局并不意外,因为当年他们向我伸出的就是侮辱性的手。我投奔英国人民,希望托庇于英国,了却残生。然而他们竟践踏了国际法,公然给我套上枷锁……英国说服了各国君主,于是全世界就看到了最骇人听闻的一幕,我孑然一身,被四个强国大肆攻击。在这岩岛上,你们是怎样对待我的!但凡能折磨我,你们无所不用其极!……你们处心积虑,要慢慢将我折磨致死!那个无耻的总督就是你们的大臣们派来的鹰犬和爪牙!就算是死,我也要像高傲的威尼斯共和国那样!我能遗赠给英国王室的就是杀我的刽子手这个头衔!”
发泄完后他倒在了枕头上。医生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皇帝的亲信们也惶恐不安。这算什么?结语、抗议还是诅咒?这不过是政治行为!晚上,他已经让人给他念汉尼拔的征战录了。
第二天,4月21日,距他去世还有两个星期。他让人把科西嘉神父叫来。自从神父来岛后,他每个星期天都做弥撒。但除此之外他与这个神父不相往来。此时,他说:“你知道什么是停灵会堂吗?你以前主持过这种会堂吗?没有?那你现在就主持我的吧。”然后拿破仑给他讲了一些细节,“我死后,你要在我床边设置祭坛,按常礼给我做弥撒,直到我入土。”
晚上,神父在他那里待了近一小时。因为神父带的礼器不齐全,这一小时他应该只是和皇帝商议此事,肯定没有听他的忏悔。因为无论现在还是过去,40年来皇帝从未领过圣餐。
病人的身体完全垮了。他几个星期都没有刮过胡子了,面颊深陷,脸色黝黑。现在他让人把床搬到了客厅,因为他的卧室太窄了。剧烈的胃疼会让他抽搐不止。风暴平静下来的时候,他总是一再地想起很多人的名字,他想要把遗产分给他们。在此期间,他的梦境重新变得轻松起来,几个女人出现在他面前,绝对没有玛丽·路易丝。“我看到了亲爱的约瑟芬,可她不愿拥抱我……她没有变,依然那么爱我。她说我们马上会重逢,再也不分开了。她向我保证——你看到她了吗?”如同那个关于将军的梦,这次的幻觉来自孩子的天堂,童话的国度。
病情若稍好些,他会让人读最近的报纸。有一次,报纸上的攻击令他情绪激动。他令人把遗嘱拿来,这份遗嘱他曾经费力地封印了很多次,现在他急切地把它打开,一言不发,用颤抖的手在上面写道:
“我下令逮捕当甘公爵并把他送上法庭:因为该审判对法国人民的安全、利益和荣誉十分必要。当时阿托斯伯爵供认,他在巴黎豢养了60名刺客。”
就像两个幽灵相对而视:一个是已死的波旁,一个是将死的波拿巴。
4月27日,他又让人取来遗嘱,费力地重新封印。他让人重新给箱子和柜子里的东西列清单,把银行信用证装入信封,亲手给每个信封写上说明。在此期间他不停地呕吐、发抖。他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盖上章,当着所有人的面核对包裹清单。他对英国是如此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