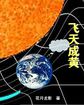没过多长时间,幸运的诗人便到了一间有着尖拱圆顶的暖融融的房间里,坐在一张漂亮的桌子跟前,当然,还有一张舒服的床,并且可以独自跟一位俏丽的少女在一起。这般奇遇就像施了咒语似的。
那少女看上去对他并不在意,不停地走来走去,有时绊到某个小矮凳,有时跟她的小山羊说说话儿,有时这儿撅一撅嘴,那儿又撅一撅嘴。最后她或许是走累了,于是走过来在桌子边坐下。
格兰古瓦仔细地端详着她,在心里嘀咕着道:“这样说来,这就是那个所谓的爱斯梅拉达罗?一位下凡的仙女!一个街头舞女!既高贵又卑贱!上午最终断送了我圣迹剧的是她!今晚救了我的也是她!她是我的丧门星!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并且,还是一个极漂亮的姑娘!而且一定爱我爱到痴狂,才会那样把我要了来。”想到这里,他不由凑近到少女的身旁,那模样儿显得又雄劲又诱惑,把她吓得直往后退,然后喝叱道:“你要做什么?”“这还用得着问我吗,可爱的爱斯梅拉达?”格兰古瓦应道,语气是那样的热情,连他自己听了也不由吃惊。
埃及女郎瞪着一对大眼睛:“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怎么!”格兰古瓦又说,浑身越来越躁热。“难道我不是属于你的吗,可爱的人儿?你不也是属于我的吗?”
既然一语说破,他立刻趁机把她抱住。吉卜赛女郎的紧胸上衣就像鳗鱼皮似的,一下子从他手中溜走了。她纵身一跳,跳到房间另一头去了,弯下身子,随即又挺起身来,手里握着一把匕首,格兰古瓦压根儿没弄明白这匕首是从哪里来的。她又恼怒又高傲,面孔红得像红苹果似的,眼珠里也闪着光。同时,那只白山羊也跑过来站在她前面,顶着两只漂亮的尖角,摆开决一雌雄的架势。这一切只是一眨眼的工夫。
我们的哲学家惊得呆住了,一会儿看看山羊,一会儿望望少女。
“圣母啊!看目的地这两个泼辣的女人!”他惊魂未定,却能够开口了,终于说道。
吉卜赛女郎也打破了沉默。“想不到你是这么一个破落户!”“对不起,小姐!”格兰古瓦此时已笑容满脸,说道。
“既是这样,您为什么要我做丈夫呢?”“我是不想看着你被人吊死?”“这么说来,您这样做只是想救我一次,没有别的要求?”诗人本来满怀爱意,这时有点颓唐了。“你要我有什么别的念头呢?”格兰古瓦闭了闭嘴唇,又说道:“算了吧,我演丘必特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成功。不过又何必摔破那只可怜的瓦罐呢?”
然而,爱斯梅拉达手中的匕首和小山羊的犄角一直毫不松懈。
“爱斯梅拉达小姐,我们相安无事吧!”诗人说道。“我不是小堡的文书录事,不会去找您的麻烦,我们还是谈正经话题吧。我用我升天堂的资本作押,向您发誓:不得到您的许可,绝不靠近您。不过,还是给我吃点儿饭吧。”
埃及女郎没有回答。只见她满脸轻蔑,撅了撅小嘴,然后猛地把头一扬,放声大笑起来,随即那把小巧玲珑的匕首,如同出现时那样莫名奇妙,倏忽地又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桌上摆上了一块黑面包,一薄片猪油,几只干皱的苹果,一罐麦酒。格兰古瓦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铁的餐叉和瓷盘碰得当当直响,仿佛他全部的爱欲都已变为食欲了。
少女坐在他前面,默默地盯着他吃,显然她又有了什么想法,脸上不时露出笑意。
一支黄蜡烛照亮了这一幕狼吞虎咽和沉思默想相掩映的情景。
格兰古瓦在狼吞虎咽了一阵之后,发现桌上只剩下一只苹果了,不禁觉得有点尴尬。“您不吃吗,爱斯梅拉达小姐?”
她摇了摇头,思考的目光在盯着圆屋顶。于是他提高嗓门又喊了一声:“小姐!”看样子她好像没有听见。
他更大声地喊道:“爱斯梅拉达小姐!”还是毫无用处。少女的心思在别处,格兰古瓦声音的力量还不足以把她拉回来。幸好这时山羊来帮忙了,轻轻拽了拽女主人的袖子。埃及女郎急忙问道:“这是怎么了?佳丽?”
“它饿了。”格兰古瓦应道,很高兴能同她闲谈起来。美人儿爱斯梅拉达动手把面包掰碎,佳丽就着她的手心窝吃了起来,仪态万方。现在,格兰古瓦不让她有时间再胡思乱想,便大着胆子向她提了一个微妙的问题:“您确实不想我做丈夫吗?”少女瞪了他一眼,应道:“不要。”“做您的情人呢?”格兰古瓦又问。她撅了撅嘴,回答说:“不要。”
“做您的朋友呢?”格兰古瓦又问。她再瞪了他一眼,想了想,答道:“可能吧。”
也许这几个字向来是哲学家所珍惜的,格兰古瓦一听,胆子便大了。
“您知道什么是友谊吗?”他问道。“知道。”埃及女郎回答。“友谊,就好比是兄妹俩,两人的灵魂相互接触而不混合,又像一只手的两个指头。”
“爱情呢?”格兰古瓦再问。
“喔!爱情,”她的声音发颤,目光灼热。“那既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融合为一个天使。那就是天堂!”
这个街头舞女说这话的时候,那样娇艳妩媚,深深震撼着格兰古瓦的心灵,而且他觉得,这俏现容貌与她言语中那种几乎富有东方感的韵味非常相称。
于是格兰古瓦穷追不舍。
“那怎样的男人才能让您欢心呢?”“是那种真正的大丈夫。”“那我怎么样呢?”
“我心中的男子汉要头戴铁盔,手执利剑,靴跟上装有金马刺。”
“得了,照您这样说,没有马骑就不算是男子汉啦。”格兰古瓦回答说。“莫非您爱着一个人吧?”
“恋爱吗?”
“恋爱。”
她想了一会儿,随后表情怪怪地说:“我很快就会知道了。”
“为什么不能是今晚?”诗人又情切地问道。“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她目光严肃地瞅了他一眼。“我只能爱一个能保卫我的男子汉。”格兰古瓦当即涨紫了脸,但也只好认了。显然,少女影射的是刚才在那危急关头,他并没有怎么帮助她。这一晚,遭受的危险太多了,上面那件事他倒忘记了,这时才又想了起来,于是拍拍额头,说道:
“对啦,小姐,我本该从那件事谈起的。您到底是怎么逃脱卡齐莫多的恶掌的呢?”
吉卜赛女郎一听,浑身打了个寒战。“喔!那可怕的驼子!”她边说边用手捂住脸,浑身颤抖,好像冷得发抖。“的确可怕!”格兰古瓦也不退步,决心打破沙锅问到底:
“可您到底是怎么逃脱的?”爱斯梅拉达轻轻地叹息几声,但是默不作声。“您知道他为什么追踪您吗?”格兰古瓦竭力采用迂回的办法,再回到他原来提出的问题。“不知道。”少女应道,紧跟着又说:“那时您也跟着我的,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瞒您说,我也不清楚。”一阵沉默。格兰古瓦用餐刀划着桌子。少女微笑着,好像透过墙在望着什么。忽然间,她用模糊的声调唱了起来:
当羽毛绚丽的小鸟疲惫了。而大地……她戛然而止,然后抚摸起佳丽来了。
“您这只山羊挺漂亮的。”格兰古瓦说道。“这是我妹妹。”她应道。“为什么别人叫您爱斯梅拉达呢?”诗人问道。“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真的?”她从胸襟里取出一个小香囊来,从里面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樟脑气味。它的外面包着绿绸子,正中装着一大颗仿绿宝石的绿玻璃珠子。“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她说道。格兰古瓦伸手要去拿这个小香囊,她赶忙往后一缩,说:
“别碰!这是护身符。你一碰,会破坏它的魔力的,再不然,它的法力会把你魔住。”
诗人愈发好奇了。“是谁给您的?”
她把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然后把护身符再藏回胸襟里。
他设法又问些别的问题,可是她几乎不再理睬他。“爱斯梅拉达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她答道。“是哪种语言?”“是埃及语吧,我自认为。”
“我早就料到了。”格兰古瓦说道。“您不是法国人?”“我毫无所知。”
“您有父母吗?”她哼起一首古老的歌谣:
我的父亲是雄鸟,我的母亲是雌鸟,我过河不用小舟,我过河不用大船,我的母亲是雌鸟,我的父亲是雄鸟。
“真好听。”格兰古瓦说道。“您来法国时有多大?”“一丁点儿大。”
“到巴黎呢?”“去年。我们从教皇门进城时,我看见黄莺从芦苇丛里飞向天空,那是八月底;我还说:‘今年气温会很低。’”
“去冬确实很冷。”格兰古瓦说道,很高兴又开始攀谈起来了。“这么说,您天生就能预知啦?”
她又不愿理睬了。“不。”
“你们称为埃及公爵的那个人,是你们部落的领头人吧?”
“是。”“可是他给我们指婚的呀。”诗人很难为情,有意指明这一点。
她又习惯地撅了撅嘴,说:“我连您的名字都不知道呢!”
“我的名字?您想知道的话,我马上告诉您:皮埃尔·格兰古瓦。”
“我知道有个名字更美丽。”她说道。“您真会开玩笑!”诗人接着说。“不过,我不会生您的气的。喂,今后您对我了解多了,或许会对我好的。还有,您对我那样理解信任,把您的身世讲告诉我,我也得向您谈一点我的身世。我叫皮埃尔·格兰古瓦,是戈内斯公证所佃农的儿子。二十年前巴黎受围困时,我父亲被勃艮第人吊死了,母亲被庇卡底人杀死了。我六岁就成了孤儿,一年到头唯有巴黎的碎石路面给我当鞋穿。从六岁到十六岁这段到底是怎么煎熬过来的,我自己都不清楚,总之是到处流浪,没有被饿了。十六岁时,我下决心找个差使干干,接二连三地,总之三百六十行都干过了。后来,我终于发现自己不论干什么都缺少点什么;眼见自己没有任何出息,就甘心地当个诗人,写起韵文来了。有一天,我进去地,碰到了圣母院德高望重的住持堂·克洛德·弗罗洛大人。承蒙他的关心,细心培养,我今天才成为一个真正的文人,可以说,只要不是炼金术,我样样都精通。今天在司法宫大厅演出圣迹剧,观众人山人海,在下便是这出戏的作者。我还写了一本书,内容是关于一四六五年出现的那一颗曾使一个人发疯的大慧星。我还有其他一些成绩。因为我多少可以算是个制炮木匠,所以参加了约翰·莫格那门大炮的制造,您知道,在试放的那天,一下子就炸死了24个看热闹的观众。您瞧,我作为配婚对象并不赖吧。最后,我本人,还有我的心智,还有我的学识,还有我的文才,所有都完全恭从您的命令。我已做好准备,愿同您一起生活,忠贞不贰并且是快快乐乐同您生活在一起。小姐,都悉听尊便,您若觉得好,就成为夫妻;您若认为做兄妹更好,那就作为兄妹。”格兰古瓦说到这里打住了,观察这番高谈阔论对女郎的作用如何。只见她的眼睛盯着地上。
“弗比斯,”她低声说道。然后转向诗人,问道:“弗比斯,这是什么意思?”
格兰古瓦不明白他那番宏论和这个问题之间有什么牵连,但他还是马上答道:“这是拉丁语一个词,意思是太阳。”
“太阳!”她立即说道。“这是一个极其英俊的弓手、一个神的名字。”格兰古瓦又加了一句。“神!”埃及女郎重复了一声,腔调里带有某种思念和热情的意味。正在这时候,恰好她的手镯有一只掉了下来,格兰古瓦连忙弯身去捡。等他直起身来,那少女和山羊早已不见了。他听见门闩的声音,那扇小门从外面反锁上了。
“她至少总得留下一张床吧?”我们的哲学家叹息了一声后说道。
他绕着房间转了一圈,没有可以睡觉的家具,只有一只很长的大箱子,箱盖还是雕了花的。格兰古瓦躺了上去,就和米克罗梅加斯伸直身子躺在阿尔卑斯山顶上的感觉很相似。
“算了!能忍则忍吧。不过,这真是一个离奇的新婚之夜。多可惜呀!摔罐成亲,具有某种铅华洗尽的朴素的古风,本来我还挺快乐的哩。”他尽力将就着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