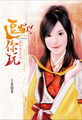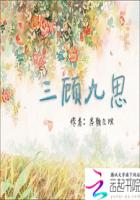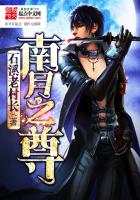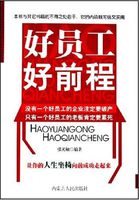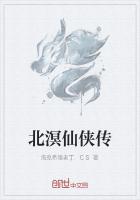中国当代法治史上有个小问题,就是1955年建立学部的时候,学部委员中为什么没有法学家?这是个简单问题,但又是个复杂问题。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中国是帝制国家,农耕社会是主要特征,传统社会的治理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中,有许多办法与现代法治相通,但中国传统社会不是法治社会,这一点学术界有共识。法治社会,严格讲也是西方经验。晚清中国向西方学习,法治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应当说,当时中国有见识的人,还是明白一个走向现代社会的国家,法治是极其重要的内容,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法治国家,这也是共识,法治比专制好,这不但是现代知识,也是现代道德,也是现代常识。
早期中国人对法治的理解,我个人以为相当成熟。我看过黄人编纂、1911年由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的一本《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其中有一个专门辞条:“法治国”。这个辞条的解释是:“对于专制国而起者。在专制国,统治者为君主,国权随意行使,不拘法规,纵令国权之行使有经规定者,亦只为君主所下之训令,而国家与臣民之间,无拘束之法规,是为绝对之专制国。专制国,亦有民法、刑法,民事、刑事之裁判,国家亦有拘束者,然行政权之行使,则无法规之拘束,反之在法治国,不唯司法权拘束于法规,即行政权之行使,亦拘束于法规,不唯行政官厅,即君主与行政权之行使,亦拘束于法规。行政法,为关于国家与臣民之行政之法规,有拘束之力,如此行政悉依法规者,谓之法治国。此行政法规之原则,依法律而定,在君主一方,不能任意制定变更,必得议会之协赞而后可,因此行政法规上,为治国之基础。凡法治国所定各条件,若行政官厅有背法规时,可以行政诉讼——行政诉愿方法救济之。”
进入“百科辞典”一类书中的知识,一般是当时社会有普遍认同的观念,也就是说,当一种外来的知识,成为中国人一般知识系统中的共同知识时,这些知识才有可能稳定下来而进入相关的“辞典”。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向认同好东西在哪里都好的判断,东西的冲突和不适应,过分强调东西差异,其实常常是我们排外的借口,我们必须相信人类有共同的人生经验,这也就产生了共同的人生智慧。中国人的法治知识和法治观念,至少我们从上引的那个辞条判断,可以认为相当成熟。我们法治观念的退化是1949年后的事。
1948年,国民政府就完成了中国第一届院士的选举工作,对第一届中国院士的选举工作,当时和后来都有所批评,但人们公认这个选举大体公正,确实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这个选举为后人称道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学术和政治的分离,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一向批评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马寅初都当选为院士。但这个传统到了1955年学部建立的时候却放弃了。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是另外一种方式,据当时负责学部筹备工作并担任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秘书的刘大年回忆:“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产生属于协商性质,是协商产生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人选是科学家推荐,但推荐不是选举。”刘大年回忆说,社会科学方面是在提出名单之前,征求了各学科主要人物的意见。他当时参加了这些活动,主要在北京地区找有关人士谈。北京以外的就没有去找,是书面征求意见的。他记得当时找了这样几方面的人:哲学方面有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汤用彤;语言学方面有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叔湘;历史学方面有季羡林;经济学方面有狄超白,等等。当然不止这几位,还有一些他记不清了。在征求意见时,他们首先把科学院的精神告诉大家。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政治的标准。社会科学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根据这个要求,来征求他们认为适合做学部委员的人选。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
1953年7月21日,张稼夫在科学院第23次常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学部的完整构想。当时的想法是:“成立学部,以改善学术领导工作,扩大学术领导机构。拟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四部。学部之下成立部务委员会;部务部委会下设常务委员,常务委员建立工作会议,吸收秘书工作人员参加。”
1955年1月6日,中科院党组第一次会议讨论筹建学部问题,认为这是当年党组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对于组建学部的工作机构和相关人员都进行了讨论。经过近半年的紧张工作,1955年5月9日,科学院党组致函中宣部,汇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对学部委员名单所作的修改情况,学部委员名单由238人,减至224人。中央审批时,又加了11人,最后名单成为235人。
科学院在给中宣部的信中认为,学部委员选定的标准是从学术水平和政治情况两方面考虑。总的原则是:“学部委员必须是学术水平较高,在本门学科中较有声望,政治上无现行反革命嫌疑的人。”
根据这个原则,科学院定出了不应列入的三条标准和应列入的四条标准。不应列入的三条标准是:
1.学术水平较高,但政治上有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嫌疑者。
2.学术水平较高,目前虽无现行可疑情节,但因历史上有严重恶迹为科学界所不满者。
3.学术水平一般,在本门学科中威望不高者。
应列入的四条标准是:
1.学术水平较高,政治上虽有某些可疑情节,但无适当理由向科学界进行公开解释或因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担任着国家机关或企业厂矿重要职务而不能不用者。
2.学术水平虽然不高,政治上也无可疑之处,但因该学科人才十分缺少,必须适当照顾者。
3.旧科学界代表性人物,然有的学术水平不高,有的学术观点陈旧甚至反动为了照顾旧的科学传统。
4.由于工作需要,党派到各学术部门从事学术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学术水平不高或懂得学术很少。
当时科学院对中国科学界的总体评价是:科学基础仍很薄弱,学术水平一般不高,各门学科的发展亦不平衡,旧科学家中政治情况又比较复杂。
应该说,1949年前后,新政权对未来科学体制的设想还是非常努力。竺可桢在参加会见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时曾问及苏联科学院院士的选举情况,政权接收过程中,比较早地考虑到了未来中国科学体制的制度设计,当时建立院士制度是高层和知识精英共同的理想,作为向院士制度过度的一种设想,建立学部是一种临时选择。1955年5月31日学部成立前一天的预备会上,郭沫若说:“科学院应该以院士、通讯院士为基础的,中央已交给我们建立院士制度,学位制度的任务了……正式的科学院需要等院士大会选出院长、副院长、及主席团,学部委员会是产生院士的基础。”
1955年2月12日科学院在给周恩来和陈毅的一封信中认为,对于原中央研究的院士,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没有承认,现在承认这些院士,他们不知该采取什么态度。信中说:“如果我们采取‘宁缺勿滥’的方针,则有许多资历老而学术上有错误或没有成就者,如陶孟和、马寅初、冯友兰等人就势必被淘汰,这样做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当前的工作;如果把现在大陆的1948年选的院士都承认下来,再另增加一批新院士,则对比之下人选就势必太多太滥,如选择不当反而会造成新的纠纷。”所以他们建议,先以“学部联席会议和院务委员会”的组织作为正式建立院士制度以前的过渡形式。陈毅在学部成立后的一次学部联席会议上特别强调:“我们科学院现在也是先搞学部,再过渡到院士制度,选举院长,从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也有一个办法是先搞一批院士、选举院长,再搞学部,由上而下,这样最不得人心。”
按当时的设想,学部的过渡期大约是一到三年,但1957年以后,这个工作实际上就停止了。但在当时的构想里学部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而是一个领导机构。科学院在学部成立后的一个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至于院士制度实行后,学部委员制度仍可并行不悖,因学部委员的团结面比院士更加广泛,对团结全国科学家和沟通科学院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可以说学部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学部建立中一个值得肯定的思路是它保留了对原中央研究院制度中包括人文科学的理念。郭沫若在中国科学刚刚组建时的一次茶话会上特别强调:“我们所了解的科学是包含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产生中,政治介入学术表现得特别严重。
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在组成的理念上完全不同。中央研究人文组的院士是28人,过了五年时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委员就成了61人,是过去的两倍多。除了时代转换以外,学术并没有发展,而学部委员的人数却在激增。仔细观察又会发现,学部委员名单中除了人数增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强化了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构成中,除了顾及各学科的专业水平以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法学家在人文组院士中有较大比例,有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四位院士。到了学部委员时,这四位法学家中(王世杰、王宠惠去台湾)留下来的周鲠生、钱端升都没有成为学部委员,也就是说,1955年科学院学部建立以后,代表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机关中,已经完全没有法学的地位。
一般的理解是1955年学部建立的时候,中国已经取消了社会学和法学,所以原中研院院士陈达也不是学部委员。
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这样理解,1949年以后,中国高层不但没有法治观念,更没有对法治的敬意;当时取消法学和社会学的一个理由是有了马列主义,其他的知识体系就不需要了,这个判断中隐含着对知识体系的无知和自负,也是一元化知识逻辑的必然结果。知识体系中取消了法学、社会学,学部委员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再有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法学和社会学的恐惧,可能还不仅仅是一个无知的问题,而是垄断对所有复杂社会现象解释权力的一种选择,这也是专制社会对知识的一般态度,法学更不能例外。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此有一个解释:“社会科学即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例如制造Symbolique暴力的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解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
一般社会科学的命运如此,法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