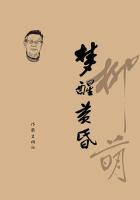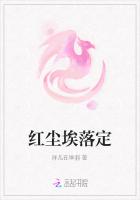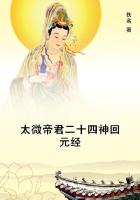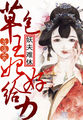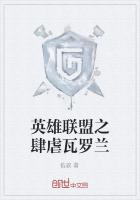现代学者研究《古诗十九首》时注意到古人“比兴”解诗的现象,朱自清在《古诗十九首释·前言》中谈道:“有些并不根据全篇的文义、典故、背景,却只断章取义,让‘比兴’的信念支配一切。所谓‘比兴’的信念,是认为作诗必关教化,凡男女私情、相思别离的作品,必有寄托的意旨——不是‘臣不得于君’,便是‘士不遇知己’。”马茂元在《古诗十九首探索》中也谈道:“解说《十九首》的往往把屈原《离骚》‘以求女喻思君’的表现手法移植过来,产生许多误解。”曹旭将《古诗十九首》研究的第二阶段归为“以‘比兴寄托’的方法注解《古诗十九首》,以元代刘履的《古诗十九首旨意》等专书为代表”【1】。对于教化性比兴解诗,朱自清认为是“断章取义”,马茂元也称此法会产生“误解”,大多持否定的看法,而曹旭认为“‘比兴’释诗是一种创造”,“多了一个角度,也多了一个法眼”。是“创造”,还是“误解”?对于《古诗十九首》的“比兴”解读肇始于何时?为什么自唐至清,教化性比兴解诗占据主流?其现象背后有什么深层的原因与意义?本书回溯《古诗十九首》的阐释史,力求在比兴的源起、发展和演变的历时性结构系统框架中,对《古诗十九首》“比兴”解诗现象作一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评估。
第一节 ”比兴”钩沉
“比兴”乃中国传统诗论中一个重要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2】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为“六义”。先秦时期的“六诗”或“六义”中,“赋比兴”往往是作为诗歌表现的艺术手法,是先秦对《诗三百》创作经验充满灵性的体悟。同时,在先秦,“比兴”一开始就介入以“讽喻”为目标的“赋诗、引诗、用诗、教诗”等“诗教”活动,如孔子《诗》论中“兴、观、群、怨”(《论语·阳货》)、“兴于诗”(《论语·泰伯》)等。“兴”这种“引譬连类”【3】的独特阅读方式,成就了孔子对《诗三百》文本政治、道德及伦理含义的解读,从而凸显了《诗经》文本的政教功能。古典美学的“以物比君子之德”更是肇始于孔子。《礼记》曾记载子贡向孔子提出君子为何贵玉的问题,孔子认为,玉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大、地”等“九德”,实质上是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道德赋予玉,即玉成为“道德附身”之物。汉朝的刘向在其《说苑》卷一七一中也记载了孔子以水比君子之德的观念,在孔子看来,水具有“仁、义、智、勇、察、包蒙、善化、正、度、意”等多方面的品德,其中“善化”即仁德,“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水被赋予道德伦理的内涵。孔子对《易经》的解读正是在这种“以物比德”的观念下展开的。
“比兴”,特别是对兴之内涵的解释,在中国诗学发展中向来是异彩纷呈的,但也因此常常是“缠夹”多义的,其原因就在于对“比兴”的解释未能清楚地区分作为形式阐释的审美比兴与作为内容阐释的政教比兴【4】。两汉时期,郑众和郑玄对比兴的解释,奠定了后来“政教比兴”与“审美比兴”两个比兴系统的基础。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孔颖达《毛诗正义》引)。纯粹从修辞学角度,他认为“比”是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则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他强调的是“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审美特点。郑玄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孔颖达《毛诗正义》引),将比兴跟政治、教化、美刺内容联系起来,重视阅读批评所达到的政治教化作用。诗歌创作与阅读批评具有一定的逆向同构性,萧华荣先生曾指出:“其实在汉代,比兴不仅是创作中婉转曲折的传达方式,也是解诗中婉转曲折的解释方式。”【5】之后,在中国诗学史上,创作与阅读批评都关注比兴之法,但“审美比兴”与“政教比兴”交错发展,文学原则与伦理原则扭结在一起,因而造成某种程度的矛盾与混乱。
郑众的“托事于物”、刘勰的“起情附理”【6】、皎然的“取象取义”【7】、李仲蒙的“索物触物”【8】、朱熹的“此物彼物”等诸说,不外乎“物象”之与事、情、理之间如何关联及关联的内容。从根本上讲,“比兴”乃是一种思维方法,其根本特点在于引譬连类的联想。从思维结构上讲,比包含此物与彼物即喻象与喻体两项,两者之间有类的相近的属性,联想的方向有一定的逻辑解释基础,容易把握;兴也包含此物与彼物,但此物与彼物通常通过“感发”而至,联想的方向更随意,更难把握。因而,刘勰有“比显兴隐”说。朱自清认为后世“比兴”连称,“兴”往往就是“譬喻”或“比体”的“比”【9】。比与兴都追求言在于此,意见于彼,有所寄托。因而,在诗歌创作与阅读批评中常常“比兴”合为一词,即追求言外之意的寄托。
诗歌形式的解读与内容的阐释,对于读者来说同样重要,而且相辅相成。对读者来说,更注重政治伦理原则的社会价值还是文学原则的审美价值,决定其对诗歌意旨体味的不同层面与方向,我们可将之区分为“社会功能派”与“审美鉴赏派”。经学家重视诗歌内容的教化作用,完全是“社会功能派”,重在传诗、解诗时运用“比兴思维”引导大众将“引譬连类”的方向往政治教化层面延伸。诗论家重视诗歌创作技巧,重在指导诗人如何运用“比兴思维”创作诗歌,达到婉曲含蓄的诗歌之美。显然,不同的是诗论家们又可分“社会功能派”和“审美鉴赏派”。
持“审美比兴”说的主要是诗论家中的“审美鉴赏派”。一般认为在“文学自觉”的魏晋时代,“言情”五言诗发达,“政教比兴”显然跟不上文学创作的步伐。“言意之辨”的玄学理论成果经刘勰、钟嵘、殷璠及后来唐宋时期的司空图、严羽等一大批诗学理论家的努力,与赋比兴理论尤其是“兴”的理论汇流,“审美比兴”系统在形而上的层面得以发展。后世之诗歌审美理论如“滋味”说、“兴趣”说、“兴象”说、“神韵”说、“性灵”说、“境界”说等大都在“审美比兴”基础上发展而来,并影响着中国诗歌的创作与欣赏。大而化之地来说,魏晋南北朝与元明时期“审美鉴赏派”占据主流,两汉、唐宋时期“社会功能派”引领文坛,而清代呈现出的是两种学派汇流与交融的景观。
“社会功能派”的“政教比兴”,包括经学家与诗论家两方面。“政教比兴”肇始于孔子的解《诗》,形成于汉儒经学家的《诗经》阐释,是汉儒传诗、解诗的重要方法。在解诗的过程中,汉儒们往往将诗中的“草木鸟兽”等自然物象寄托政教风化、美刺讽谏等义理,对诗进行政治、伦理、道德的隐喻,深掘其中的微言大义。自汉以后,宋儒(理学家)、清儒(朴学家)更发展了汉儒的政教比兴之说。不仅经学家,历代复古思潮中(尤其唐、明清时期)坚持复兴儒家诗学政教精神的诗论家和诗人们,均将“比兴”的方向引导向政治教化层面。如唐宋期间,伴随着唐初陈子昂、白居易的复古与新乐府运动,“政教比兴”得以提倡并发展。特别是白居易从儒家诗学立场出发,提倡“风雅比兴”、“美刺比兴”,在创作上,诗人们接受了《毛诗》以男女比君臣的象征意义,明确地以“政教比兴”思维进行创作,如白居易的《新乐府·太行路》小序明确地说主旨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李商隐也说过“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力均声同,德邻义比”。如果说唐代的“政教比兴”侧重于对诗歌创作的指导,那么宋代的“政教比兴”则侧重于对诗歌的阅读欣赏。宋人继承了汉儒“政教比兴”说诗的传统并推至词的阐释,如刘克庄以比兴寄托来评词,在《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一文中评曰:“叔安刘君落笔妙天下,……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所谓“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即借草木以寓情志;“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即借男女以寓托君臣大义。清代,常州词派更将“比兴寄托”发展为一套解读词的理论。张惠言以儒家“诗教”论词,以治经之法解词,倡“意内言外”、“比兴寄托”,求“微言大义”。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说:“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明清之际,通过对“比兴寄托”传统更进一步反省与共同体认,诗坛各种诗学观念异彩纷呈,“性灵”、“神韵”、“格调”、“肌理”等学说各显其趣,审美比兴与政教比兴也都得以发展。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侧重于审美比兴,而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则承接政教比兴,认为政治伦理价值优先于审美价值。其中,翁方纲认为诗人所感发之情应是“天性忠孝”之理,所托之物应为经典书籍;沈德潜也主张比兴,他说:“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咏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约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10】尽管沈德潜强调诗歌的审美价值,但又认为诗歌所托之物应用以表现忠君爱国思想,其社会伦理价值是诗歌的最终旨归。总的来说,“审美价值”与“社会伦理价值”在清代得以广泛检讨,经学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但同时也认识到诗歌独特的“审美比兴”的特点;诗论家们在“审美价值”与“社会伦理价值”的权衡中各有主张,但将“审美比兴”与“政教比兴”都纳入他们的创作与阅读批评视野,如冯班认为“诗以讽刺为本,寻常嘲风弄月,虽美而不关教化,只是下品”【11】,将政治道德作为评诗的最高标准。在清代,儒家诗教传统得以复兴,“政教比兴”思想被用于指导诗歌的创作与阅读批评。
朱自清曾将古代比体诗概括为“以古比今、以仙比俗、以男女比主臣和以物比人四类”【12】。其中,“以夫妇譬君臣”模式成为古代诗歌阐释的一道耀眼风景。这一模式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时代赋诗、引诗、用诗时的“微言相感”、“断章取义”,即含蓄地以男女关系象喻霸主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到汉代,以夫妇譬君臣的阐释策略一方面源自《毛诗》的阐释,如《邶风·谷风》、《周南·关雎》、《陈风·衡门》和《小雅·伐柯》等以男女关系比附君臣关系的具体阐释实践;另一方面,王逸在《楚辞》注中开始将自然物象与政教意义的对应关系具体化、系统化。其《楚辞章句》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比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此处,王逸连举六种典型例证予以说明“夫妇譬君臣”模式。其后魏晋至唐,大量的诗歌创作有意识地以“男女譬君臣”,特别是由《楚辞》发展而来的“求女喻思君”模式指导创作,大量以女性口吻写作的诗歌往往寄托着男性诗人怀才不遇、知遇君王以及政治理想抱负等。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说“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佞,比兴之义也”。唐代杜甫读元结《春陵行》,和诗一首说“不意复见比兴体制”;杜甫用“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来评价元结的《春陵行》、《贼退示官吏》二诗;白居易称杜甫的《石壕吏》等有“风雅比兴”之意。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说:“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元代杨载的《诗法家数》曰:“古人凡欲讽谏,多借此以喻彼,臣不得于君,多借妻以思其夫,或托物陈喻,以通其意。但观魏、汉古诗及前辈所作,可见未尝有无为而作者。”清人方世举在《兰丛诗话》中谈道:“比兴率依《国风》之花木草虫,《楚辞》之美人香草止耳。愚意兼之以《周易》彖爻,《太玄》离测,尤足以广人思路。”【13】署名唐代贾岛的《二南密旨》更为具体地阐释物象与政治伦理的关系,用君与臣之关系比喻诗家与物象之关系。其中,在“论物象是诗家之作用”的条目下有这样一段话:“造化之中,一物一象,皆察而用之,比君臣之化。君臣之化,天地同机,比而用之,得不宜乎。”在“论总例物象”的条目下,又强调说明各种物象与君臣、贤臣、君子、小人之间的比附关系。僧虚中的诗格书《流类手鉴》中,列出五十五类物象的象征比兴义,从而使得“夫妇譬君臣”这一诗歌创作与诗歌解读最强有力的武器得以系统化、模式化。
朱自清在《比兴·比兴论诗》中认为:“系统的用赋比兴或‘比兴’说诗,朱子《楚辞集注》是第一部书。”“系统”一词在此的限定意义很重要,实际上“比兴”解诗可以溯源至孔子对《周易》、《诗三百》的研读。《易》之爻辞多乃远古的歌谣,可以说是诗歌雏形。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下》中认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在《易》、《诗》之“述”中,孔子表达了其一套以“仁”为核心、“君子”为人格典范的儒家思想,奠定了后世比兴论诗的伦理基础。《易传》中的“以象比德”,即将易象作“君子小人之德”的解读。《论语》提出了一套学《诗》、用《诗》的方法与理论,其中,“兴”是孔子具体诗歌教学实践中读诗、写诗的体悟与总结,孔子的这些诗论深深地影响着汉代儒者,导致汉儒注《诗》独标“兴”体。六朝文论家注重对诗歌“审美比兴”的总结,钟嵘在《诗品》中解释道:“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比兴”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诗学方法,更在于它揭示了中国古代诗歌“含蓄委婉”这一最基本的审美特征。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篇区分了“比体”与“兴体”,冯班在《钝吟杂录》中评曰:“千古区分比兴二字,莫善于《文心雕龙》。《比兴》篇云:‘比者,附也;兴者,起也。……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较之康成,尤圆通不滞。”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认为“彦和辨比兴之分,最为明晰”(《文心雕龙义证》),但其在宗经思想下扬兴体、贬比体,并认为汉代辞赋“比体云构”、“兴义销亡”,失去了《诗经》的政教价值。宋代理学家朱熹以审美形式区分了“赋、比、兴”的内涵,更明确地提出“兴体”与“兴物诗”的概念。《朱子语类》中载“《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又曰:“‘兴’之为言,起也,言兴物而起其意。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皆是兴物诗也。”【14】此外,朱熹更有一套“夫妇君臣说”,即以男女人伦关系喻比君臣际遇关系的政教比兴内容说。可以说,朱熹清晰地区分了审美比兴与政教比兴这两个系统,并具体地运用于《楚辞集注》。在宋代之后,“借男女以寓托君臣大义”的比兴说诗之法成为一种潮流,如元代刘履的《选诗补注》受朱子《楚辞集注》的影响,有意识地直接以“赋比兴”系统来释“义”。其中,刘履着力之处是运用比兴这一诗歌表现手法,延伸比附“君臣关系”,并特别强调诗中合乎“温柔敦厚”这一诗教传统之处。陈沆在《诗比兴笺》中也自觉而明确地以教化性比兴解诗。清代,魏源在《诗比兴笺序》中说:“以笺古诗‘三百篇’之法,笺汉魏、唐之诗,使读者知比兴之所起,即知志之所之也。”(《诗比兴笺序》)冯舒的《家弟定远游仙诗序》认为“诗无比兴,非诗也。读诗者不知比兴所存,非知诗也”【15】,并从创作与阅读两方面将比兴提升至诗之本质的认识。吴乔更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解诗的两种方式——“比兴诗”与“赋义诗”,提倡“比兴诗”,同时坚持比兴的解诗方式,并将其上升为诗歌诠释的普遍原则。至此,教化性比兴解诗方法发展成为一套公式化的诗歌阐释模式。
第二节 《古诗十九首》经学阐释史回顾
《古诗十九首》的阐释主要依附于《文选》以及历代古诗选本而传播,直到清代方独立为显学,出现大量评、说、解、笺注等专著。纵观《古诗十九首》的历代阐释情况,自唐代至清代将《古诗十九首》意旨作“臣不得于君”、“忠人被逐”、“士不遇知己”的阐释一直占据主流。伴随着这种“比兴”解诗的过程,《古诗十九首》逐渐强化了其道德伦理、政治教化意义。
唐宋两朝崇尚《文选》。唐高宗之后,诗赋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文选》作为当时士人学习诗文的主要范本,遂逐渐上升至科举教科书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唐代“文选学”兴盛,其中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当属唐高宗时代的李善注本,其后是唐玄宗时代的五臣注本。对《古诗十九首》的最早阐释来自唐代李善的《文选注》。“时谓宿儒”(吕延祚《进五臣集注文选表》)、“通儒”(四库馆臣)的李善以互文阅读思维,注《文选》重在字词的训诂,直接揭示诗文意旨的较少,但经学传统中的微言大义、比兴思维亦时有渗透。这种政教比兴的阐释是零星的、片段式的,多渗透在词句渊源考证或征引文献中。例如,他对《行行重行行》中“浮云蔽白日”一句的注释为:“浮云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毁忠良。故游子之行,不顾返也。”然后,列出《文子》、《新语》、《古杨柳行》为证。其对《西北有高楼》的注释为:“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达,知人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居也。”
由于受过唐玄宗的褒奖,五臣注《文选》【16】盛行于当时。在宋代,李善注、五臣注单行本又被六臣注逐渐取代。《古诗十九首》六臣注本的出现,缘于李善的“不解文意”,读者难以直接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六臣注有其宏观意识,对诗文意旨有总体的把握和各句内容的直接揭示,常常在第一句的笺注中揭示整首诗的基本精神,同时在字词训诂的基础上注重句意的把握。作者虽未以“赋比兴”标注,但其中“喻”、“刺”、“托”解法的运用则是儒家政教解诗的直接体现。《古诗十九首》六臣注本中,作者的思妇、游子身份首次被直接置换为臣、忠人、贤人和士等政治身份,诗中的物象也顺应诗之意旨进行定向的阐释,其意旨自然阐释为“臣不得于君”、“忠人被逐”、“士不遇知己”。例如,其论及《行行重行行》时说,“铣曰此诗意为忠臣遭佞人谗谮见放逐也”;在《青青河畔草》下注“铣曰此喻人有盛才事于暗主,故以妇人事夫之事托言之”;《今日良宴会》注“向曰此贤人宴会乐和平之时而志欲任也”;《西北有高楼》的注解为“翰曰此诗喻君暗而贤臣之言不用也”;对《迢迢牵牛星》的解说是“济曰以夫喻君,妇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为谗邪所隔,亦如织女阻其欢情也”;对《东城高且长》注曰“铣曰此诗刺小人在位拥蔽君,明贤人不得进也”。总体而言,六臣注《古诗十九首》的第一句注释中先对整首诗的意旨进行揭示,同时在词句的解释中将诗中物象以君臣关系、君子、忠臣、贤人、小人和佞人等进行比附,如“芙蓉芳草以为香美,比德君子也”(《涉江采芙蓉》);“娥娥美貌,纤纤细貌,皆喻贤人盛才”(《青青河畔草》);“城可以居人,比君也,高且长喻君尊也,相属德宽远也,逶迤长远也”(《东城高且长》),等等【17】。据统计,《古诗十九首》中,以“忠臣、贤人、小人、佞人等君臣关系”进行政教内容解读的诗歌包括《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迢迢牵牛星》和《东城高且长》共六首。
自唐代以来,《文选》一直是士人阅读的经典。至宋元时期,《文选》地位骤降,但《古诗十九首》的诗学地位丝毫未动摇,更成为学诗的准则与规范。宋代汪晫曾有诗句:“秪作古诗十九首,不消柱史五千言。”【18】南宋文天祥在《文山集》中更独推崇“选诗以十九首为正体”【19】。特别是理学古诗的范本——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及刘履的《选诗补注》,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阅读古诗的重要范本。元明时期,研究《文选》的学人不多,但刘履的《选诗补注》至今有存本,而且颇受当今研究者重视。刘履的阐释方式不同于李善、五臣注的笺注式阐释体例。李善的“比兴”解诗采用零星渗透法,五臣注则直接置换其抒情主人的身份;除注解集中在篇末外,刘履受朱子《楚辞集注》的影响,选诗与注解都有朱熹理学诗学的痕迹,尤其是有意识地直接以“赋比兴”系统来释“义”。在他那里,作为诗歌表现手法的比兴,被用于延伸比附“君臣关系”,凸显“十九首”契合“温柔敦厚”这一诗教传统之处。曹旭先生认为,刘履的《古诗十九首旨意》是以“比兴寄托”方法注解《古诗十九首》的代表,并进一步指出以“比兴寄托”的方法注解《古诗十九首》始自五臣注。刘履本人也在《风雅翼·选诗补注》中谈到,其对意旨的解释“大抵本之‘五臣旧注’,曾原演义,而各断以己意”【20】。在阐释理念上,刘履遵循《诗经》的风雅传统,以尊经思想为指导,往往在篇末强调其合于儒家的诗教传统。比如,他在《行行重行行》注解后面指出,“见弃如此,而但归咎于谗佞,曾无一语怨及其君,忠厚之至也”;评价《青青陵上柏》“不失性情之正者欤”;对《青青河畔草》则指出“以倡女为比其深得诗人托讽之义欤”。据统计,《选诗补注》十九首中独标注“赋也”九首,“兴也”一首(《青青陵上柏》),“赋而兴也”一首(《明月皎夜光》),“比也”四首(《西北有高楼》、《迢迢牵牛星》、《凛凛岁云暮》和《孟冬寒气至》),“赋而比”两首(《行行重行行》和《东城高且长》),“兴而比”两首(《冉冉孤生竹》和《青青河畔草》)。
《钦定四库全书》中收录明代叶盛所撰《水东日记》,其中提及(日记第二十四卷)当时人对刘履注古诗的看法:“祭酒安成李先生,于刘履《风雅翼》常别加注释,视刘益精。安成李先生者,李时勉也。其书今未之见,然时勉以学问醇正,人品端方,为天下所重。诗歌非其所长,考证亦非其所长。计与履之原书,亦不过伯仲之间矣。”
作为朱熹理学诗学的产物,《文章正宗》与《选诗补注》都具有浓重的理学意味。无论释义还是选目,都“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顾炎武《日知录》)。刘履的《选诗补注》在明代得以广泛传播,除明代杨慎质疑其以“君臣治道”解诗的“此何理耶”,认为其“所见寡陋”外【21】,明代曹安在其《谰言长语》中云“古诗为上,刘坦之选诗补注可法”。明代著名文学家胡应麟认为,刘履的注释是比较好的本子:“刘坦之《选诗补注》虽稍溺宋人,其论汉、魏、六代及唐,剖析深至,亦似具只眼者。”(《诗薮》)由此可见刘履《古诗十九首旨意》在明代的影响。
明代以前,特别是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以诗赋和儒家章句取士,使得《古诗十九首》的阐释与儒学的理学思想相联结。这一时期,《古诗十九首》的阐释主要以《文选》、《选诗补注》的政教比兴“释义”为主。明代以后,各类新型的鉴赏及汇评性的古诗选本开始出现。与主要作为科举教材课本的《文选》不同,古诗选本不仅具有诗歌范本的功能,同时编选者还通过对作品的鉴赏及汇评,传达推广自己的诗学主张。尽管许多论诗仍保留着明道宗经的名义,但实际上已不同程度地向文学审美敞开。即《古诗十九首》的阐释体现出由“释义”为主转为注重诗歌审美欣赏的特点,如竟陵派陆时雍的《古诗镜》以情解诗,强调《古诗十九首》之“托”的运用:“所谓托者,正之不足而旁行之,直之不能而曲致之,情动于中,郁勃莫已,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故,其言直而不讦,曲而不洿也。”“《十九首》谓之风余,余谓之诗母。”此处之“托”,可理解为审美意义上的“比兴”之法。随着评点体的兴盛,诠释形式也受到了影响。在评点类著作中,篇、章、节的意旨与审美特点的揭示多在相应部分以眉评、文末评或夹评方式标注,语言极其简洁、精练。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孙月峰的《文选》评点。在《青青河畔草》首上眉评曰“盖刺小人诗”;对《行行重行行》中“思君令人老”句,孙评曰:“是妇忆夫诗,以比君臣,妙处似质而腆,骨最苍,气最炼。”这种点评对诗歌潜藏意旨的揭示极为简洁,但也以“比兴寄托”和“美刺”诗教观为出发点。
清代,《古诗十九首》已成为独立的显学。除《文选》阐释(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古诗选本中对《古诗十九首》的诠释(沈德潜《古诗源》、王夫之《古诗评选》、张玉谷《古诗赏析》、方东树《昭昧詹言》)外,还出现了大量的专书或专论,如刘光贲的《古诗十九首注》、张庚的《古诗十九首解》、朱筠的《古诗十九首说》、饶学斌的《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姜任修的《古诗十九首绎》都具有代表性。尽管诸家的阐释特点各有不同,但以比兴释义,强调其儒家诗教“政教功能”的阐释仍为主流话语。
在儒家诗教观念下,清代阐释者探求“游子思妇”的“情中之理”,关注“比兴”、“寄托”之“道”、之“义”、之“理”。如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以意逆志》篇中主张“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他将“意”解释为儒家典籍的思想内容或意义,即通过典籍的思想内容推求作者的原意。【22】出于尊经的目的,吴淇最后得出的论断是“诗不合圣贤之旨不传”【23】。吴淇在《古诗十九首定论》中认为,“十九首”在内容上“要皆臣不得于君而托意于夫妇朋友,深合风人之旨”。朱筠在《古诗十九首说·总说》中提出:“诗有性情,兴观群怨是也。诗有寄托,事父事君是也,诗有比兴,鸟兽草木是也。……叹《十九首》包涵万有,磕着即是。凡五伦道理,莫不毕备。”在具体篇目的阐释中,由物象之比兴,寻其寄托,由情入性,最后常常归于“真得三百篇遗意”(《行行重行行》)、“如此言情,圣人不能删也”《涉江采芙蓉》)、“数语中多少婉折,风人之笔”(《冉冉孤生竹》)等。朱氏在总说之最后还特别指出:“此等诗不必拘定一说,正不可不为之说,……吾愿学诗者从此入手,忠臣孝子,亲友节妇,其性情皆可从此陶铸也。”【24】朱筠对古诗中社会政治伦理意义的强调是清代儒流的共识。钱大昕在《古诗十九首说序》中称赞朱氏的解说,认为“十九首者,三代以下之风雅也,读后山之说,使人油然有得于‘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意,其亦古诗之功臣而足裨李善诸家训诂之未备者乎?”徐昆在《古诗十九首说序》中也认为:“每说诗,辄以十九首为归。……贯经史,括情事,……移我性情矣。”
张庚的《古诗十九首解》同样采用教化性比兴解诗的思路,如《行行重行行》的阐释“此臣不得于君而寓意与远别离也”;《青青河畔草》的解释“此诗刺也”;《涉江采芙蓉》的诠释“此忠臣立心”;《庭中有奇树》的阐释“此亦臣不得于君,而托兴于奇树”;《冉冉孤生竹》的诠释“此贤者不见用与世而托言女子之嫁不及时也”。此类诠解可谓典型的经学阐释。
“男女比君臣”的阐释模式在清代被普遍接受。虽然方东树、张玉谷等人的阐释有所突破,强调“说自己话”,不必“深于义理”、“动关忠孝”,提倡创作个性的多样化,但仍然强调诗歌的政治伦理教化功能。方东树在《通论五古》(《昭昧詹言》卷一)中认为,“夫论诗之教,以兴、观、群、怨为用。言中有物,故闻之足感,味之弥旨,传之愈久而常新。臣子于君父、夫妇、兄弟、朋友、天时、物理、人事之感,无古今一也。故曰:诗之为学,性情而已”【25】。而张玉谷的《古诗十九首赏析》在提示古诗主旨时,也将教化性比兴作为解诗的一种方式,如对《古诗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主旨的提示“此自伤婚迟之诗,作不遇者之寓言亦可”,对《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主旨的提示“此怀人者托为织女忆牵牛之诗,大要暗指君臣为是”,皆属此类。
第三节 ”比兴”解诗的价值与意义
诗歌的经典化过程是一种效果性的历史,各不同文本都有其独特的样式。通过对《古诗十九首》经学阐释史的梳理,我们发现:《古诗十九首》这种具有民歌意绪、乐府音韵并经过无数文人润色的优美诗篇,其内容表达的是人生失意、朋友阔绝、死生新故等俗世情怀。自唐至清,阐释者们将其作“臣不得于君”、“士不遇知己”的阐释一直占据主流,甚而形成一种“独断”。在“历史选择”的过程中,这种阐释证明比别的诠释更得到官方的青睐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如张庚的《古诗十九首解》在1736、1796、1850、1851、1911、1936、1987年被一再刊印(据国家图书馆资料),显示了出版界、学界和政界对其阐释的普遍认同。以现代眼光看,这种阐释是一种“误解”。在马茂元的笔下,“误解”一词是一个负性的评价词语。“误”者,谬也,狂者之妄言也。但这种“误解”为何能穿透历史的厚障而存在?其合理性与有效性何在?
首先,“误解”的合理性在于学术发展本来就包含一定的合理性“误读”。
“误读”理论是近几十年来文本阅读理论的热点。在阐释学、现象学和接受美学等众多理论看来,“误读”现象是文本阅读的常态,现代学者有意识地将“误读”现象在理论上目的化、价值化和合法化。作为一种理论的“误读”的首倡者当推美国耶鲁大学的著名理论批评家、解构主义大师哈罗德·布鲁姆。在其一系列理论著作如《影响的焦虑》、《误读地图》中,他明确提出作为文学理论的“误读”这一术语,并系统地阐述了“诗的误读”理论,认为“人们在阅读文学经典时常常以自己的想象参与了再创造的活动,而阅读文本时失控的变化和个人的审美体验势必影响对原文的‘正确’理解,于是便导致了‘创造性误读’(Creatively Misreading)”,他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在这一“误读”理论下,他关注的是创新焦虑中诗人们对于前辈先驱者的误读。在中国古代,孔门说诗的实践和春秋赋诗言志的大传统左右着主流诗坛。不论是先秦原儒“诗言志”的命题,抑或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诗》无达诂”的论点,在立论的前提中已经包含着对《诗》的“断章取义”式“误读”、“误用”,埋下了“误读”现象合理化和合法化的逻辑伏笔。这种出于政教目的,为建构封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而建立和发展的中国式“误读”理论,同样敞亮了诗歌文本意义的多元性和阐释空间的丰富性,但“误读”实践在得到理论总结的同时也被推向极端。因此,意大利当代符号学家、小说家艾柯提出了“过度诠释”问题。他认为:“说诠释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26】艾柯强调文学阐释不是无限的,实际上,一些诠释的确比另一些诠释更合理或更有价值。但怎么判定哪种解释更合理或更有价值?艾柯求助于“文化达尔文主义”,认为在“历史选择”的过程中,某些诠释自身会证明比别的诠释更能得到认可,正如经典形成需要时间来印证一样,好的、有效的诠释也要靠时间来检验。因为正是在历史的不断“误读”中,经典文本相对确定的内涵与价值会意外地沉积和凸现出来,成为相对获得认同的“独断阐释”。按照艾柯的说法,“历史选择”就已凸显和证明了《古诗十九首》“臣不得于君”、“士不遇知己”等比兴阐释是合理的、有效的误读,是更有价值的误读。
其次,经学时代权力话语运作下的有意“误读”。
历史为何作如此选择?其深层原因何在?“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27】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实在”找寻“历史理解的实在”就不难发现,《古诗十九首》的这种阐释乃经学时代权力话语运作下的有意“误读”。冯友兰指出“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也”,自唐代至清代,《古诗十九首》阐释的历史语境“与一切学术都依附于经学”这一现象完全吻合。经学是文学无法挣脱的主流源脉,从“五经”到“十三经”,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一直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王权的合法性基础而发挥作用。比兴解诗本身就是儒家诗学传统中解诗的一种重要方法,是儒家政教精神在诗学中的反映。比兴解诗来源于“诗言志”的《诗》学观念,成就于“微言大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诗无达诂”的解读理念,促成了中国诗学传统中特有的重“诗教”、“载道”、“教化”的诗歌批评传统,有效地将儒家政治伦理文化投射到文学解读的深层结构上。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其权力话语理论中提出:“视历史为话语的构造,在话语及历史所标志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些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是阐释者运用权力话语进行“价值判断”后“被动地建构起来”的。从阐释者的身份看,历代有影响的阐释者,李善、五臣、刘履、吴淇、沈德潜、王夫之、张庚、朱筠等,大都是兼士大夫与文人双重身份于一身,有些更是“通儒”或经学家,文苑之人望,处于握各朝之文柄的地位。因此,自然地维护儒家诗学传统,将夫妇置换为君臣伦理的有意误读,均来源于其本然的知识结构与观念。他们既是权力的拥有者,又是话语空间的占有者,因而,这样一种权威误读顺理成章地演变成公共误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独断”解读。同时,《古诗十九首》经典地位的确立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考试制度密切相关。从《古诗十九首》的历史传播途径来看,“萧统《文选》不仅使《古诗十九首》有了集体的名字,并进入了教科书和官方传播的主渠道”【28】。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古诗十九首》主要依托《文选》而传播和流布。“《文选》烂,秀才半”的民间俗语,反映了《文选》已成为国家教育机构确定的教科书。《古诗十九首》原本是下层文人俗世情怀的抒发,但是纳入官方文化教育系统就必然得到完全不同的阐释,从而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工具。文本意义的阐释必须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念或旨趣,方能被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进而被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比兴解诗现象出现在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特别是“由教育体制来传承并构成了主导意识形态中不可或缺的那些文学艺术作品”,即作为“正典”【29】的文学作品,如《楚辞》、杜诗、李商隐的无题诗等。一般而言,这些“正典”代表的是文学正统价值观念,承载着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
再次,比兴阐释模式的价值转义功能。
栾栋先生在谈到比兴的诗学特点时,从两个方面阐发了虚实相生的灵趣。一方面,“比兴拟体,涵养万类。比兴为用,奇正参同。比兴为诗,体用合一。比兴入理,情亦附丽”,这是说比兴在诗学方面兼体用而涵万类,融情理而合齐正。另一方面,他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其孕生“多种误读”的可能:“比之所向,意象多样;兴之所至,志外有志。比兴解诗,难免迷离。连类无穷,误解有之。”【30】这里所说的误解,是指比兴本身就包蕴着丰富的误读设定。“误解有之”,恰恰也是比兴作为诗歌创作的精妙所在。栾栋先生对比兴理论“误解潜能”的发掘,发人深思。超越诗歌文本浅层的词句训诂,探究言外之意、蕴外之蕴,从而把阐释与理解引向深入,应该说这是对传统比兴说有益的思考。当我们翻检“比兴”说的历史,“误解有之”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线索。
从唐宋至明清,比兴阐释模式由实践到理论逐步完善。元代钱惟善在《韩诗外传》中称之为“断章取义,有合孔门商赐言《诗》之旨”,朱熹则认为“解诗多是类推得之”。“义”之所得,由“断章”到“类推”演进,是“生硬牵强到合理比附”的进化过程。从先秦到晚清的两千多年中,数不胜数的阐释者通过“比兴”一词,将诗歌审美的艺术思维与政教的社会功能作了丰富多彩的嫁接。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阐释中,“知人论世”阐释模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该模式的特点是用历史信息将文本意义禁锢在其原初的历史或身世背景之中,导致这种文学的历史阐释具有封闭性。在知人论世的阅读中,诗歌文本意义简约为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该模式具有束缚甚至扼杀文学阅读审美性、主观能动性的一面,会使诗歌文本或多或少失去灵性。在历代《古诗十九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纠结于对其创作年代与创作者的考证,既说明这一强势阐释模式的必要性,也证明学者们被历史时空局限的无可奈何。反过来看,正是由于其创作年代与创作者的不确定性,历史阐释始终只是诸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其中“枚乘说”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而也为开放性的解读留下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与传统“知人论世”阐释模式比较,比兴解诗则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意义,“比”其所向和“兴”之所至,阐释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参与到《古诗十九首》的再创作之中。
《古诗十九首》之“夫妇譬君臣”的比兴解诗方式不是误解,而是阐释者有意为之的一种选择,一种系统化的误读。作为解读者“比”其所向和“兴”之所至,有其正当性与有效性。“比兴”解诗之“臣不得于君”、“忠人被逐”、“士不遇知己”的阐释,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个角度,一个法眼”,是诸种意义话语阐释的一种,凸显了《古诗十九首》的道德伦理、政治教化意义。在走向经典的过程中,《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被正统的诠释所选择,被主流诗学话语所认同,正在于其解读倾向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相吻合,同时也由于此种比兴解说方式可与审美诠释转接,至少可与纯文学阅读的另类语境通化。广义地讲,比兴作为诗学的手段兼目的(体用合一),其中之伦理比兴、政治比兴与审美比兴、界外比兴(如宗教超度及彼岸想象)都有相通互变之处。
以《诗经》为准绳来衡量《古诗十九首》,是将后者经典化的一种方法或策略,是用既成文学经典对可能经典或准经典的琢磨和玉成。《诗经》的锉刀程度不等地提升了来自民间或下层文人的作品,表现俗世情怀的《古诗十九首》因之被加工、润色,这组诗歌的地位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以提升。同样在此过程中,历代阐释者传承发展的比兴解诗模式,成功地将游子思妇转嫁为君臣关系,强化了政治伦理意义,打通了通往主流诗学语境的关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这种“误读”成就了《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人类需要给难解的审美理想寻找放飞的渠道时,总是迂回进入,曲径通幽。从纯审美的诗学立场看,这是“误解”;从人类理智的诡谲和诗化的谋略而言,这是兑换审美自由的门票,尽管“夫妇譬君臣”的比兴解诗方式可能会让读者感觉沉重。假如真正的作者地下有知,他们是遗憾?或是欣慰?也许兼而有之。既然《古诗十九首》巧妙地或者说阴差阳错地通过了层层权力关卡,成为传世的文学经典,那么“经夫妇,成人伦”这种“比兴”就不能够约束读者的理解与想象了。读者们的“比”其所向和“兴”之所至,有了另外的多种可能。《古诗十九首》所包蕴的其他可能性完全能够冲决被遮蔽、被封闭的隐在状态。当审美解诗由隐变显之时,政治伦理的解读就变成了学术舞台和欣赏园地的篱笆围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各有千秋,可也并非势若水火,政治伦理的解读既遮不住“红杏枝头春意闹”,也挡不住“穿花蛱蝶深深见”。
文学史永远是各种误读更替交错的历史,经典也会通过重新阐释而获得更新和解蔽。马丁在其《当代叙事学》中指出:“有两种因素有助于我们成功地发现新意义。一是那些将以前的文学束缚于其他文化语境的事实和成规的消失;二是允许我们积极地参与意义创造的解释成规是有助我们发现经典的现代意义。”【31】在经学时代终结后的现代语境下,比兴解诗模式将会继续成就新的“误读”。“误读”未有穷期。
注释:
【1】朱自清、马茂元:《朱自清、马茂元说古诗十九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7、60页。
【2】《周礼·春官·大师》,《周礼注疏》卷二十三,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
【3】《论语注疏》(卷十七“阳货第十七”)。何晏、邢昺解释“《诗》可以令人能引譬连类以为比兴也”。
【4】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中国诗学思想史〉导言》一文认为:“中国古代的比兴观可分为两种,一是比附政教风化的经学比兴观,始于汉儒解诗;二是被今人称为形象思维的美学比兴观,六朝时虽有所透露,但基本成熟于明代,李梦阳认为比兴是‘假物以神变’,可谓形象思维的同义语。”萧华荣对其来源语焉不详。
【5】萧华荣:《作为释义批评的“比兴”说》,《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
【6】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中认为“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7】(唐)皎然《诗式·用事》认为“今且于六义之中,略论比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关雎》即其义也”。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页。
【8】(宋)李仲蒙:“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故物有刚柔缓急荣悴得失之不齐,则诗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则不足以考情性,情性可考,然后可以明礼义而观乎诗矣。”见《致李叔易书》,转引自(宋)胡寅:《斐然集》,《四库全书》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1137页。
【9】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17~119页。
【10】(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11】白居易《玩半开花赠皇甫郎中》一诗评语。见二冯评本《才调集》卷一。
【12】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81页。
【13】(清)方世举:《兰丛诗话》。见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77页。
【14】黎进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70、2095页。
【15】(清)冯舒:《家弟定远游仙诗序》。见《默庵遗稿》卷九,《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16】(唐)李济翁《资暇录》:“世人多谓李氏注《文选》,过为纡繁,徒自骋学,且不解文意,遂相尚习五臣者。”(宋)苏轼《东坡题跋》卷二《题文选》说“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所谓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亦谬矣”。
【17】(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文选卷二十九》。
【18】《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四·康范诗集·别集类三》,《用尊字韵·寄胡约之》:“芙蓉红晚对高轩,何日论文共一尊。秪作古诗十九首,不消柱史五千言。一声南雁霜华重,连夜西风木叶翻。自叹须眉今白尽,复愁友道更昏昏。”
【19】(元)文天祥:《萧焘夫采若集序》。见《文山集》卷十三。
【20】(元)刘履:《风雅翼·选诗补注》卷十四,《四库全书》卷一百八十八集部四十一总集类三。
【21】(明)杨慎:《升庵集》卷五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本。
【22】(清)吴淇著,汪俊、黄进德点校:《六朝选诗定论》,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34页。
【23】(清)吴淇著,汪俊、黄进德点校:《六朝选诗定论》,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1、3页。
【24】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香港)1955年版,第61页。
【25】(清)方东树:《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
【26】[意]艾柯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页。
【27】[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页。
【28】曹旭:《朱自清、马茂元说古诗十九首·导言》。见《朱自清、马茂元说古诗十九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9】帕特里克·富尔瑞指出:“正典就是文化传承和机制确认的一套文本。”Patrick Fuery et al.,Cultural Studies and Critical 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9.转引自江宁康:《文学经典的传承与论争——评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与美国新审美批评》。
【30】栾栋:《诗说》讲义。
【31】王先霈、王又平:《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