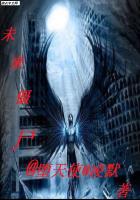毋庸置疑,外公的天花板顶门上被外婆用萝卜直接修了一个蒙古包,工期之快效率之高就是美利坚速度也望尘莫及。
蒙古包不大不小,刚好在他的眉毛与发际线的夹角地带占了三分之一区域。这是由大量毛细血管出现渗漏造成的,就像经常漏水的城市给排水管网在大街上形成的天坑一样,不同的是那种天坑一般都因为地心的引力而将肿胀面掩人耳目地长到了地下。
它的规律在这儿不适用,因为外公的高钙质颅骨绝对不会允许将那个肿块反向长到他的颅腔以内。如果真出现那种情况,那可就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了。
外公的恼怒程度可想而知,他揭竿而起,为了他即将步入的富人生活而向一直被贫穷欺压的残疾生活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开始张罗着准备休妻,写离婚协议书,找律师代写状子,状子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休妻驱妇,一部分是控诉犯罪,他将前一部分丢给外婆,而将后一部分搞了个复印件送给了我爷爷。
这两份状子发出后很快就收到了意相想不到的结果,首先是逼得外婆不得不为了顾全大局做出牺牲,打算从此对他俯首称臣。其次是爷爷那边为了息事宁人赶快派出了媒人。
媒人来的那天晚上,外公正在外婆的亲自护理下将两只几个月都不洗一次的脚放在热水盆里有滋有味地一边吐烟圈一边享受。媒人进门后,我外公为了将自己置于居高临下的地位,故意怠慢着将脚放在盆子里不拿出来。他头也不抬地凌空给媒人扔过两支带把的香烟,舌头后面像拉着李元霸的八棱锤似的拖泥带水地问:“过来啦?”
媒人是我爷爷的亲哥哥,他见外公那种姿态俨然是个鬼见愁,就知道今天这事不太好拿捏。他来的任务很简单,满打满就七个字:一稳二拖三砍价。松绑以后的意思就是:先稳住外公,不要激怒,以免他心血来潮控制不住一怒窜到法庭上去;其次尽量谈,谈不成就再谈,再谈不成就想办法拖,拖一天算一天,在这里时间就是金钱;最后再转弯抹角地努力砍价,最少得砍去三分之二,否则就是爷爷家现有的几口人全都给了人贩子也筹集不够。
媒人是鸭子被赶着上架,兄弟家摊上了事情,做哥哥的这时候就是这里的少东家,他不出面让谁出面?托别人不是不行,就怕运气不好碰上个嘴长耳短之人,事情成不成且不说,别到时候被他一张风箱一样的嘴,风花雪月地将家里那点丑事扬得像早春的柳絮似的满天飞,还没等上到法院自家就先输了大半截,那就得不偿失了。
媒人头重脚轻地刚刚坐好,正想着怎么与外公这种难缠之人打交道,忽听他问就顺口答道:“唉、嗯、是的。”
外公挺直接:“准备得怎么样了?”
媒人干咳了两声,掏出火机将他扔过来的烟点燃狂吸了两口,然后将浓浓的烟雾吐出来罩住自己不安的脸庞,想了一下就对外公说了一句文不对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