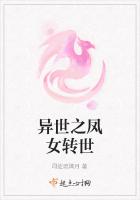媒体在报道“孙志刚事件”时,可能还没有“公共新闻”理念的指导在其中。媒体的报道、公民的行动虽然不具备普遍性,但还是在舆论的主流声音下取得了成功。这表明,媒体不仅仅需要客观性的报道,在公共事务上,媒体在公共领域的介入和对民众的引导能极大地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同样,在这样的例子中,是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大多数普通的公民的公共意识只停留在言语上,很少有行动上的表示。那么,“公共新闻”理念的引入及其实践在我国公民公共意识的影响是从哪方面体现的呢?
就如任何实践都需要行动的空间一样,“公共新闻”在中国的实践也取决于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出现,而这种出现准确地来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和政治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媒体的功能由单一的宣传功能向信息传播功能转变,媒体也逐步走向市场,民众的声音表达不再是一种奢望,“公共新闻”的实践也就有了适当表达的平台。
那么,“公共新闻”对公民公共意识的影响体现在何处呢?首先,“公共新闻”提倡公民在公共事务上的参与。就如泰德·格拉舍教授强调的那样,将受众作为公民,作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公共事件的)牺牲者或旁观者。在传统的新闻学理念中,受众是无意识或被动接受意识的,没有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原来的民生新闻是把受众定位为老百姓或大众,而公共新闻是公众,公众本身的内涵比大众应该说更具有某种社会含义,特别是公共新闻突出的一些民权的问题,突出公众的权益的问题,这个理念是对民生新闻的提升。”[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
倡导公民的参与,事实上就是肯定了公民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在传统的党政新闻中,媒体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媒体在告知受众发生何事时,在新闻报道中大多采用媒体视角、媒体话语,而公众在媒体这个公共领域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即使是在近几年的民生新闻潮中,由于媒体对百姓生活的关注,使部分人乐观地认为公民的话语权得到了回归,但实际上,这种话语权的回归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大多出现在家长里短的市井生活中,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民众话语权回归的本质是媒体为追逐收视率所采取的手段。当媒体、民众过于关注社会新闻,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时,政府和民众的沟通渠道就会被阻塞,公共领域的矛盾无法得到及时完善的解决,就有可能导致公民公共意识的觉醒在萌芽状态即被抑制或扼杀,更谈不上在公共事务上的参与。
从传播学的角度说,大众传播效果依其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构成的变化,属于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属于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这些变化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即成为行动层面的效果。[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从认知到态度再到行动,是一个效果的累积、深化和扩大的过程。“公共新闻”提倡公民的参与,实际上是对作为公民的受众在行动层面上的鼓舞,或者说更能起到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公民在这样的参与过程中,不仅获得了其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的媒介传播权、知晓权、媒介接近权,更重要的是在公共事务得到解决后,提供给其他观望者一个信息:民众唯有自己行动起来才能争取到自身的权益。如《1860新闻眼》报道了一则有关马上人行道的新闻,它不局限于新闻事实的报道,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一则滑稽新奇的社会新闻或者民生新闻,而是采访了相关的部门和法律专家,并且设置了问题:马究竟能不能上马路?利用现代手机媒体短信方式吸引观众参与讨论,有一万多名观众参与其中,63%的观众认为不可以,37%的观众认为可以。观众的探讨也愈加深入: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合法的吗?闹市骑马是否侵犯他人的公共空间?许多观众建议,既然立法上有欠缺,就该将这条明确写入法规。节目的客观效果是,观众争相去查阅交通、防预、市容等各类法律文件,试图找出骑马者合法或不合法的依据,立法部门则开始研讨有无必要将之写入法规。如果该栏目只是将其作为一则社会趣闻加以报道,那么这一万多公民就很难去思考“马能不能上马路”会涉及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也很难会想到法规方面的问题。也是因为他们的参与讨论,使立法部门开始行动。正是该栏目倡导公民的参与,使公民的公共意识在参与中觉醒并不断地延伸。“公共新闻”倡导公民在公共事务上的参与,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平台来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
其次,“公共新闻”实践中,媒体具有“组织者”的作用。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在1901年5月《从何着手?》一文中曾提出,“报纸不仅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冯健:《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近些年,随着新闻界一系列的改革,国内许多媒体都注重在报道上的组织策划。如《新京报》持续关注圆明园防渗工程,并发表多篇专家文章,讨论防渗工程的同时,也对圆明园的管理乃至文物保护进行了探讨;在北京计划取消公交月票的报道上,《新京报》更是委托一家调查公司进行民意调查,又发表许多评论员文章,探讨如何借鉴其他城市取消月票的经验。但是,国内媒体很少主动关注尚未被提上政府议程的话题,也很少发动和组织大范围公民参与的讨论,而更加注重权威人士的意见,在问题的解决上也缺少具体的方案。许多媒体对公共事务的报道,更多的是一种深度报道,缺乏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其中的热情。
作为公民的受众,虽然规模巨大,但分散、异质,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无组织性。在公共事务上,公民试图影响的对象——政府,却是一个庞大的力量中心,是一架有系统的暴力机器、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强制力量,面对这种整体的组织力量,分散的公民是无能为力的。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媒体,完全可以在公民与政府之间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本身强大的技术力量和舆论力量,将公众组织起来,就公共事务与政府进行对话,而同时这种对话也是政府所希望的,因为一个国家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是公民。国内著名学者孙旭培将“公共新闻”概括为: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张恩超:《公共事务比凶杀案更吸引: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南方周末》,2004年11月6日。]从他的概括中,笔者发现,媒体的组织作用是贯穿其中的。由于媒体掌握着大量的信息资源,兼知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情况,因此“公共新闻”理念要求媒体关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鼓励、组织公民广泛参与,以实现政府、媒体、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共同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
根据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的“议程设置功能”假说,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也就是说,大众传媒虽然不能决定社会大众“怎样想”,但它可以告诉人们“想什么”。根据这个假说,我们可以预想一个这样的事实,媒体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在增加,在公共问题上的组织讨论愈加频繁,而且公共问题在政府、媒体、公众的研讨下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么公民的公共意识会因为“媒介的议程设置”得到提升,那样,公民公共意识的培养就不会停留在假说层面,而会是不变的事实。
地方媒体可以更好地实践“公共新闻”
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如果从中央到地方,千人一面地讨论同一类的问题,而有些问题并不是该地区公共领域内急需解决的,那么“公共新闻”理念的实践难免会流于形式和模式化,并不能真正起到培养公民公共意识、解决公共事务的实际作用。地方媒体因为在地理和心理上的接近性,更容易引起公民的参与欲望,使沟通和互动成为可能,而且当地的公众因为地理上的接近性对公共事务有更高的认知程度,讨论问题更具有针对性,更能形成有效的沟通,对公共问题的解决也更具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