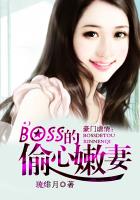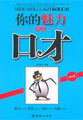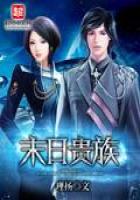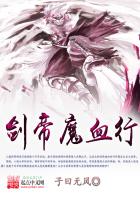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考虑
在二战结束后,国家战略安全利益是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美国插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这个利益。美国对台、对华政策的制定,总是与其远东政策和全球战略紧密联系。中美紧张对峙、中美缓和乃至建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受这一因素的影响十分明显。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军事力量极度膨胀,力图推行全球霸权政策。为遏制苏联,美国曾企图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之中:“美国的安全利益要求将中国置于苏联的控制之外。否则,亚洲所有地盘都完全有可能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之中。”美国担心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会使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美国政府曾一度试图离间中苏关系而暂时采取了“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剧了美国反动势力对新中国的敌视。因此,美国打出了遏制中国的“台湾牌”。
美国支持台湾的目的在于:一是企图在政治上遏制共产主义。这首先是由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对外政策的原则决定的。二战后,美国推行全球霸权政策,从当时来看,能够对其形成制约的力量主要来自苏联及其影响下的人民民主国家;其次是由美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造成的,它不单是美国反华势力的主张,而且是美国一府两会及不同党派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它表现为扶蒋反共,与前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在新中国成立后,它表现为西化、分化,并把台湾作为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政策的重点。二是在军事上,把台湾作为美国的附庸。台湾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通向太平洋的门户。这种重要的战略地位表明,控制了台湾,就控制了中国的一个重要出海口,也有利于向北控制日本和向南震慑东南亚地区。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借机采纳了麦克阿瑟视台湾为“不沉航空母舰”的战略分析,派遣第七舰队直接侵入台湾海峡。从此,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最大的争议问题和斗争焦点。三是在经济上,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海外贸易开通航道。美国控制台湾,是以表面上不侵占中国领土的方式,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开辟市场提供方便,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不断向亚太地区拓展。
在观察美国媒体的时候,必须注意到他们的“公正”、“客观”、“自由”理念后面所包含的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从根本上说,美国资产阶级控制的美国主流媒体的利益与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美国媒体必然要把资产阶级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所谓“民主”和“自由”,但如果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即使他们认为实际上某个国家并没有民主和自由,美国媒体仍然会忽略意识形态的差别,正面报道这个国家。
李希光、刘康在《美国媒体为什么总是消极报道中国?》中有如下叙述:
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28年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浪漫化,(20世纪)80年代的天使化和(20世纪)90年代的妖魔化三个阶段。
中国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在民主法制和个人自由上有进步,美国媒体对之的报道离中国的现实越远。究其原因,美国媒体关心的不是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社会开放和个人自由,他们的新闻价值标准只有一件东西:美国的利益。
1972年,当尼克松访华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高峰,很多基本人权正遭到严重践踏,但是,尼克松带来的那一大批记者对这些根本看不到,也不做报道。他们关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浪漫而神奇的世界:自行车,针灸,大熊猫,长城,故宫,人民公社,讲道德守纪律的人民,富有异国情调的蓝色海洋(毛式服装)。
进入(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刚刚对世界打开门缝,允许私人雇一个工开一个小饭馆,允许年轻人跳迪斯科,妇女留披肩发,穿牛仔裤,超短裙,这就不得了了,中国在各方面都是个好孩子。简直没有任何毛病,跟邪恶的苏联帝国相比,中国简直就是一个天使。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五大后,中国全面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连续多年保持8%的增长率,个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允许各种规模的私人经济,并把保护私人经济写进了宪法。但对这些,美国媒体多半视而不见,他们眼中只有不同政见者、达赖喇嘛、“台独”、赤字、政治献金、卫星技术泄密、盗窃核武器技术和民族主义妖魔。
一位西方记者是这样描绘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演变过程:
在(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他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采访动物园,看大熊猫”;
在(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他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迪斯科舞厅”;
在(20世纪)90年代,他一下飞机,对翻译说:“带我去见不同政见者。”
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美国媒体要浪漫化和天使化中国,把中国当成乖孩子和好孩子?事实上,在苏联解体前,特别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前,美国媒体把中国的确看成最乖的孩子了。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富·斯密司在回忆当时的美国电视画面时说:“瞧,一打开美国电视,就会看到,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成为美国人了。”
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美国把中国当成“好孩子”,因为当时有苏联的存在。正如一个美国老学者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指出的,“当时,我们出于自私的原因,希望中国在军事上强大,以对抗苏联。”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罗马尼亚在今天的美国人看来是个绝对的极权国家。但是,美国舆论的唯一标准历来都是国家利益第一位。由于他们发现齐奥塞斯库与苏联保持一定的距离,美国政府和舆论极力扶持齐奥塞斯库的政府,直到被推翻。红色高棉(20世纪)70年代在柬埔寨的极端行为早为中央情报局和媒体所闻。但是,当时,美国媒体对此却无兴趣去追究波尔布特的“种族灭绝的罪行”,相反,为了对抗越南和苏联在那个地区的扩张,中央情报局和媒体分别给予红色高棉军事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和同情。而今天,它却摆出了一副要把红色高棉残余引渡到美国审判的国际道德警察的架势。
诚如这篇文章所言,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纽约时报》甚至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服道札记”,由一位记者每天评述尼克松的访问。这些文章告诉美国人说,中国人十分有礼貌,乐于助人。而在实际上情况决非如此,这无疑不符合美国人历来对“自由”和“民主”的推崇。当时美国媒体对此视而不见,而是大谈发展美中关系的重要性。这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美国遏制苏联、联系中国的国家利益的需要。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美国人开始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否会在某一天像前苏联一样挑战美国利益,威胁美国安全。这种担心使得“中国威胁论”一个时期以来在美国社会甚嚣尘上。不论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夸大,还是对中国军事意图的猜疑,“中国威胁论”的作者们都流露出对中国动摇美国支配地位的担心。美国外交的一以贯之的基本目标就是,防止任何一个除自身以外的大国在亚洲或欧洲处于支配地位。现在,一些美国战略分析家环顾世界后,把中国当作了可能的对象。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一位华裔官员曾对他的中国朋友说,美国对华的根本战略目标是:在苏联垮台以后,不允许有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为此,美国媒体寻找种种证据,给中国罗织罪名。报纸上一会儿断定中国国防费用不透明,一会儿指责中国扩充武库,一会儿说中国威胁台湾。这就是美国媒体在台海问题报道上不遗余力地抨击大陆的主要原因所在。
美国学者约瑟夫·斯特劳布哈尔(Joseph Straubhaar)和罗伯特·拉罗斯(Robert La Rose)认为,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到越南战争再到水门事件,经历了从“趴儿狗”(lapdog)到“看门狗”(watchdog)再到“攻击狗”(attack dog)三个角色的转变,这一概括相当形象也相当准确。“水门事件”以后,特别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已经转变成了第四个角色,即“牧羊犬”(sheep-dog)角色。
当前,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也不情愿卷入台海冲突,这是现阶段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美国需要以台湾制约大陆,用大陆牵制台湾,既不能让局势失控,又不时制造两岸对立,从鼓动李登辉访美、敦促美国政府对台出售武器到抨击大陆《反分裂国家法》,美国媒体始终秉承美国的国家利益。
当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瞬息万千,随着美国对中国利益需求的增减变化,美国媒体对大陆的批评也会因之变化:美国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方面有求于中国时,对大陆的批评就会适当减少;美国不需要中国时,美国媒体对大陆的批评就会持续增加。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分歧
美国社会的“开放”、“多元化”和“言论自由”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美国的政治词语中,“意识形态”一词常常含有贬义,通常表示一种偏狭的信念,因而在美国往往用“价值观”、“信念”、“精神”、“气质”、“理想”、“信仰”等词来取代“意识形态”这个词。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不重视意识形态,但实际上,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特别是在媒体中无孔不入,美国媒体所标榜的新闻自由和客观公正原则背后更深层次的是关于自由、人权、个人主义、法治、基督信仰等隐性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体系。在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欧洲白人的价值观,即强调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为自由和幸福的最大威胁。
美国的意识形态根植于一种“自由”的个人权利观。这一核心理念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人眼中的世界只有两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以美国的敌人为代表的“邪恶”世界,而美国的使命是要“捍卫自由世界”和“消灭邪恶势力”。
美国传媒和学术界主流把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主流意识形态描绘为普遍的意识形态,主张与非美国的意识形态对峙,抵制和围堵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在其国际报道中,美国媒体绝对是以意识形态划线,跟政府保持一致,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强权政治服务。以台海问题报道为例,大陆是一个与美国迥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美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根本对立,使中国无论怎样融入国际社会,都不被美国公众接受,特别是冷战后,美国媒体一有机会就攻击中国。美国媒体多年来的负面宣传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形成了敌视中国的思维定式和偏见,较少关注外部世界的美国公众受到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美国媒体的左右。
意识形态在美国媒体中非常普遍、无孔不入。欧洲白人的价值观在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价值观倡导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是对自由和幸福的最大威胁。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决定着新闻记者观察世界的能力和角度。记者们无论如何努力地力求客观,仍将受到他们所坚定不移地奉行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国际事务报道中,美国媒体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在国内事务报道中更加突出和明显。
长期以来,美国人判断别国“好坏”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该国是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长期冷战思维的影响,又使美国人视共产主义为“自由、民主”制度的对立面。冷战结束以前,前苏联就是共产主义的代名词。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就成为了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仇恨的对象。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美国媒体把中国塑造成一个改革的先锋,正在偏离共产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在美国媒体上的形象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并严重影响了之后数年的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与冷战有关的国际性事务成为美国外交的中心议题,也是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这种思维是西方至上的文化价值观的表现,是一种不自觉的、更具隐蔽性的思维定式。当美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或危机时,这种思维定式表现得尤其明显。媒体被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所左右,与美国政府及其外交政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体现出鲜明的倾向性,而不会站在“无派别”的中间立场上“客观”地报道事实。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经常将中国与“大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色中国”、“独裁政府”甚至是“邪恶帝国”这些充满敌意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在看待中国时,可以说美国媒体时时不忘“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对立。这种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把持美国媒体的“社会精英”阶层心中,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