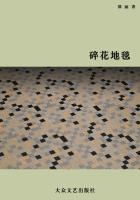阿三阿四把乐慧夹在当中,走着走着,挤作一堆。阿三搂着乐慧,给她递烟,乐慧把烟圈吐在他脸上,阿四一个劲儿恭维她的眼睛。
进屋,关门,上锁。乐慧在床边稍坐,两个男人进隔壁房间,压着嗓子谈论什么。过了一会儿,阿三先出来,问:“你累吗?”
乐慧答:“还行。”
阿三过来解她衣服。
两小时后,乐慧要走。
“不要,不让你走。”阿三在门口拦她。
乐慧留了一晚。三人一张床,折腾个没完。乐慧只想冲把澡,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再次想走。阿三阿四不答应。又在床上躺一天。乐慧浑身发粘,下体疼痛,感觉没意思透了。
到了晚上,乐慧尖叫着,大半个人倾出窗外。阿三掐灭烟头:“滚吧,小婊子,老子玩腻了。”
乐慧从楼梯上折回去。阿三将乳罩从门里扔出:“稀罕啥呀,你有胸吗?”
走了一段,发现不对劲,探手一摸,乳罩里被吐了两口痰。想找他们算账,又在兵营式的新公房间迷了路。只好打的回去,却发现牛仔裤口袋里的七百块钱没了。
乐慧走到家,两腿发颤,站立不稳。开灯时吓一跳。
“你回来啦?”
“嗯。”毛头瓮声道。
“啥时候回来的?”
“刚到。”
“噢。”乐慧松了口气。
脱掉鞋,把钥匙放在柜子上,猛灌一大杯水,又问:“怎么就睡了?才八点。”
“不舒服,可能感冒了。”
乐慧打开浴室龙头,又跑出来:“我刚才嫌闷,出去转转,看了个电影。”
毛头蒙着头,不应声。等水满了,乐慧坐进浴缸。洗了许久,还是感觉脏腻。擦干出来,躺到床上,毛头仍然面朝墙壁。乐慧让他匀点被子,他把被子全推过来。
“电影好看吗?”毛头问。
“一般般。爱情片,哭个没完,结局大团圆。”
乐慧睡不着,毛头呼吸平缓,乐慧知道他也没睡着。
“我很想你。”乐慧道。
又补充道:“真的。”
过了一会儿,乐慧趴到毛头身上:“老头子,干嘛不理我?”
“发烫,喉咙难受。”
“给你拿药。”
“不必。”
乐慧掖上被子,琢磨这个“不必”。似乎冷淡,又像真的病了。
第二天乐慧醒得早,发现床上空着,阳台也没人。她像被砸了一下,脑子闷闷的。潦草地抹把脸,开冰箱觅食,发现毛头买了很多好吃的:泡芙、巧克力、圈圈饼干……拿起一盒酸奶,湿乎乎的瓶底粘了一张收银条,日期打的是前天。
当毛头把收银条塞进马夹袋时,她正吐着烟圈,听人夸眼睛好看呢。乐慧浑身一凛,冲到门口。门被反锁了。她呆了一会儿,进厨房拿菜刀。第二下时,菜刀被弹歪了。乐慧觉得腿上一热,一摸一手鲜血。她找了件棉布衬衫,胡乱扎了腿,跑到窗口,朝下看了两眼,坐到窗子上,两腿对准底楼的雨棚,屁股往外一挪。
乐慧感觉被撑挡了一下,左肩和后背一记闷疼,人就在地上了。她一瘸一拐到路边,好不容易喊住一辆出租车,搭着玻璃窗道:“我付双倍的钱。”司机略一迟疑,乐慧打开车门。
白椅罩被染红了,还在凹槽里聚出一个小血塘。司机骂骂咧咧。乐慧掏出一把钞票,扔在副驾驶座上,司机才住嘴。
乐慧花了七八分钟,从弄口走到家门口。又花了七八分钟敲门。“乐鹏程,死出来,快死出来!”隔壁开了条门缝,甩出一句话:“你老头住院了。”又嘭地关上。
乐慧止了血,吃了消炎药,休息一晚。起床后找隔壁邻居。邻居道:“那天有个你爸的同事,找不到你,在我这儿留了医院和病房号。”
乐慧失了血,觉得脑筋不好使,转了半天,才找到那间病房。站在门口时,恰听护士吆喝:“手别抖,你抖,我怎么戳得准。”往里一探头,瞧见正在换输液瓶的乐鹏程。
邻床的老头道:“老乐,老乐,是不是你女儿?”
乐鹏程被护士挡住视线,闷闷地“嗯”了一声。他脸色蜡黄,下巴瘦得尖出来,眼睛的形状也变了。护士瞅着乐慧道:“家属?”不待回答,就转身走了。邻床老头道:“你爸没人照顾,吃苦头了。我儿子请了看护,烧菜烧饭的,我就分点给老乐。”
乐慧问乐鹏程:“什么病呀?”
“胃出血。”
“上次见你还好好的。”
“连着几天大便发黑,突然就路上昏倒了。”
“好象挺严重。”
“那是,”乐鹏程闭起眼睛,“死了也没人管。”
乐慧掖了掖他的被角:“我不是来了嘛。要吃东西吗?”
乐鹏程点点头:“不要太油腻。”
“那就烧点粥。”
“医院有小灶的。”
乐慧问附近哪有超市,就去了。乐鹏程的眉眼舒展开来。他对邻床老头道:“我女儿手很巧的,什么都会做。以后出院了,请你来吃饭。”
老头道:“好,好,一定。”
乐慧煮好粥,洒了肉松。乐鹏程执意要老头品尝,老头分了小半碗,喝一口,赞道:“香喷喷,韧笃笃。”乐鹏程呵呵一笑。老头道:“女儿来了,你终于高兴了。”
乐慧整天待在医院,煮粥、端便盆、给乐鹏程读报。她让自己忙一点,就顾不上七想八想了。乐鹏程几次说:“阿慧,以前不知你这么好。”热泪盈眶,还试图握住乐慧的手。乐慧觉得他可怜兮兮,像条狗。五十天后,乐鹏程出院了。乐慧让出大床,自己睡沙发。她烧菜、清洗、喂药、整理房间、接待乐鹏程的同事。乐鹏程能起床了。乐慧渐渐有了空闲,那个她努力不想的问题,又摆到面前。
乐慧相信,她和毛头没完,但怎么个“没完”法,却不晓得。夜晚漫长得犹如疾病,来时骤然降临,去时却似抽丝,一寸一寸,没个尽头。
一次半夜,乐慧起床小便,外间铃声骤响,乐鹏程接了,“喂”一声,又“咦”一声:“怎么不说话就挂了。”
乐慧猜是毛头打的,翻来覆去到凌晨,忍不住打毛头手机。那头不接。一晚无眠,清晨感觉头疼,胃难受,浑身发冷。乐鹏程烧完饭,热好隔夜菜,问她吃不吃。乐慧不答。乐鹏程自己吃了,给她留一碗。乐慧迷糊了一会儿,听见电话铃响。乐鹏程说:“大概是阿二师傅。”接起,听了,转头道:“你的。”乐慧蹦到电话旁,“喂”了一声。对方也“喂”了一声。各自沉默。
片刻,毛头道:“上午没带手机。”
乐慧问:“昨晚你打的电话吧。”
“没打过。”
又不说话。片刻,毛头轻轻掐断电话。
乐鹏程问:“阿慧,你和那个民工怎么了?”
乐慧抱着话筒出神,然后又拨过去:“那天干嘛把门反锁?”
“哪天?什么反锁?”
“你误会我了。”
不响。
“乐鹏程病了,我回来照顾他。”
“哦。”
“真的。”
“哦。”
“乐鹏程,你是不是病了?是不是?”乐慧大声问,又回到话筒旁道,“你不相信就算了。”她挂断电话。乐鹏程递过一张纸巾,让她擦眼泪。乐慧不接,一骨碌翻进沙发,躺了几秒,又一骨碌坐起:“走,吃饭店去。”
“我吃过了。”
“吃过了也可以吃。你瞧那几根蔫菜,算吃过了吗。”
从饭馆回来,还没开门,就听屋里电话响个不停。乐慧冲进去,气喘嘘嘘地“喂”了两声。
毛头说:“你好。”
乐慧说:“你好。”
“干嘛去了?”
“吃饭。”
“算午饭还是晚饭?”
“午饭。”
“哦,这么晚呀。”
“还好。”
“你老头什么病?”
“胃出血,住了几十天院。”
“现在好点吧?”
“好多了。”
“胃靠养的。”
“嗯。”
“注意饮食。”
“嗯。”
等了十几秒,毛头又道:“多吃细软,粥之类的,养胃。”
“嗯。”
毛头又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