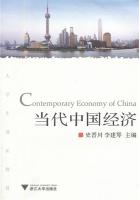我有太多的疑问需要贡献出来,这就是我理解的“献疑”一词的语义学含义。因此,这一部分文字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我恳请列位牧师能够给我以教导——如果没有真牧师,伪牧师也行。反正我已经分不清真假了。
不断减少的文字,但越来越多的问号……
1
古典中国素无“世纪”一说。自从船坚炮利的欧洲人强行敲开中国的大门,追随着鸦片、洋泾浜英语和太阳旗,作为概念的“世纪”也明目张胆地来到了神州大地,并以加速度的方式,很快在咱们炎黄子孙心中安了家、落了户。那个被庄子点化为“心斋”的玄奥处所,自此融进了异质物品。有点无可奈何,有点悲哀,也有点喜剧色彩——如果考虑到“世纪”带来的广泛后果的话。我当然没有能力确切地指出,“世纪”概念究竟是在何年何月取得了华夏户籍,但有一点我倒是敢担保:在“世纪”和“甲子”的对垒中,甫一接火,就以前者的大获全胜、后者的一败涂地而告终。尽管在相术手册上,在拒不“进化”的某些老农民口中,“甲子”还像虱子藏在穷人内裤的某个夹缝中一样存活,但毕竟只能算是苟延残喘而已。
在中国,刚刚过去的一百年因此被指认为“20世纪”。追随着“甲子”嬗变为“世纪”,古典中国的生活内容,也跃迁为专属于“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与社会。在摩登学者口中,这满可以被称作特定的“历史境遇”、特殊的“历史语境”。确实,同样是战争,但不同于垓下之战;同样是话语拼杀,但不同于陆九渊会朱熹于鹅湖;同样是谋杀,但不同于玄武湖之变;同样是水涝旱灾,但不同于乾隆年间的中原大旱、汉武帝或宋太祖年间的江南水患;同样是买卖,但不同于扬州八怪时期那些盐商们的行径、徽州商人故作姿态或潇洒自如的把酒临风;同样是向天空开炮,但不同于刘禹锡烟花爆竹迎新年;同样是痛苦,但不同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紧随着鸦片、洋泾浜英语和燃烧着的圆明园,拼命跟进的,是更加威力无比的“世界”。恕某不敏,没有能力指明那个叫“世界”的家伙究竟何年何月在中国人心中插队落户,但有一点我仍然敢担保:在“世界”和“天下”的肉搏中,刚一交手,我们念叨了数千年的“天下”,在我们祖先那里永远郁郁葱葱、永远水灵和沾满露水因而坚固无比的“天下”,顿时溃不成军、树倒猢狲散。尽管在我们的口头上,在我们的赌咒发誓中,还“天下、天下”叫个不休,但恐怕没有人不明白,那充其量不过是对古典中国的“天下”的拙劣模仿,不过是“世界”差强人意的同义词。何况所谓的“同义”也许并不成立。
追随着中国进入“20世纪”,中国又如此这般地被置入了“世界”之中,从此与“天下”无涉。同样是出游,但那个头戴纶巾手持鹅毛扇的人却走向了“世界”;同样是长江,但越来越浑浊的江水却流向了“世界”范围内的太平洋,而不是笼罩在“天下”之中的东海;同样的剑门关,但到来的是汽车,而不是陆游的毛驴;同样的泰山、长城,却迎来了来自“世界各地”而不是“五湖四海”的宾客;同样是“理”,却不再是“道理”“性理”,而是“真理”“法理”和“定理”……
“甲子”意味着循环,意味着团圆和圆圈,与“天圆地方”的“天下”刚好暗合。数千年来,它始终自给自足、怡然自得并怀柔远人;“世纪”意味着直线,意味着冲刺。它拒绝循环,只愿意与“进步”神话媾和并狼狈为奸,勇往无前,直到传说中的“天尽头”。“甲子”是圆形或倒梨形的子宫,“世纪”则是硬得笔直的阳具;“天下”是封闭的盾牌,“世界”则是随时都在待机而动、在睡梦中都在挥舞着自己的那根长矛。
此时此刻,天高野阔,星汉垂地。玩味着刚刚过去的一百年,那个填充了“世纪”之肠胃并让“世纪”圆满的一百年,我丝毫没有动用比喻的心情,更没有玩弄语言花招的癖好。我衷心赞同“天下”人无数个“甲子”以来都遵循的“修辞立其诚”。那是个伟大而辉煌的格言。在这里,我不过是想说,崇尚“天下”和“甲子”的人民,那些视圆圈和循环为上天之厚德的老百姓,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成为信奉“世纪”与“世界”的强悍者,更不可能成为那些强悍者的对手。所以,鸦片、夕阳残照下的圆明园废墟、南京大屠杀、三年“自然灾害”中生产出的累累白骨、“文化大革命”里的冤屈无告者……都有理由抗议:我本来好好的,凭什么假借“世界”“世纪”,让我承担如此结局?让我担待这样的命运?我听见惨死在“世纪”和“世界”刀剑下的冤魂,排着长队,在我的窗外大声吼叫……
2004年春节,我穷极无聊,躲在北京城南的一套陋室内,向臆想中的听众或读者,讲述了一个至今还没有推销出去的怪诞故事——那些专司出版的衙门告诉我,你的故事拙劣之极,根本就没有资格出版。就是在这个故事中,我杜撰了一个在全球地图上都查找不到的地方。它叫隆庆府,位于地球北部。按照我的虚构,隆庆府以盛产哲学家、酸菜、醋坛子闻名全地球。在故事中,我说完了这些添油不加醋的开场白后,马上调笑式地说到了欧洲,那个位于我们西边、以“远东”来称呼我们的“西方”:
学通史时,基本上都以“米利都的泰勒斯”来开篇。这只能证明:那些皮肤苍白的西方人既无知,又妄自尊大。大脑袋哲学家牛勇增就曾严肃地考证过,泰勒斯根本就不配成为全地球第一个哲学家,即使是他的著名学说“世界是睾丸组成的”,也不是他的发明。牛勇增说得很明白,泰勒斯的学说完全偷自隆庆府。而且他偷窃的还不是隆庆府最早的哲学,更不是最好的哲学。他偷去的只是隆庆府视若敝帚的玩意。听牛哲学家论证说,那玩意有点类似于隆庆府人民吃鸡时扔掉的鸡屁股。牛先生还有一个重要推论,特别值得转述:泰勒斯既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家,又是一个哲学小偷,因此全部西方哲学就都是盗贼的产物,盗贼的产物当然只能催生出强盗哲学。牛先生甩开膀子,动用了最先进的考古手段和思想侦破仪器,如此这般地操作了一番,终于挖掘出了强盗哲学的精髓:强权有理,偷窃无罪。季明生对牛氏的推理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并以一个小车司机特有的哲学语言,表达了对牛氏推理的高度首肯:“他(即牛勇增——引者注)把西方人挺着老二到处乱戳的秘密,全部暴露个球了。”
(敬文东:《隆庆府当代哲学小史》)
我也许并没有开玩笑,何况在2004年春节的恶劣天气中,我连开玩笑的心情都没有。实际上,季明生先生所谓“挺着老二到处乱戳”,考诸历史,正是“世界”和“世纪”本来含义。从最为宽泛的语义学角度来说,“天下”意味着“至大无外”,“世界”则意味着“我”与“他”;“无外”意味着所有人都可能是自己人,“我”与“他”则意味着我是我、他是他,一切都是那么汤清水白、利益清晰;“所有人都可能是自己人”意味着用怀柔的方式感化同类,“我”与“他”则意味着“我”对“他”必须进行武力征服、可以进行武力征服——反过来,“他”对“我”也一个熊样。为了和自己的时空主张获得一种类似于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效果,“天下”为自己配备了“甲子”,“世界”则为自己发明了拥有“乱戳”能力的“世界”。
“世纪”“世界”天然具有自产自销、强买强卖的禀性。它是强悍者,它是笔直者,它是“刺破青天锷未残”的长矛,它天然能找到买主,天然有能力把别人发展成为买主。谦卑的美洲、非洲、亚洲,还有我多灾多难的祖国,成了它最好的促销对象,成了铁蹄下的牺牲和祭品,并供奉在“世界”和“世纪”的神龛前。当然,它偶尔也打出广告,号召潜在的、正在被生产中的顾客,甚至以发展连锁店的方式,将这些顾客发展成自己的同类,让他们的心脏和“世界”“世纪”在同一个振幅上跳跃。
我没有在“世纪”“世界”修理中国人心性的进程中,看到过任何排异反应。或许它短暂地出现过,但在轰轰烈烈的“20世纪”,在“20世纪”的中国,大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一百多年来,无数唾弃“天下”“甲子”的中国人果断地选择了“世界”和“世纪”。他们被公正地看作具有“世界眼光”的“龙的传人”。在更年轻的中国人那里,我指的是在那些吃麦当劳、肯德基、汉堡包,看美国大片、读《苏菲的世界》和“廊桥梦遗”长大的中国人那里,“天下”和“甲子”只不过是比喻和梦痕。那些刚刚尿完中国炕的人,都毫无转折期地成了“世界”主义者、“世纪”的潜移默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本着“世界”和“世纪”的威风,想假借“世界”和“世纪”把中国拖进“世界民族之林”,却无意间和“世界”“世纪”上下其手、里通外合,继续摧残自己的同胞,而且手段花样翻新,比那些“乱戳”的家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则渴望着绿卡,梦想着大洋彼岸,希望有朝一日洗去“天下”“甲子”在自己基因中的残余。为此,他们都在不懈地努力。作为一个善解人意的犬儒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我衷心祝愿他们能够成功;但作为另一类中国人中渺小的一分子,我也愿意向前者提出申请:求你们高抬贵手,咱们都是炎黄子孙,你们那样做又是何苦呢?也愿意向后者提出建议:既然是基因,恐怕就没那么容易被洗去。
2
“世纪”革新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它不仅仅要求知古而鉴今,更要求面向未来、开创未来;“世界”则涂改了中国人的空间感觉,它不仅需要我们知道“至大无外”,还要我们明白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我们被称作“远东”,被指认为“东亚病夫”。我们的视野由此得到了全方位的更替。我们的鲜血、唾液,我们的肠胃、骨骼,我们的视线、灵魂,在“世界”和“世纪”的双重逼视下,得到了全面的更新。在整个“20世纪”,在中国,所谓时间,不过是一支向前飞驰的箭头,不过是一维的、线性的光阴;所谓空间,不过是分辨人我的度量衡,不过是标志异己的界碑。“天下”和“甲子”的时代,随着“世界”和“世纪”的广泛来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20世纪”的中国,飞驰的箭头既意味着现代化,又意味着在“甲子”定义着和定义过的地基上,现代化具有何种程度的紧迫感和结巴感;分辨人我的度量衡既意味着革命,也意味着在“天下”笼罩着的土地上,革命具有何种程度的复杂性和暧昧性。总之,一切都变了,时间改变了方向,空间更换了气流和密度,男人改变了发型,女人则换了睡姿……
与此同时,和“天圆地方”暗中吻合的许多方块字,也被迫改变了自身的语义。在这些旧瓶装了新酒之后的方块字中,“革命”是异乎寻常的一个。考诸历史,古典中国的“革命”,莫不始终在“甲子”派定的框架内循环往复。从秦至清,每一个因“革命”而鼎立的朝代,看上去都像一个大家族中的不同成员:从眉眼、腰身、挺胸、俯首到安心受射,竟然是如此相似;它们虽然各有韵味,但我们一眼就能断定,那些自己把自己命名为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的,确实是一母所出的兄弟,符合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比喻。但在“世纪”“世界”暗中怂恿或公开教唆下,“20世纪”的中国革命始终是现代化的严正要求。革命是现代化的助手或拐杖,现代化则是革命的终极目标。这当然是一种被迫的现代化、被迫的革命,它要求古典中国更换自己的血液,改变自己的骨髓,变更自己的灵魂。确实,这一切都来了,也都无一例外地被中国人做到了。
应和着一维的、线性的时间的旨意,应和着分辨人我的度量衡的严格规定,“20世纪”的中国革命始终在两个向度上展开:顺着线性时间的手指给出的方向,奔赴现代化,为此,需要一场旨在走出“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的时间革命;顺着分辨人我的度量衡的指引,去推翻一切异己的力量,为此,需要一场旨在保种求存,旨在维护本党、本阶级利益的空间革命。这两种革命都被恰如其分地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这些叫内涵的家伙,都来自“世纪”和“世界”或热得滚烫或冻得冰冷的枪管中喷射出的液体,也都更进一步地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的灵魂。
有鉴于“世纪”和“世界”的固有禀性,“20世纪”中国的时间革命始终是一维的、线性的,始终是一根向前挺进的长矛,尽管它步伐凌乱不堪,在广袤的时间雪地上留下了许多螺旋式上升的轨迹。但它无疑把“世纪”的语义更加直白化也更加肉身化了。空间革命则始终在划分人我:要么是民族的仇敌,要么是同胞;要么是本党、本阶级的异己,要么是同志。它当然性地将“世界”给丰满、浑圆了,它也因此给了“世界”一个或丰腴或干瘦的面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