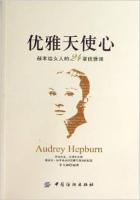第二天去红场拍摄,刚下车,就见一位年轻高挑的俄罗斯姑娘不停地四处张望,看见我们肩扛手提的一堆人,立马向我们走过来。有过前面的事,俄罗斯国家新闻局专门派出了工作人员陪同,这应该是我们使馆经过协调后的结果。姑娘刚作完自我介绍,一个体魄健壮的中年男人,长得很像施瓦辛格,穿一身便衣,站到了她的身边,姑娘说他是克格勃的。摄制组立马紧张起来,但中年男人脸上一丝微笑,表明了友好。我们在红场被允许拍摄一小时,这期间,这对壮男靓女始终保持着警惕,紧紧地跟随着我们。当红场拍摄接近尾声的时候,“施瓦辛格”居然提出让我们进入禁区拍摄列宁墓,这出乎我们的意料。他把我们领进紧贴着红场红墙的一个地方,向门口一位持枪的岗哨做了交代,就见那个岗哨“啪”的一个军礼,然后打开铁栏,让我们进去拍摄。这里,除列宁墓外,埋葬着逝去了的苏俄高官,都是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物。“施瓦辛格”介绍说,这里还有两位中国人,一位姓张,一位姓王,但是他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接着他又提议我们拍摄“长明火”,这是俄罗斯民众悼念无名英雄的一个地方。我们从列宁墓出来,经过一个安检口,一拐弯,就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正向无名烈士墓献花。一层层的鲜花围绕着“长明火”,非常壮观。伊戈尔说这些花都是俄罗斯百姓自愿献上的,每天都有人来,所以花永远是艳丽的。我不禁对俄罗斯民众产生了深切的敬意,同时对“施瓦辛格”的举动稍有困惑,因为从斯大林别墅的冷峻到红场的热情,毕竟是个大转弯,我又想到这一定是我们使领馆的功劳。
有趣的伊戈尔,在俄罗斯拍摄的外景所涉及的时间和区域跨度都很大。王稼祥在俄罗斯的历史,最早的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在我们寻访中,很多地址有的更名有的搬迁,这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拍摄难度。细心的老朱为我们特地找了一位俄罗斯司机,他就是伊戈尔,莫斯科人,今年50多岁。第一次见到伊戈尔时,他正认真地低头看地图,而事实上,他自己几乎就是莫斯科的一张活地图。他指指胸前的徽章对我们说:“我是老布尔什维克,选我当司机,算你们找对了人。但在莫斯科,谁也不敢说,自己认识莫斯科,因为莫斯科实在太大了。”他拿起地图说:“这个小圆圈代表城市的中心点,一圈有16公里。这个大一点的圆圈,代表城市,一圈要走60公里,你能说自己认识莫斯科吗?”眼神中流露出几分得意。
伊戈尔甚至知道克里姆林宫的最佳拍摄角度,哪座桥最适合拍摄莫斯科河,哪里有典型的俄罗斯建筑,哪里能拍到莫斯科全景,哪里的夜景最美。即便是王稼祥1925年就读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1928年就读的红色教授学院,伊戈尔也会毫不费力地帮你查找到。但当我问到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办公地,他却一脸茫然,说无论作为“老布”还是“老莫”,他均未听说过这个地方。言外之意,要么拆了,要么你们搞错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但这在我们片子的历史还原中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面包会有的,粮食也会有的。”说话的是随行的翻译小李,这是个热情而又机灵的小伙子,5年前来莫斯科留学,主修俄罗斯历史,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对我们这次拍摄,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除了翻译之外,也帮助我们查寻资料。见大家开始犯难了,小李马上拿起手机,拨通了他的导师——知名的俄罗斯汉学家的电话。汉学家只知道当年的办公地还在,但确切的位置无法提供。一个星期以后,伊戈尔开车带我们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幢三层的办公楼前停下来,然后神秘地笑着,大家十分诧异,他手一指:“微笑吧,这就是共产国际的办公地。”欢呼声随之而起。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罗高寿,“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前驻华大使、着名汉学家罗高寿见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采访罗高寿的地点是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的会客厅。这位中苏外交史上的传奇人物,有40余年的外交生涯,本名叫伊戈尔·罗加乔夫,连续出任驻华大使达13年之久,经历了不同时期的中国。
罗高寿第一次到中国是1932年,那时他才出生1个月。他父亲老罗高寿在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工作,也是汉学家,曾翻译过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鲁迅和老舍的作品,这对罗高寿选择研究中国问题和学习中文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包括他的中文名字罗高寿也是父亲传下来的。
提起亲身经历的中俄关系史,罗高寿谈兴特别浓。他说,自他1992年担任驻华大使以来,他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亲身参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起草。“我同中国同行多次讨论过这个条约的构想。在得到两国领导人的批准之后,我们在谈判桌上谈了很长时间,认真起草每一个条款。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他清晰地道出条约的签署日:2001年7月16日。
罗高寿告诉我:“我永远记得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的外交事件。回忆过去就会明白,如果多一些克制、善意和忍让,少一些教条主义,60年代初发生的许多问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两国关系蓬勃发展的时候,在各种会晤、访问的繁忙工作中,只要时间许可,我就会努力去感受中国的变化。我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京剧是我百看不厌的,最喜欢的是《三岔口》。”
谈起第一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罗高寿说:“王稼祥在中苏双边关系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任大使时,毛泽东也来了,他参加了所有斯大林与毛泽东、周恩来,还有其他领导人的会见、谈话。王稼祥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
毛泽东的手很宽阔很柔软——季塔连科,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博士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全俄汉学家协会主席和俄中友协主席。采访放在俄罗斯社会科学院远东所季塔连科办公室。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中国字画,其中一幅“俄中友谊,源远流长”的书法,最为醒目。会议桌上摆放着中国的工艺品,有景泰蓝花瓶、青铜编钟和兵马俑以及各种玉雕、瓷器和双面绣猫,还有赴俄罗斯访问的中国代表团赠送的纪念章和徽章。
季塔连科能说流利的汉语,尽管其中常常要夹杂俄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他告诉我们,他出生在距莫斯科约五六千公里远的一个叫做阿带的农村。在小学六年级时,也就是中国解放战争期间,季塔连科买了一张“世界政治地图”,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城市用红铅笔标出来,并把苏联广播和报刊的有关报道搜集起来,向同学们作介绍,于是就被称为“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季塔连科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苏联了不起。
我们从小就受到了系统的国际主义教育,所以一般老百姓对于国际问题都很重视的,中国革命是苏联人民最重视、最敬佩的事情。”
让季塔连科引以为豪的是,1957年和毛泽东握手的情景。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欢迎宴会,也邀请了苏联留学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和他们一一握手。季塔连科清晰地记得,毛泽东的手宽大柔软,周恩来的手握得很紧,刘少奇握手非常用劲,就像一把钳子那样,很有力量。说到这里,季塔连科不禁笑了起来:“回到宿舍,我们用毛巾把手包了起来,舍不得洗。”
“你是掌柜的”——齐赫文斯基,齐赫文斯基是世界上着名的汉学家,在俄罗斯有“学术教父”之称。初次见到他,也是在季塔连科的办公室。一件风衣让他显得很飘逸,手持一根拐杖,又显得十分精干。当老朱介绍我是《中国大使·王稼祥》的导演时,齐老冷不丁地用汉语说了句:“掌柜的。”
第二天,我们到齐老家采访。齐老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高知楼里,那是一座斯大林时期的建筑,看上去非常坚实,像这样的大楼,包括莫斯科大学和外交部大楼,整个莫斯科只有7幢。齐老住在9层,150平方米的房子齐老一个人住着,他的妻子和子女共8位亲人都相继去世了。他的家简直就是一个博物馆,收藏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品,最多的还是中国工艺品。正当我兴致勃勃地欣赏着这些艺术品时,齐老又冷不丁地说:“你是女人,你要招待客人。”我只好给每位来客斟上茶水。接着他又说:“现在我们可以开始采访了。”好像我是他们家的女儿,这种吩咐有种说不出的亲切。在齐老的回忆中,中苏建交时的细节和过程历历展现,我们像听大书一样听那些遥远而又陌生的故事,尤其是1949年10月1日他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苏联承认新中国的全过程。那敏捷的思维、清晰的表述、简练的语言,你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这是个93岁高龄的人。
“我是你们的朋友”——列多夫斯基,和齐老一样,列多夫斯基也迈过了93岁的门槛。根据我们的采访提纲,列多夫斯基竟然认真地准备了整整10页的稿纸。采访那天,他还特意穿上他当大使时的服装,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并且对我说,他要作一个发言,结束后你觉得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提问。
列多夫斯基是三四十年代苏联派驻中国的外交官。他亲历了解放后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交国书的全过程。
1949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担任一秘的列多夫斯基正从北平赶到南京。“5月24日,解放军过江,我们赶到江边,手中拿着小红旗,去欢迎解放军。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同志到南京来了,我们的中国同志。当时,他们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苏联人,就发生了误会,骂我洋鬼子(他做了一个滚出去的动作)。他们的敌人是美国人,所以看见白人都认为是美国人,洋鬼子,滚出去!”列多夫斯基笑起来:“我不是洋鬼子,我是苏联人,我是你们的朋友。”
莫斯科不仅是王稼祥心中的“赤都”,它在我们采访到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心中也永远是“赤都”。时过境迁,往事如烟,打开被时间尘封的历史,追寻王稼祥当年足迹的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个全新的俄罗斯。
送走俄罗斯摄制组,韩蕾突然找我,说吴建民办公室来电话,一星期后吴建民去法国参加国际展览局的一个会,她必须随行,要不就没有时间跟踪采访这位“国际飞人”。韩蕾面有难色,她知道,在一周之内要完成新闻采访所有的出国手续,这是不可能的。她说她问过外交部帮我们联络的官员,得到是同样的回答。怎么办?我和主编崔予缨直接冲到省外办主任那里,求他现场办公,竟然通过,又冲到外宣办如法炮制,竟然又通过,一关关,都是一盏盏绿灯。在出发的当天,韩蕾拿到了签证和机票,看了半天不相信。我说走吧,她还问真的假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中国大使》的如期完成是因为有很多部门和很多人的支持。
一周要办妥所有的因公签证,连外交部都说“没有过先例”,我就根本不抱任何希望了。当时我正在广州,没想到亚妮动用了所有“非常规应急预案”;崔予缨每天西装领带,鲜亮得跟新郎官儿似的,出没于政府各处室之间;做行政的陈大姐骑着自行车东一趟西一趟……奇迹就这么产生了!这四个字死活要送给亚妮:“神通广大”。
脸也没洗就去拍大使了
到戴高乐机场是当地时间凌晨5点,来接我们的司机小曲一看到我们就傻眼了,这么多设备!在机场门前大动干戈了好一阵子,终于把我们连人带设备像沙丁鱼一样罐进了他的罗孚车,把门顶牢。从大巴黎到小巴黎再到十三区,整个巴黎还在沉睡。我们先在酒店对面的“早点铺”里吃牛角面包,等着酒店的工作人员开工,因为我们到来的时间还太早。
这家酒店在中国可是大大的有名,Holidayinn(假日酒店),都是四星、五星的,可是在巴黎却很小很旧,还没有我们台对面的“银星”大;电梯很小,每次停时使劲一顿,我都差一点跪下去。为什么一进中国“档次”就高了?
终于等到服务员出现在小小的柜台后面,一问,要等到中午12点才能办入住手续,现在还不到8点!看着天边开始透出鱼肚白,我们决定先把不用的东西寄存,马上开工,去拍“巴黎的早晨”。
小曲把我们送到最近的一处标志性建筑——巴黎圣母院,刚刚露出头的太阳映照着哥特式的钟楼,塞纳河沐浴在晨光中,天空澄碧如洗,肥硕的鸽子悠哉地迈着绅士步,旁若无人地到处溜达,旁边就是着名的“左岸”……拍完这一组镜头,我们才突然感到特别冷,巴黎的早晨还是有一些凛冽的。
9点钟,我们到了位于乔治第五大道的中国大使馆,跟大使秘书和新闻处参赞落实好采访日程后,一问,赵进军大使正在楼上办公,便询问可不可以拍大使工作的镜头。新闻处的黄参赞感到很意外,因为知道我们刚到巴黎还没住下,没有采访安排。我说:“闲着也是闲着。”其实一天一夜了,我脸都没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