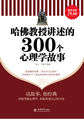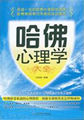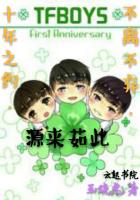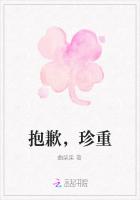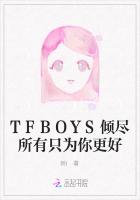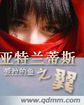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正念/觉知静心、现象学与认知科学互动的方法论核心。我们的建议是,改变反思的本性,使之从抽象的、非具身的活动转变为具身的(警觉的)、开放的(open‐ended)反思。通过“具身的”,我们意指的是身心在其中从来就是统一的反思。这个表达的含义是,反思不仅仅是针对经验的,而且它自身也是经验的一种形式——这种经验的反思形式能通过正念/觉知来施行。当反思以那样的方式来施行时,它便能斩断习性的思想模式和先入之见的链条。这样一来,它便能成为一种开放的反思,向诸可能性开放而不是向那些束缚在一个人当前生活空间的表征中的可能性开放。我们称这种形式的反思为“警觉的、开放的反思”。
作为西方科学家和哲学家,在我们通常的规训和实践中,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明显与之不同。我们问,“什么是心智?”“什么是身体?”继而进行理论反思和科学研究。这一过程引起了有关认知能力的各方面的全面的主张、实验和结论。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常常忘记究竟谁在问这个问题,以及它是如何被问的。若不把我们自身包括在反思之中,我们追求的也仅是部分的反思,这样我们的问题也就变成非具身的了;它试图表达一种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 Thomas Nagel)所说的“无源之见”(view fromnowhere)。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试图拥有一种非具身的无源之见,导致有了一种来自特定的、理论上受限的、被先入之见套牢的某处(somewhere)之见。
自胡塞尔以来,现象学传统就强烈地指责这种不包含自我的反思,但现象学传统在其中只能提供一个对经验的理论反思方案。而另一个极端则是,把自我包含在内,但又出于朴素的、主观的冲动性而完全舍弃了反思。
正念/觉知则两者都不是,它直接针对我们基本的具身性,并因此表达了我们的具身性。
让我们来看看反思的理论传统和正念传统的差别如何表现在实际的问题——即所谓的心-身问题中的。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中的主导性问题就一直是:身心是同一的还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属性、描述层次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存在论关系是什么。我们已经看见在正念/觉知的静心中采取的这个简单的、经验的、务实的进路。我们的心和身可以分裂,心智能够游移,我们可能觉知不到我们在何处以及我们的身或心正在做什么——这些不过是一些简单的经验。但是这种情形,这种非警觉的习性,可以被改变。
身和心可以统一(be brought together)。我们能够开发身和心完全协调一致的习性。这个结果就是一种精熟(mastery),它不仅被个体静心者本人所知,而且对其他人也是看得见的——我们很容易通过它的精准和优雅识别出因完全觉知而洋溢生机的姿势。通常我们把这样的正念与诸如运动员或音乐家那类专家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我们认为,笛卡尔有关他是一个思维之物的结论是他问题的产物,而问题是特定实践——那些非具身的、非警觉的反思——的产物。胡塞尔的现象学尽管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涵盖了经验,可是它只是以反思思想的本质结构来继续这个传统。尽管最近对这种“我思”(cogito)的观点的批判或“解构”很流行,但哲学家仍然没有离开这个对之负有责任的基本的“实践”。
理论反思没有必要是非警觉的(mindless)和非具身的。对人类经验的这个渐进(progressive)进路的基本主张就是,心-身关系或模态不是完全固定的和给定的,而是本质上可以改变的。许多人会承认这个信念的明显的真实性。西方哲学并不像它所忽视那样否认这个真实性。
要扩展这一点:正如一般的正念情形,这里存在两种谈论具身反思发展的方法。一种方法——预备或初学者的进路——是把它比作技能发展。以学习演奏长笛为例。可以这样来描述:向学习者展示手指的基本位置,能以直接的方式,也能以指位图谱的形式。接着学习者以各种组合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这些音符,直到掌握基本的技巧。一开始,心理意图和身体活动之间的联系很生疏——心理上,一个人知道要做什么,但在身体上却无法做到。随着练习的深入,意图和行动之间的联结变得越来越紧密,直到最终,两者之间的差别感完全消失。学习者进入了这样一种境界:在现象上,感觉既不是纯粹心理的,也不纯粹是身体的,确切地说,这是一种特别的身心统一。当然,存在许多可能的解释层面,正如在许多造诣高深的演奏者那里所看到的。
尽管这样的例子似乎是引人注目的,并且尽管静心指导对于初学者而言有时会使正念听起来像某种技能的发展,但只依照这些术语所作的对该过程的描述可能确实会引起误解。来自世界各地的沉思传统都认同:如果一个人认为静心修行的关键就是发展特定的技能,从而使自己进入宗教、哲学或静心的大师之列,那么他不过是在自我欺骗,结果适得其反。特别是,涉及正念/觉知的修行,事实上从来没有被描述为静心精湛技艺的训练(当然也没有被描述为发展一个更高境界的精神性(spirituality)),而是描述为对非警觉(mindlessness)习性的放下,描述为非学习(unlearning)而不是学习(learning)。这种非学习也许会采取训练的方式并且要用功,但是这与我们习得某种新东西的那种用功的意义不同。确切地说,恰是在静心者以最大的雄心——一种通过决心和用功获得新技能的雄心——开发正念时,他的心凝固和空转着,而正念/觉知变得难以捉摸了。这就是为什么正念/觉知的静心传统谈到无功用行(effortless efforts)以及为什么它用了有关静心的弦乐器调音的类比而不是弦乐器演奏的类比——这个乐器的音被调得既不要过紧也不要过松。当正念静心者最终开始放下,而不是竭力去获得某种特定的活动状态时,他发现这时身心已自然地协调一致并成为具身的。
于是他发现警觉反思完全是自然的活动。当我们继续我们的故事时,技能和放下之间区分的重要性应该会变得日益明显。
总之,正是因为我们文化中的反思一直以来与其身体生活切断开,才使得心-身问题对抽象反思而言成为一个中心主题。笛卡尔的二元论与其说是一个竞争的解决方案不如说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明确表达。反思被当成完全是心理的,于是问题就出于它究竟如何与身体生活相连接。尽管关于这个问题的当代讨论很大程度上因为认知科学的发展而变得深奥微妙,但是它们都没有离开本质上是笛卡尔的疑问,即试图理解两个似乎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不管这些东西是实体、属性或者仅仅是描述层次,对讨论的基本结构而言都无关紧要。)从一个警觉、开放的反思的观点看,心-身疑问不必是“不管是谁的经验,心与身之间的存在论关系是什么?”的问题——而毋宁是“在实际的经验中身与心的关系是什么(正念的方面),和这些关系如何发展以及它们采取什么形式(开放的方面)?”的问题。正如日本哲学家山寺宏一(Yasuo Yuasa)所评论的:“一个人开始于这样的经验假设(experiential assumption),即通过心身的培养(shugyo)和训练(keiko),心-身模态会发生改变的假设。
只有假设了这个经验前提后,一个人才能问心-身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心-身问题并不完全是一个理性的思辨,最初来说它是一个实践的、活生生的经验(taiken),涉及一个人完整心身的凝聚。这个理论的问题仅仅是对这个活生生经验的一个反思。”
我们可能注意到,这个观点与实用主义发生了共鸣,实用主义是一个在现代不断得以复兴的哲学观念。身心关系是因为它能做什么而为人所知。
当一个人在哲学或科学中采取更为抽象的态度时,他可能会认为那些身-心关系问题,只有在他首先在孤立和抽象中满意地决定了身是什么和心是什么之后才能得以回答。然而,在务实的、开放的反思中,这些问题是与“一个人完整心身的凝聚”无法分离的。身心的这种牵涉防止了“心是什么”这种问题变为非具身的。当我们在对一个问题的反思中包含了问题的发问者和发问过程本身时(回忆一下基本的循环),那么问题就会获得一个新的生命和意义。
或许在西方人所熟悉的学科中心理分析最接近一个对于知识务实且开放的观念。我们想到的与其说是心理分析理论的内容,不如说是它的观念,在这个观念中,当自我于其中的表征网络通过分析慢慢被渗透时,心这个概念和正在经历分析的主体这个概念被理解为是变化的。然而,我们相信传统的心理分析的方法所缺的东西就是反思的正念/觉知成分。
2.6实验和经验分析
在科学中,与实用主义联结最紧密的形式是实验方法。如果一个人想知道马有多少颗牙齿,那么他必须去数数。通过演绎推理,更精细的假设在理论上可以还原到可能的观察。尽管历史上这种实验的哲学理论一直与客观主义者的非具身的知识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也不必总是这样。
正念/觉知静心能够被当成一种发现心智本性和行为的实验——一种具身的和开放的实验吗?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在正念/觉知静心中,一个人不要从企图获得某种特别的状态(正如在专注、放松、出神(trances),或具有神秘性的修行中)开始,确切地说,其目标应该是依其本身的过程来使心警觉。通过以这种方式使心放下,这样警觉和敏锐之心的自然活动就会变得明显起来。
当心变得敏锐时,佛教教义主张完全成为心正在进行的观察。的确,所有佛教的主张(无我、经验的缘起,等等)都被佛教导师当作发现而不是信条或教条。佛教导师喜欢指出,学生始终被邀请或的确被要求去置疑这类主张,并且以自己的经验直接来检验它们,而不是接受它们作为信念。(当然如果他们提出了一个极为异常的答案,他们可能被邀请再看看——就如科学教导在其常规形式中所做的那样。)就正念/觉知是一个发现经验本性的主张而言,两种反对意见可能会出现。首先,一个人可能想知道由静心获得的知识与我们称为内省的活动之间的关系。毕竟,作为一个心理学派的内省主义(因19世纪的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而出名),最终没有为实验心理学提供一个基础。在不同的内省实验室之间,对于内省方法所产生的结论根本没有一致的意见——这正是科学的对立面。但被称为内省的方法是什么呢?每个实验室都以一个理论为开端,该理论认为经验可分解为某种元素,而被试可以被训练用那种方式分解他们的经验。实验要求被试像一个外在的观察者那样注视自己的经验。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认作是内省的东西。这恰恰就是被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称之为科学和哲学的抽象态度东西的本质。
正念的静心者会说,内省主义者实际上根本没有觉知到心智,他们只是在考虑他们的思想。这样一种活动当然只适合于展示一个人对心智所抱有的各种先入之见——因此,不同的实验室难以达成一致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斩断了内省的态度,正念/觉知静心才存在。
对正念/觉知原本作为一个现场的心智观察方法可能出现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通过静心或变得警觉和觉知,一个人逐渐瓦解了他在世界中的常规的存在模式,即他积极地介入,以及体会世界是独立实在的那种想当然的感觉。那么正念如何赋予我们它所瓦解的常规存在模式的任何信息呢?我们的回答是,这个问题要有意义,那么本身必须假定这种抽象态度;一个人正在回顾这种积极的介入并且说它被瓦解或未被瓦解,好像这能从某个独立的、抽象的、有利的知识点被知觉到。从佛教的观点看,正是通过自然正念,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才有可能首先知道一个积极介入世界的常规的存在模式。(梅洛庞蒂本人确实在其《知觉现象学》的前言中这样说过。)正念所瓦解的是非警觉——也就是说,虽然非警觉介入却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他正在做的。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观察改变了正在被观察的,而这就是开放反思的含义所在。
最后,我们始终认为,有必要有一个对人类经验的训练有素的观点,它能够扩展认知科学的领域以便涵盖直接经验。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已经存在于正念/觉知静心的形式中。正念/觉知修行、现象学哲学和科学都是人类的活动;每一个都是我们具身性的表达。自然,佛教学说、西方现象学和科学,每个都继承了各种各样的学说争论和相互冲突的主张。然而,就其作为实验的形式而言,它们的每一个都是向每个人开放的,可以由每一个他者的方法加以检验。因此,我们认为,正念/觉知静心可以在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之间架起一座自然的桥梁。我们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佛教学说、现象学和认知科学的一些主要论题——关于自我和主客关系——中,我们已经发现了汇聚点。在我们的发现之旅中,我们现在要转向的就是这些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