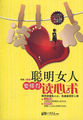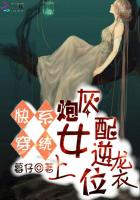4.1我们所说的“自我”是什么
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时刻都有体验在进行着。我们看,听,闻,尝,触摸,思考。我们可以高兴,生气,恐惧,疲劳,困惑,感兴趣,处于烦恼的自我意识(agonizingly self‐conscious)中,或者专注于某一追求。我能感觉到我正被我自己的情绪控制着,别人的表扬让我觉得更有价值,失败让我觉得自己被打垮了。这个出现又消失,看起来如此恒常却又如此脆弱、如此熟悉却又如此飘忽的自我,这个自我-中心(ego‐center)是什么呢?
我们陷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即使只是草草地留意一下经验,我们也能发现:我们的经验总是变化不定,而且始终依赖于一种具体的情境。要成为人——实际上要活着,就总是要处于一种情境,一个背景,一个世界。
我们不会经验到任何永恒的、独立于这些情境的东西。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都相信我们的同一性(identities):我们有人格、记忆和回忆,我们有计划和期待,所有这些似乎都凝结在一种连贯的视点中,凝结于一个中心,由此我们面向世界,立基于其上。如果不是植根于一个单独的、独立的、真实存在的自我,这样的视点怎么可能存在呢?
这个问题是本书所论及的一切事物的交汇点:认知科学、哲学和正念/觉知的静心传统。我们希望提出一个彻底的主张: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反思传统——哲学、科学、精神分析学、宗教、静心(meditation)——都已经挑战了这种朴素的自我感。从未有一种传统宣称在经验世界中发现了一个独立的、稳固的,或者单一的自我。让我们援引大卫·休谟的名言:“对我而言,当我亲熟地进入我所谓的我自己(myself)的时候,总是碰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知觉,如冷或热、明或暗、爱或恨、痛苦或喜悦。任何时候,没有知觉我就把握不到我自己,而且除了知觉也观察不到任何东西。”这种洞见直接与我们从未止息的自我感相矛盾。
正是这种矛盾,这种反思的结论与经验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驱使我们开始本书的探讨。我们认为许多非西方(甚至是沉思的(contemplative))传统和所有西方传统,在对待这个矛盾时避而远之,拒绝考虑它,采取一种可以二者取一的回避(a withdrawal that can take one of twoforms)。通常的方式就是干脆忽视它。例如,当休谟在研究中反思时,他无从发现自我,他就选择回避并沉迷于西洋双陆棋游戏,让自己安然于生活与反思的分裂。
让·保罗·萨特通过说我们“注定了”要相信自我,也表达了这一观点。第二种策略是假设一个经验无法触及的先验自我,比如奥义书(Upanishads)中的灵魂(atman)和康德的先验的自我(the transcendental ego)。(当然,非沉思传统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矛盾——例如心理学中的自我概念理论(self‐concept theory))我们所知的主要或许唯一直面这个矛盾并且长久以来研究这个矛盾的传统来自于正念/觉知静心修行。
我们已经将正念/觉知修行描述为一种逐渐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能在正式的静心中,而且也能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呈现人的心智和身体。
通常,当知觉、思想、感觉、欲望、恐惧和其他种类的心智内容就像猫儿在咬自己的尾巴那样无止境地互相追逐时,那些静心的初学者会惊愕于他们心智活动的纷乱。当静心者增强了正念/觉知的稳定性的时候,他们会经历这样一些时期,这时他们不会总是(用传统的意象来说)被吸进漩涡或者从马背上摔下来,他们开始洞察心智在被经验到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注意到经验是无常(impermanent)的。这不仅仅是所有人都异常熟悉的树叶飘落、少女凋零和国王被遗忘之类的无常,而是个人心智自身活动的无所不在的无常。每时每刻,新的经验生起又消逝,就好像是瞬间生灭的心智事件(mental occurrences)变迁的急流。而且这个变迁除了包含知觉还包含知觉者。正如休谟所注意到的,没有一个始终保持不变的接受经验的经验者(experiencer),没有一个为经验立足的平台。这个真实的无家园的体验被称为无我。每时每刻,静心者看到心智正在摆脱其无常感和缺乏自我感;看到心智在执着于经验,仿佛它们是永恒的;看到心智在评论经验,好像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知觉者在评论一样;看到它正寻求任何打断正念的心智娱乐(mental entertainment),然后不安地转向心智的下一个专注点;所有这些都伴随着一种不断地挣扎的感觉。这种弥漫于经验的不安、执着、焦虑以及不满的潜流被称为苦(Dukkha),通常译为suffering。当心智力图避免它天生的无常和缺乏自我时,苦便自然地生起并成长。
在佛教中,日常经验中持续的自我感与无法在反思中发现的自我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有着核心的重要性——人类苦的起源就是在没有自我的地方试图抓住和建立一个自我感,一个自我。当静心者瞥见了无常、无我及苦(存在的三法印),并约略地领会到一切皆苦(以第一圣谛闻名)的原因可能源于他们自己的我执(self‐grasping)(以第二圣谛闻名)时,他们就会发展出真正的动机和深入研究心智的紧迫感。他们试图建立一种强大而又稳定的对心智生起时刻的洞见和好奇。他们被鼓励研究:这一刻(this moment)是如何生起的?它的条件是什么?“我”对它的反应的本质是什么?“我”的经验是在哪里出现的?
因此探寻自我是如何产生的是一种问的方式:“心智是什么,它在哪里?”对这些问题原初的好奇实际上与笛卡尔在《沉思录》中所展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说法或许会让有些人感到吃惊,因为笛卡尔在当今实在是不受欢迎的。从一开始,笛卡尔就决定不仰赖教父(Church fathers)言论,而是依靠自己的心智在反思中所能辨明的东西。很明显,就像现象学一样,这也彰显了自恃研究(self‐reliant investigation)的精神。然而,笛卡尔很快就此打住了:他着名的“我思故我在”并没有触及那个在思考的“我”的本性。
的确,笛卡尔推断说“我”根本上是一个思考的东西,但是这里他走得太远了:“我在”所承载的唯一确定的东西是那个作为一个思想的东西。假如笛卡尔更加严格、缜密,他就不会匆忙地得出我是一个思考者(a thinkingthing)的结论;相反,他将保持对心智过程本身的关注。
在正念/觉知修行中,对思想、情绪和身体感觉的觉知在我们通常经验到的基本的不安中变得相当明显。为了洞察那种经验,了解它是什么以及如何产生,某些类型的正念静心指导静心者尽可能精确和冷静地专注于经验。只有通过一种务实的、开放的反思我们才能系统地、直接地检视通常为我们所忽视的不安。当这些经验内容——散漫的思想、情绪的色调(emotionaltonalities)、身体的感觉——生起的时候,静心者是警觉的,但是并不是通过关心这些思想的内容或者“我”正在思考的感觉,而是仅仅通过注意(noting)“思考”以及去留意那些永不停息的体验过程。
就好像正念静心者惊异地发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失念(mindless)一样,那个开始置疑自我的静心者的最初洞见通常并不是无我而是对完全利己狂的发现。一个人不断地思考、感觉和行动,就好像有这么一个自我需要保护和保持。对自我的领地的最轻微的侵犯(指缝中的碎屑、吵闹的邻居)都会激起恐惧和愤怒。张扬自我的些微的希望(成就、赞誉、名望、快乐)都会激起贪念和执着。一个情境显露出任何一点与自我无关的迹象(等公交车、静心)都会引起厌倦。这样的冲动是本能的、自动的、普遍的和强有力的。在日常生活中,它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冲动确实在那里,并不断地发生着,然而对那些抱有怀疑的静心者而言,它们有意义吗?他认为他要拥有何种自我来确保这种态度呢?
西藏的上师楚臣嘉措(Tsultrim Gyatso)表述了这一两难困境:
要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这一种自我必须是持久的,因为如果它每时每刻都在消亡,那么人们就不会如此关心下一刻它会发生什么;它不再是某个人的“自我”。再者,这个自我必须是单一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单独的本体,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会担心发生在“自我”上的事情多于担心其他任何人的自我呢?它必须是独立的,否则说“我做了这个”(I did this)及“我拥有那个”(I have that)就没什么意义。如果一个人不是独立的存在,那么就不会有人宣称行动和经验归属于自己。我们行动着,就好像我们有一个需要我们时刻呵护和促进的持久、单独和独立的自我。绝大多数人通常都不大可能去怀疑或解释这样一个想当然的习惯。然而,我们所有的苦都与此相关。所有的失去与获得、快乐和痛苦的生起皆因我们如此地认同我们这种模糊的自我感受。我们在情绪上与“自我”如此密切关联,以至于我们认为它理所当然……静心者并不去思考这个“自我”。对于自我存在抑或不存在,他也没有什么理论。相反,他只是训练自己去观察……他的心智是怎样依附于自我和“我的”的观念(the idea of self and “mine”)以及所有苦是如何从这种依附中生起的。同时他仔细地寻找着那个自我。他试图将它从所有其他经验中分离出来。既然自我是他所有苦的罪魁祸首,他就想找到并鉴别它。具有讽刺的意味的事情是,无论他如何努力,他都找不到可以算是自我的东西。
如果并不存在那个被经验到的自我,那么我们以为存在这样一个自我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侍弄自我(self‐serving)这种习惯的根源是什么呢?
那个在经验中被认为是自我的东西是什么呢?
4.2在蕴(积聚)中寻找自我
现在我们转到佛教教义中被称为阿毗达摩藏(Abhidharma)(论藏)的一些范畴来。这个词是指一些文本的集合,它是佛教三种文献中的一种(另两种分别是包含道德戒律的律藏(Vinaya)和包含佛陀言论的经藏( Sutras))。基于阿毗达摩的文本和其后对它们的评注,形成了对经验的本质进行分析性研究的传统,大多数佛教流派仍在教授和研究这种传统。阿毗达摩包含了考察自我感产生的诸套范畴。它们并非作为本体论范畴,就像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看到的那样。相反,这些范畴一方面用于对经验的简单描述,一方面是作为展开研究的线索。
这些范畴中最普遍的,也是所有佛教流派所共有的一套范畴名曰五蕴(aggregate)。(蕴对应的梵文是“skandha”,字面意思是“积聚、堆积”。据说,当佛陀第一次教授用以考察经验的框架时,他用谷堆来代表每一蕴。)这五蕴是:
1.色
2.受
3.想
4.行
5.识
五蕴中的第一蕴被认为是基于身体层面或物质层面;其他四蕴则是心智层面。这五蕴构成了心色法(psychophysical complex),这个心色法组成了人,也形成了经验的每一个瞬间。我们将考察将每一个蕴作为我们自己的方式,并且探寻我们是否可以在五蕴中找到什么来解释我们对自我实在性的基本的、情绪的、反应性的信念。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寻找一个成熟的真实存在的自我(ego‐self)——某种作为我们情绪信念的对象的持存自我,即相信在独立的、无常的日常人格之下有一个根基。
色
这个范畴是指身体和物理环境。然而,严格说来这个范畴是在感觉——六种感官及其相应的感官对象——层面上来指身体和物理环境的。它们是:眼睛和视觉对象,耳朵和声音,鼻子和气味,舌头和味道,身体和可触物,以及头脑和思想。这些感官并不是指身体的外部器官,而实际上是指知觉的物理机制。将心智器官(传统上关于它的物理结构是什么样的存在着争议)和思想作为一种感官和它的对象,是因为它们在经验中就是这样显现的:我们感觉我们用心智感知思想,就好像我们用眼睛感知一个视觉对象那样。
我们可以指出,即使在这种分析的层面上,我们也已经摆脱了一个抽象的、非具身的观察者的通常观念。按照这个观念,就好像一个认知者空降到一个既定的世界,这个抽象的、非具身的观察者作为一种单独的和独立的范畴与世界打交道。而在此,就像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里一样,我们与物理世界的遭遇已经情境化和具身化了。事物都是根据经验来加以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