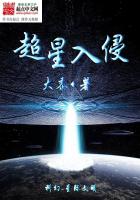然后,我看到阿其扔掉烟头站了起来,他一步跨到了我面前把我从椅子里一把拽到了他怀里。在他疯狂地亲吻着我的时候,我又一次闻到刚才在我的床上我闻到过的,发自静茹身上的那股气味,辛辣,且甜腻。
一种强烈的羞辱感,当我需要的时候,我从未得到过,而现在,我却意外地被迫接受。我用力推开阿其,同时我看到秧子在墙上笑得更加灿烂了。我说:阿其和静茹结婚吧,快快,否则静茹会逃走。静茹总是会不失时机地逃走。
阿其抬起头来,他的口角上沾了我的紫红色的唇膏。
阿妹,你为什么好久不来?我去找你,静茹说今天晚上你会在家,可是你不在,静茹在……
我的双眼刹那间又涌满了泪水,我安静地站着,眼睛里却涌动着疯狂的泪光,我重复着:阿其,让静茹和你结婚吧,她需要你。
然后,我听到自己狠毒的哭声,很轻,却很凌厉。
十一
那天以后,静茹搬走了,她给我留下了一封信,她在信里说:其实,阿妹,我爱的是你所爱的一切,史帝文也好,阿其也好,都是你的,但是,我却爱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
静茹,占有着我的爱人,我的朋友和我,并且,是这样理直气壮毫无愧色。而我,恰恰因此而爱着她,这个不可救药的女人,我的静茹。
这封信里,静茹只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没有别的联系方式。
不久以后,阿其真的结婚了,和他店里的一个做发型的小姑娘,很大的眼睛,笑的时候露出一只虎牙,淳朴而透明。
婚礼那天,一块红色的地毯从美容院里一直铺到大街上,豪华轿车停了一街。静茹没有看见这场面,她要在,她一定会在我耳边叫嚷:阿妹,我结婚的时候,也要在这样一块长长的红地毯上走进婚礼的殿堂。
静茹永远也不会在说这话的时候想到,她其实已经走入过一次婚礼的殿堂,可是她自己逃逸而出了。
我绕道去pianobar上班是为了躲过婚礼的场面,但我还是看见了站在街角等着婚车的阿其。他穿着燕尾服,脖子里的领结在阳光下闪耀着瑰丽的光芒,依旧是高挑的身影,健硕的长腿。我想起那个多年前拿着指挥棒走上舞台在掌声中鞠躬谢幕的男人,那时候的我,却总是坐在乐队众多的人群中被淹没无踪。
独自蜗居的白天里,我常常打开早年的影集,看那些我曾经拥有却不再回来的生活。那张三个人的旧照片已经褪色发黄,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军装站在中间,笔直的身姿显得有些僵硬,脸色竟然是严肃的。左边的女孩羞涩地低着头,一抹淡淡的笑容洋溢在嘴角边,右边那个穿着军装把一脸笑容开得象太阳花一样的二十岁女孩一去不返。那是阿其、秧子和我在八年前的一张合影,那时候,阿其是部队文工团的乐队指挥,秧子是歌手,那首《血染的风采》常常被她唱得如泣如诉,她是我们军区的百灵鸟。而我,仅仅是乐团的一名键盘手。然而,那些年月里的我,脸上却常常有着如此灿烂的笑。
秧子已经大红大紫了,拍了许多颇有影响的电影,常常出现在首映式或者新片的新闻发布会上。电视镜头里看到的秧子,和阿其店里的照片有着截然不同的装扮和气质。许多次看到那些秧子主演的影片,我总是想,没有人会知道,我,秧子,还有阿其,曾经是部队文工团里的战友。那时侯,我爱上了那个叫阿其的男人,然而,阿其却追随着秧子,秧子转业了,阿其也改行去做了发型师。而这,仅仅都是历史了,不可挽回。
阿其的美容院已经远近闻名,不仅是因为他的手艺高超,更多的原因是秧子的出名让他挂在墙上的那张照片成了最好的广告。去美容院做发型或者脸部护理的人依旧是时髦女人居多,人们都说,墙上那个和阿其肩并肩笑着的女孩很象阿其的妻子,阿其是娶了大明星了吗?人们知道,这个当红明星曾经与这位潇洒英俊的美容院老板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美容院扩建了,招收了许多学徒工,每次走过那扇巨大的茶色玻璃门,我总是看见阿其的妻子坐在收银台里用一把金属指甲锉修理着她那些尖细的指甲,那张酷似秧子的脸上一对大眼睛顾盼生辉,有顾客进店门,她总是笑着招呼,一笑,嘴角露出虎牙,洁白明亮,那笑,便是纯净而无所忧虑的笑。
阿其穿梭于为客人修理着头发或者做着皮肤按摩的服务生之间,他不断指点着那些年轻人的手法和技术,他严肃的表情让我反复回忆起多年前他捏着指挥棒皱着眉头敲击着谱架叫着:重来重来,第三乐章的第一小节起,华彩段的激情要表现出来,开始!
那些美好的回忆在我逐渐低弥的生活中已经定格,没有复活的希望。
冬天过去了,二月的春天以羞涩矜持的姿态开始降临这个东方繁华的都市。我没有看到新绽的绿叶,我象一只夜行的猫独自走在午夜的pianobar外清冷的大街上,黑暗中,绿叶亦是黑色的。大街上的商店早已关闭,橱窗里的塑料模特却以千篇一律的姿态终年对着我展露虚假的笑容,那个穿着白色紫澜门羊绒大衣的金发女人伸出一只纤细的手和任何一个走过巴黎春天百货的人招手微笑,意欲勾引人们走进那扇豪华的玻璃门。
在那些和静茹搂着肩膀走在这条归家路上的过往时日里,静茹常常会指着这个塑料模特说:阿妹我什么时候可以拥有这样一件大衣啊!
那件标价8898元的大衣在灯火阑珊的夜色中闪烁着冷艳的光芒,静茹的神色满怀希冀,一如她在对我说“史帝文对我很好我想嫁给他”或者“阿其好性感,你看他那两条长腿多么迷人”时一样充满向往。那种时候,我多半笑而不答,我知道我不必表示我的好恶,静茹永远把我的所爱看作是她的,我相信这是因为她也爱我,就象我爱她一样,我无能为力。
在我独居的单身公寓里,我的屋子依然充满史帝文的气息。古朴的蜡染壁挂、精巧的俄罗斯套娃或者张扬的羊头墙饰,无一不在告诉我,这个地方,曾经被一个叫史帝文的画家占据。他出现在我脱下军装后的某一个年头,他给了我信以为真的爱情生活,却终究脆弱,犹如那只青花瓷瓶,在一场变故中钝然破碎,如此不堪一击。
阿其完全陷入了忙碌的生意,史帝文死了,静茹远离了我,我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过着前所未有的孤独生活。但我似乎并不寂寞,我在阳光灿烂的白天深眠于纷杂繁复的世界之外,我在深夜寂静的街头独步徜徉,我知道我是自己的,我不属于任何人,我不需要走过任何一块红地毯,我依然可以过平静安然的生活。
我想我很满足,宁静的满足,死心塌地。
十二
一个午夜已过的凌晨,我从pianobar下班回家。走过巴黎春天百货的玻璃橱窗,我看见一个留着卷曲短发的女人正站在橘黄色的路灯下看着我。
静茹!
她向我奔过来,圆脸上的大眼睛里闪着小野兽一样幼稚而凶狠的光芒。
“阿妹,我给过你电话号码,你为什么不找我,你好狠心。”她看见我,依然是哭诉,就如那次她从三轮车上下来红肿着眼睛说“阿妹我过不下去了,我要离婚。”时一样,我是她的依赖,始终如此。这个女人,岁月和磨砺竟是无法改变她的幼稚、以及浅薄到可爱的率真性格。
我宽厚地对她笑笑,张开了双臂。她一头撞在了我的胸口,然后开始大哭起来:“阿妹我忍不住寂寞,让我回来吧!”
这个天真到无知的女人,为什么我永远摆脱不了她,一如她也永远离不开我一样。我曾经决定要照顾她一辈子,现在,她果真回来了,在我毫无防备的一个午夜的街头,她再一次站在了我的面前。
我无言以对,只是看着暗淡灯影中的静茹微笑着,然后,我搂住静茹的肩膀,向着我的单身公寓走去。
子夜的城市,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