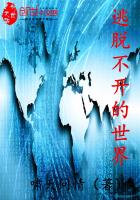走廊的顶灯忽明忽暗,跟物业说了很多次,总不见有工人来修。
电梯缓缓地打开门,里面的强光瞬间照亮女人那张惨白的脸,淡脂素粉淡化了她的年龄,乌黑的头发直直地垂在肩上,与身上的黑色风衣混成一体。
女人走进电梯,疲惫地靠在角落,身上所有的力气早已消耗殆尽。十八楼的按钮极不情愿的映出红色,门又缓缓地关闭……
聪明的女人是在懂得世事难全的道理后,还能泰然自若地周全一切。
生活的记录总是会不经意地连成一部电影,又不挑时间、不分场合地播放在人的脑海里,欢快的电影总是档期很短,而那些悲伤的,无奈的,伤痛的却永不删档。
此刻,卓荷苏的电影便是从初恋失败开始。关于“初恋”那些美好的画面早在冗长的岁月中氧化、褪色……她依稀还记得男主角的样子。他很高,很瘦,眼睛深邃,嘴唇丰满。
他们大概有过一段开心的日子,左不过是和其他初恋男女一样,做些很傻、很无聊的事,两个人却乐在其中。只是再多的快乐都没办法逃过“大四失恋季”。
没哭也没闹,没有偶像剧里那些撕心裂肺的纠缠镜头,好像还吃了一顿散伙饭。男孩儿将有更好的前程,荷苏说:祝福你。男孩儿一再表示,只要女孩儿愿意,可以稍微等一等。荷苏说:不愿意。
荷苏没告诉男孩儿,在他们分手的前一天,卓爸卓妈刚刚协议离婚。卓妈早就知道丈夫外面的女人,荷苏却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一个五岁大的弟弟。
为了不影响女儿的学业,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竟然可以相安无事地生活四五年。女孩儿没有埋怨任何人,甚至感谢父母、那个女人和一个未谋面的弟弟,她的学业里莫名地多出好几个人的付出。
曾经以为十分美好的什么情,什么爱,在荷苏眼里,都像是堆放在学校垃圾站的东西,不分冬夏地散发着臭不可闻的味道……
上学那会儿,荷苏很喜欢看小说,跟着男女主角命运多舛的爱情欢喜流泪,可看得多了,类似的情节就容易混淆,唯有些刻骨铭心的或是莫名其妙的字句留在心里,历久弥新。
“不饿的时候,爱情很重要,饿的时候,什么都不重要。”读小说的时候,这句对白可归于莫名其妙那一类。可到大四下学期找工作的时候,荷苏对它的理解忽然变得无比深刻。
寝室里最漂亮的女孩儿肖畇畇与男友闪电分手。一连几个晚上,抱着荷苏痛哭不已,她抹着眼泪说没有办法,她不想回到家乡,不想像母姐辈那般碌碌一生。
荷苏一直没想明白“不回家”与爱情的冲突点,可那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某个清晨,畇畇突然浓妆淡抺约见了她的新男友。荷苏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位“新男友”似乎有些神通,帮女孩儿拿到留校的名额。在荷苏与其他同学每天一身臭汗地挤人才市场,又彻夜不眠地制作简历时,女孩儿已经搬进男友准备的婚房里。
面试连续失败后的某个凌晨,月光照在宿舍里的电脑显示屏上,那上面是被修改过无数遍的简历,荷苏看着窗外一片漆黑,想起畇畇抱着她哭的那些夜晚,原来该哭的人是自己。
毕业之后的几年,卓荷苏在各种作坊式的软件公司和不知名的通讯公司中跳来跳去,终于如愿跳进一家在业内有名有号的瑞士电子公司,并成为公司研发部负责数据收集分析的小主管。
上班第一天,荷苏接到一个男孩儿的电话。说是男孩儿一点都不过分,青涩的嗓音带一点点沙哑,听起来像是刚刚过了变声期。
男孩儿在电话里说:“姐,爸过世了,你和阿姨要不要来送送?”
曾经陪伴她二十多年的男人死了,却连见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给她,荷苏隔着电话,竟很羡慕那个陌生的男孩儿。
下班时,荷苏为自己找了辆出租车。人一坐进去,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她给卓妈打了通电话,老人浓重的鼻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原来男孩儿也通知了卓妈。
老人不准女儿去送行:“死了就死了,活着的时候他也没管过我们,那个狐狸精也太狠了,最后一面都不让你见,现在还装什么好人……”
荷苏本想说些亲情、恩情的话来开解,可话没来得及出口,就听见卓妈放声大哭,连出租车司机都惊动了。
母女俩隔着电话对哭了个把钟头,直到荷苏惊觉自己正身处陌生的路上。
“你一直都没告诉我,你要去哪儿?”司机憨厚地指了指副驾驶位置前面的监督卡,上面有他的照片,照片下面用中英文双语写着他的名字:“石毅”。
石毅一边开车送荷苏回家,一边说些劝解的话,不过是“节哀顺变”之类的。站在痛苦外面劝痛苦,本来就是件很容易的事,荷苏敷衍着道谢。下车时,石毅忽然叫住她:“甭管‘老家儿’有什么不对,也都是身前的事。人死如灯灭,是非对错都随一把黄土埋了吧。”
那是荷苏第一次打量石毅。黝黑的一张脸,五官浓重得恰到好处,笑起来两排雪白的牙齿立正排好,浅浅的梨窝在嘴角若隐若现。
父亲的葬礼上,卓荷苏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和为她舍去五年父爱的弟弟,他长得很像老卓,荷苏忍不住伸手去摸他的脸。
男孩儿有些腼腆,脸红红的,却没躲开。卓妈到底没来,那个女人几次看向荷苏,似乎有话要说,终归什么也没说出口。
“爸爸不在,乔松就是大人了。”荷苏说话时看着父亲的墓碑,照片上的男人跟离开她时没有两样,“你要好好照顾妈妈,有事打电话给我。”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卓乔松意外地看着荷苏,此前,他只在照片上见过这位“姐姐”。
“傻瓜,我是你姐姐。”荷苏拍了拍男孩儿的肩。她不敢想,如果卓妈看见这一幕会有什么激烈的反应,可他们上一辈的恩恩怨怨,真的不必牵涉到这样一个孩子。
葬礼之后,荷苏匆忙赶回家陪卓妈。本想说说她,一日夫妻百日恩,不管之前还有多少难消之恨,都不该连最后一程都不去送。可一进门就看见卓妈肿得桃一样大的眼睛,荷苏什么都没说。那天晚上,娘儿俩难得一起吃顿饭,卓妈做了一桌子的菜,荷苏举起筷子才发现,没有一道是自己爱吃的。
安抚了母亲,荷苏不得不连夜赶回她工作的城市,公司是有丧葬假的,只是她入职时,负气地在社会关系里只填了卓妈。
石毅没故意去车站接荷苏,只是刚好在那里等活,女人也是上了车才发现是石毅,男人笑呵呵地说,这是缘分。
出租车还没绕进主路,荷苏就睡着了。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还在石毅的车里,身上盖着粗糙的工作服。车窗外,天色渐白,石毅站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哆哆嗦嗦地抽着烟。
后来,荷苏很多次回想起那个黎明,想起朝阳照着男人瑟瑟发抖的背影,想起出租车和工作服带给她的温暖,她想,那大概就是他们的交往纪念日吧。石毅并不是理想中的男主角,卓妈对老卓的原谅也不足以改变她对感情的态度。可就在那一刻,荷苏想起自己已经二十七岁了,想到这个年龄便觉得很累,很想依靠一下,一下而已……
肖畇畇对卓荷苏不经筛选的与石毅交往始终持反对意见。彼时,她早已辞掉了大学教书的工作,经营一家规模不大的咖啡馆。因为离荷苏的公司很近,所以两个女人常常见面。
上一次,荷苏捧着畇畇亲手煮的咖啡,忽然想起,大学时女孩儿说的,不要想“碌碌一生”,那她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吗?畇畇没给她答案,只是笑笑,荷苏第一次见到这样分辨不出任何情绪的笑容。而畇畇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指责荷苏的。
畇畇说他们不相配,迟早会分手。荷苏不同意,这都什么时代了,难道还讲门当户对那一套?
“不是门当户对,是要登对。你看,自古以来,书上那些深宅大院的小姐为什么偏爱穷酸秀才?人家有共同语言,谈个诗,作个画,吟风弄月的。她是不嫌贫爱富,可她也没找挑粗脚汉去啊……”畇畇总是理直气壮,好像每一句都是真理。
荷苏不同意,两个人的默契都是磨合出来的,哪来那么多天生“登对”的人?
“我看你和那个谁……”畇畇话一出口就发现不对,却还是坚持说完,“就挺登对。”
女人之间的默契,就是能把任何敏感的人、事、物用代号来替代,且事先不必沟通,便能相互了解对方代号的含意。
荷苏低下头,手中的咖啡陡然变冷:“帮我换一杯吧。”
两个女人都沉默了,荷苏知道畇畇不是故意的,可大四那年,她与“那个谁”吃完散伙饭,就已经各不相干了……
聪明的女人是在懂得世事难全的道理后,还能泰然自若地周全一切。就像卓荷苏隔着包房的门,分明听见石毅的母亲小声责怪儿子:“这样的女人能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生孩子?看她穿成那样就不像是干活的人,那过了门是你伺候她,还是她伺候你?还找这么贵的地方吃饭,有金山银山也得让她吃穷……”
第一次拜见家长,荷苏特意打扮自己,精心挑选馆子,而直到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的傻,石妈说的那些大部分算是中了,可惜荷苏连掩饰都忘记了。
纵然知道自己不被喜欢,荷苏还是积极陪老人逛街。远道而来看望子女,总要多多买些特产,带回去荣耀乡里。
好不容易把母亲送上车,又亲眼目送列车缓缓出站,石毅粗壮的大手始终紧紧握着荷苏的细指:“我妈说她很喜欢你。”
荷苏仰头看着男人的笑脸,他显然不擅长说谎,却愿意为了自己说谎,女人的手指反握得更紧:“早点下班,我订了你最喜欢的湘菜馆。”
“啊?今天晚上不行,早应几个哥们儿一起喝酒。”石毅不好意思抓抓头。
“哦。”荷苏把失望掩藏在笑容里,“那改天吧。”荷苏说不清为什么没把今天是两个人交往二周年纪念日的事说出来。如果她说了,男人应该会推掉一切应酬先来陪她。可是……所谓“纪念日”,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如果不纪念,那便只是个普通的日子。既然是普通的日子,记得或忘记都没什么好大惊小怪。
回公司的路上,荷苏用自己的道理安慰了自己的失望,可到了公司,却没能安抚其他同事的 “大惊小怪”。
装满格子间的大房像要炸锅一样的热闹,从瑞士空降的研发执行总监刚刚来过。前台的女孩儿们交流着新总监的颜值,大房里仅有的几个女助理也忙着补妆。
就在刚刚,荷苏的顶头上司吴经理为表诚意,集合部门所有同事办了个简单的见面仪式,独缺荷苏一人。吴经理是个等待安全着陆的人,做事谨慎小心。荷苏实在明白他不能召集全部属下时的着急心情,可想来,老外应该不会在乎这些虚礼。荷苏简单整理一下自己,准备去吴经理那 “自首”。关于新总监的种种窃议,都渐渐消失在她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