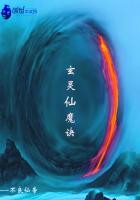我坐在温德米尔的台阶上,仍然盯着盖特在夜色中消失的方向,忆起这些,就像重新经历了一遍。对我做过什么的认识像一场雾进入我的胸腔,冰冷、黑暗、蔓延开来。我皱起眉头,俯下身。冰冷的雾从我的胸腔穿过背部,上达我的脖颈。它充斥我的大脑,下达我的脊柱。
寒冷、寒冷、悔恨。
80
这是有关美好的辛克莱家族的真相。起码,这是外公知道的真相。他小心地不让报纸披露的真相。
两年前的一个晚上,一个炎热的七月晚上。
盖特威克·马修·帕蒂尔,
米伦·辛克莱·谢菲尔德,
以及
约翰尼·辛克莱·丹尼斯,
丧生于一场房屋失火,这场火灾被认为是一罐汽艇燃料在衣物间翻倒而引起的。在附近的消防队赶到现场之前,那栋房子就被烧为了灰烬。
发生火灾时,卡登丝·辛克莱·伊斯门在小岛上,但没有注意到火,直到火势蔓延开来。她意识到有人和动物困在屋内时,大火让她没法进入。她试图营救,手和脚都烧伤了。接着她跑到岛上的另一栋房子里,打电话给了消防队。
救援最终抵达时,人们在小海滩发现了伊斯门小姐,一半在海水里,蜷缩成一团。她没法回答发生了什么,脑部似乎受了伤。事故之后很多天里,她不得不大量服用镇静剂。
哈里斯·辛克莱,岛的主人,拒绝对火灾的起因进行正式调查。周围的很多树都毁了。
人们在他们的家乡坎布里奇和纽约为
盖特威克·马修·帕蒂尔,
米伦·辛克莱·谢菲尔德,
以及
约翰尼·辛克莱·丹尼斯,
举行了葬礼。
卡登丝·辛克莱·伊斯门身体欠佳,未能出席。
接下来的那个夏天,辛克莱家族回到了比奇伍德岛。他们肝肠寸断,悲痛之下,大量饮酒。
之后他们在老房子的灰烬之上建了栋新房子。
卡登丝·辛克莱·伊斯门不记得有关火灾的任何事情,不记得它曾发生过。她的烧伤很快治愈,但她对于之前那个夏天的事情表现出选择性遗忘。她执意相信她是在游泳时伤了头。医生们推测她的偏头痛是由下意识的悲伤和愧疚造成的。她接受了重度药物治疗,身心都极其脆弱。
医生们也建议卡登丝的母亲停止对这场悲剧进行解释,如果卡登丝自己记不起来的话。每天都听一遍创伤经历,会让人受不了。让她自己记起来。她在经过了大量时间疗愈之前,不应该回到比奇伍德岛。事实上,应该采取任何措施让她在出事后的那一年远离那座岛。
卡登丝表现出了一种令人忧虑的欲望,想要摆脱所有不必要的东西,甚至具有情感价值的物品,似乎在为过去的罪行进行补赎。她染黑了头发,穿着上变得十分简单。对于卡登丝的行为,她母亲寻求了专业建议,被告知这是悲痛过程的正常部分。
出事后的第二年,这个家开始恢复正常。在缺席很多课程后,卡登丝再次上学。最后,女孩表达了想回到比奇伍德岛的愿望。医生们和其他家庭成员同意了:这么做也许对她有益。
在岛上,也许,她会完成疗愈。
81
记住,别把脚弄湿了,也别把衣服弄湿了。
把亚麻橱柜、毛巾、地板、书和床浸湿。
记住,汽油罐离引火物远一些,这样你能抓住它。
看着它着火,看着它燃烧。然后跑开。用厨房的楼梯井,从衣物间门口出来。
记住,拿着汽油罐,把它还回船库。
在卡德唐会面。我们会把衣服放进洗衣机,换衣服,然后去看火焰,再打电话给消防队。
这是我对他们说的最后的话。约翰尼和米伦拿着汽油罐和引火用的装着旧报纸的袋子去了克莱尔蒙特的上面两层。
在盖特去地下室之前,我吻了他。“在一个更好的世界再见。”他对我说,我笑了。
我们有点醉了。我们喝掉了姨妈们离开岛之前剩下来的酒。酒精让我感觉头晕而有力量,直到我独自站在厨房里。我感到晕头转向,想呕吐。
这栋房子冷飕飕的,似乎就该毁掉,里面装满了姨妈们争斗的物品。艺术品,瓷器,相片。它们给家庭的愤怒火上浇油。我用拳头击打着厨房里那幅妈妈、卡丽和贝丝小时候,对着镜头咧嘴而笑的照片。照片上的玻璃碎了,我踉跄着往后退。
酒让我的头昏昏沉沉,我不习惯。
一手拿着汽油罐,一手拿着装着引火物的袋子,我决定赶快把事情做完。我先把厨房浇上汽油,然后是食品储藏室。我把餐厅浇上汽油,把汽油往起居室沙发上浇时,我意识到我应该从离衣物间最远的地方开始。那是我们的出口。我应该最后给厨房浇汽油,这样我跑出去时脚不会被汽油弄湿。
真笨。
从起居室通往前廊的正门已经浇湿了,不过后边还有一扇小门。它在外公的书房旁边,通向去往员工楼的小路。我可以用那扇门。
我把部分过道浇上了汽油,接着是工艺室,毁掉外婆漂亮的印花棉布和七彩纱线,让我有点于心不忍。她肯定对我在做的事情表示憎恶。她爱她的布,她的老缝纫机,她精致的物品。
真笨。我把我的平底鞋浸上了汽油。
好吧。保持平静。我会穿着它们直到一切完成,然后在我跑出去时,把它们扔进身后的大火。
在外公的书房,我站在桌子上,把汽油溅在直达天花板的书架上,把汽油罐举得离我远远的。还剩下不少汽油,这是我最后一个房间,因而我在书上浇了很多。
接着我把地板淋上汽油,把引火物堆积在地板上,退到通向后门的小门厅。我踢掉鞋,扔到杂志堆上。我走到一块干地板上,把汽油罐放下。从我的牛仔裤口袋里拉出纸板火柴,点燃我的那卷纸巾。
我把燃烧着的纸卷扔进引火物,看着它点燃。它着了,火势越来越大,渐渐蔓延。透过书房的双宽门,我看见一列火焰呼啸着经过一侧的过道进入另一侧的起居室。沙发亮了起来。
接着,那些书架就在我面前燃烧起来,浸过汽油的纸比任何东西燃烧得都快。天花板突然烧着了。我没法看向别处。火焰太可怕了。令人毛骨悚然。
有人惊叫起来。
再次惊叫。
声音就来自我上面的房间,一间卧室。约翰尼在第二层忙活。我点燃了书房,书房比任何地方烧得都快。火向上蹿,约翰尼还没有出去。
哦不,哦不,哦不。我向后门猛扑过去,但门上了锁。我的手因为沾上了汽油而滑脱,金属已经很热了,我转动门闩——一,二,三——但有地方不对劲,门一动不动。
又一声惊叫。
我又试了下门闩。失败了。放弃。
我用手捂住嘴巴和鼻子,跑过燃烧的书房,经过燃烧的过道来到厨房。厨房还没有烧起来,谢天谢地。我穿过潮湿的地板,朝衣物室的门跑去。
跌跌撞撞、打滑、摔倒,在汽油坑里浸湿自己。
跑过书房时,我牛仔裤的下脚烧着了。火焰舔舐着厨房地板上的汽油,猛地窜向细木工家具和外婆的明亮洗碗巾。火窜到我面前的衣物间出口,我的牛仔裤也烧着了,从膝盖到脚踝。我穿过火焰,猛扑向衣物间的门。
“出去!”我喊道,虽然我怀疑没人能听到我。“现在出去!”
到外面后,我扑向草地,在草地上打滚直到我裤子上的火焰熄掉。
我可以看见克莱尔蒙特最上面的两层受热发光,我自己的一层完全燃烧着。地下室那层,我不知道。
“盖特?约翰尼?米伦?你们在哪?”
没有回答。
抑制住惊慌,我告诉自己他们肯定已经出来了。
平静下来。没事的。肯定。
“你们在哪儿?”我再次喊道,跑了起来。
再一次,没有回答。
他们有可能在船库,正放下他们的汽油罐。并不远,我边跑边尽可能大声地叫他们的名字。我的赤脚踩在木板步道上,发出奇怪的回响。
那扇门关着。我猛地把它拽开。“盖特?约翰尼?米伦!”
没人在那里,不过他们可能已经在卡德唐,不是吗?琢磨着我怎么花了这么久。
从船库有一条小路经过网球场到卡德唐。我又跑了起来,小岛在黑暗中异常安静。我一再告诉自己:他们会在那里。等我。担心我。
我们会大笑,因为我们都是安全的。我们将在冰水里浸泡烧伤的伤口,感觉足够幸运。
我们会的。
然而我到那里时,我看见那栋房子一片黑暗。
没人在那里等待我。
我飞跑回克莱尔蒙特,它在燃烧,从底部向顶部。角楼烧着了,卧室烧着了,地下室的窗户发出橙色的光芒。一切灼热。
我跑向衣物室入口,拉开门。浓烟翻腾而出。我脱下浸了汽油的毛衣和牛仔裤,透不过气来,我塞住嘴,挤了进去,进入厨房楼梯井,往地下室走。
台阶下到一半,有一堵火墙。火墙。
盖特没有出来。他不会出来了。
我折回来,往上跑向约翰尼和米伦,但我脚下的木板在燃烧。
楼梯扶手烧着了。我前面的楼梯井坍塌了,喷着火花。
我向后踉跄了一下。
我没法上去。
我没法救他们。
现在没有地方可去,
没有地方,
没有地方,
只能下去。
82
我坐在温德米尔的台阶上,仍然盯着盖特在夜色中消失的方向,忆起这些,就像重新经历了一遍。对我做过什么的认识像一场雾进入我的胸腔,冰冷、黑暗蔓延开来。我皱起眉头,俯下身。冰冷的雾从我的胸腔穿过背部,上达我的脖颈。它充斥我的大脑,下达我的脊柱。
寒冷、寒冷、悔恨。
我不应该先把厨房浇上汽油。我不应该在书房点火。
把那些书彻底打湿是多么愚蠢。任何人都会预计得到它们会如何燃烧。任何人。
我们应该确定一个时间点火。
我应该坚持我们待在一起。
我不应该去查看船库。
我不应该跑去卡德唐。
要是我能快一点跑回克莱尔蒙特,也许我能把约翰尼弄出来。或者在地下室着火之前警告盖特。也许我能找到灭火器,阻止火焰。
也许,也许。
要是,要是。
我如此渴望我们拥有:没有约束和偏见的人生。自由去爱和被爱的人生。
可是,我杀死了他们。
我的说谎者们,我亲爱的人们。
杀死了他们。我的米伦,我的约翰尼,我的盖特。
这一认知从我的脊柱传到我的肩头,穿透我的指尖,让它们变为冰。它们破损碎裂,细小的碎片散落在温德米尔的台阶上。裂缝裂开我的胳膊,穿过我的肩头和颈部前端。在一个女巫悲伤的咆哮中,我的脸冻僵破裂。我的喉头发紧,发不出声音来。
我本应被烧死,却冻僵在这里。
我本不应该说什么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我本可以保持沉默,妥协。电话交流就很好。很快我们就会有驾照。很快我们就会上大学,辛克莱家的美丽房子会变得遥远而无关紧要。
我们本应该耐心些。
我本可以理智些。
也许那样,我们喝掉姨妈们的酒后,就会忘掉自己的愿望。酒会让我们瞌睡。我们会在电视机前打盹儿,冒干火,也许,不会点燃任何东西。
一切没法撤回。
我爬进门,用满是碎冰的双手爬到我的卧室,身后拖着冻僵的身体碎片。我的脚后跟,我的膝盖骨。我在毯子下面痉挛性地发抖,一片片的我脱落到枕头上。手指。牙齿。颌骨。锁骨。
最后,最后,颤抖停止了。我开始暖和,软化。
我为我的姨妈们哭泣,她们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为威尔,他失去了自己的兄长。
为利伯蒂、邦妮和塔夫脱,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姐姐。
为外公,他不仅看到自己的住宅烧为平地,还看到自己的外孙丧生。
为那些狗,那些可怜淘气的狗。
我为整个夏天我那些无谓的、轻率的抱怨哭泣。为我可耻的自怜。为我对于未来的计划。
我为所有赠送出的东西哭泣。我想念我的枕头,我的书,我的照片。我颤抖,为自己慈善的妄想,为我伪装成美德的羞耻,为我对自己说的谎话,加之于自己的惩罚,加之于我母亲的惩罚。
我哆嗦着哭道,这个家全被我谋杀了,我就是如许悲痛的罪魁祸首。
终究,我们没有保住那份愉快恬静。如果说它曾经存在过,已经永远消失了。我们失去了那份天真,在我们知道姨妈们的愤怒程度之前,在外婆去世外公体力衰退之前。
在我们成为罪犯之前。在我们成为鬼魂之前。
姨妈们和妈妈彼此拥抱,不是因为她们摆脱了克莱尔蒙特和它所代表的一切重压,而是出于不幸和同情。不是因为我们解放了她们,而是因为我们毁掉了她们。她们在恐怖面前彼此依靠。
约翰尼。约翰尼想跑马拉松。他想一英里一英里地跑,证明他的肺不会衰竭。证明他就是外公想要他成为的那种人,证明他的力量,虽然他很小。
他的肺里充满烟尘。他现在没有什么可证明。没有什么可为之奔跑。
他想拥有一辆车,吃在面包店橱窗看到的花式蛋糕。他想要大笑,拥有艺术品,穿制作精美的衣服。毛衣、围巾、带条纹的羊毛制品。他想用乐高做一条金枪鱼,像动物标本那样挂起来。他拒绝严肃,他让人窝火的不严肃,但他与别人一样,致力于他在意的事情。跑步。威尔和卡丽。说谎者们。他的正义感。他毫不犹豫就放弃他的大学基金,来维护自己的原则。
我想起约翰尼强壮的手臂,鼻子上防晒霜的白色条纹。那回,我们由于毒葛都不舒服,一同躺在吊床上搔痒。那回,他用薄纸板和在海滩找到的石头给我和米伦建了一间玩具小屋。
约翰尼·辛克莱·丹尼斯,你本可以成为一束光,照亮黑暗中的许多人。
你一直是。一直。
我以最糟糕的方式让你受挫。
我为米伦哭泣,她想去刚果看看。她不知道她想如何生存,她相信什么。她一直在寻找,明白她被吸引到那个地方。如今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实现,只有一些供人们取乐的照片、电影和出版的故事。
米伦谈了很多关于性交的事情,可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小些的时候,她和我一起躺在温德米尔门廊的睡袋里,笑着吃软糖,很晚才睡。我们为芭比娃娃争吵,给对方化妆,梦想爱情。米伦永远不会有满是黄玫瑰的婚礼,也不会有爱她到戴傻气黄色宽腰带的新郎。